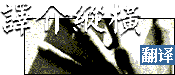《“那不可說的”》為陀爾本﹒施羅特﹒彼特森去年遞交歐登斯大 學哲學系的學位論文。(陀爾本﹒施羅特﹒彼特森, Torben Slot Peterson ,丹麥人。二十二歲。)

作者的話
從京不特處知道他有興趣於我的論文《“那不可說的”》並且將之翻譯成為中 文,我決定寫一段小小的文字,談一下關於我自己對於這篇論文的看法。
我很清楚,在論文之中還有許多地方存在著一些模糊點。但是我還是認為,對 於那些“對認識論中的問題的‘化解’”(注),我在這論文之中給出了我的這一部
分並非是非本質的思想。
首要的論點是:認識論中的這些問題是一類作為對認識概念的沉思的結果而出 現的問題,而那“關於認識的概念”則在根本上是悖論性的。
粗略地看,這裡的問題是在於:認識概念是把“一個洞察能夠代表一個絕對肯定 的事實”作為“(這所提及的)一個洞察能夠被稱作認識”的先決前提的。我想作出
論述的是:我們永遠也無法“絕對地設定”什麼事實。
既然沒有任何洞察能夠因此被稱作認識,一個這樣的認識概念的結果就是:一 切都走向並且成為“不可說的”。
注:“化解”這個詞在這裡的意思就是:“把一個問題定作是無意義 的,而隨之宣稱這是對問題的解決”。諸如邏輯實証主義通過把形而上學的問題稱作“ 無意義”問題或者“胡說”而宣告解決了哲學史上的所有無法解決的問題。〔京不特 注〕
﹒陀爾本﹒施 羅特﹒彼特森﹒
“那不可說的”
◆引言
在這篇論文中,我將闡明“那可說 的”和“那不可說的”之間的關系,並且以 此來解釋一些我們的認識上的基本條件。
這是一個嘗試,努力給出對於認識論中的 基本特征的主題。根據事實的性質,我的 嘗試將在一個頗不妥協的形式中進行。我
的目的是盡可能廣地反思這個問題,希望 以此能夠為認識論的發展作出小小的促進。
◆“那不可說的”的本體論
通常,“那不可說的”這個概念被用 來標示“那無法被說出的東西”。因而在本 體論上這是一個很廣的概念,並且被用在
許多無數不同的“實情”( Sachverhalten 維特根斯坦的用語--見《邏輯哲學論》。--
京不特注)之中。為了能夠為我對這個概 念的使用給出一個框架,出於實踐上的考 慮,最好是能夠給出一些關於“我將在論
文之中讓這個概念覆蓋在哪些方面”的例 子。
就我的設想總而言之,“那不可說的” 這個概念覆蓋了所有在“認識之彼岸(在 認識所不能涉及的地方)”的一切。這樣,
這個概念幾乎在所有哲學家那裡出現過,-- 當然,以不同的名目、並依賴於該哲學家 所認為的“認識是什麼”。
對於“那不可說的”的經典例子是斯賓 諾莎的“實體( substantia)”,
這“實體”等同於自然或者上帝。既然,實 體、上帝或者自然被理解作是自身因( causa
sui),並且,通過關於那創造出(作 為結果的)事物的先驗的條件的知識,或 者說,那關於“因”的知識,這作為“果”的
事物才能被我們認識;那麼,這實體就必 須是無限的;因為一個有限的實體總是能 為外在的“因”所作用,因此不能再成為它
自身的“因”。根據斯賓諾莎,人作為有限 的存在物無法認識實體自身,既然這種認 識要求有無限的智力,人的認識只是被限
制於一個特定范圍而僅僅了解這實體一部 分屬性。所謂這實體的屬性,換一句話說/ 就是這實體的“上層特征”(物質、意識等
等),這些屬性共同地結構於這實體的本 質。不用更深入於斯賓諾莎的論題,我們 天賦啟示於這實體的兩個屬性,也就是形
體屬性和思維屬性,而根據斯賓諾莎,我 們能夠讓自己設想有無窮多種的屬性。我 們能夠設想,但是無法認識到除了“思維”
和“形體”之外的其他無窮多種屬性,因 此這實體的本原的及其無限的本質是不可
說的。 〔注一〕
另一個例子,可能是更容易被理解的 例子,看來是康德的“物自身
das Ding sich”〔 注二〕,一個用來標示“作為自身而在
的事物”先驗概念,--就是說,這個概念 是關於事物是怎樣不依賴於人對它們的認 識而存在,或者換一種方式說:如果存在
一個無所不知的上帝能夠同時以所有不同 的本體的存在的方面“看”事物,在這個上 帝“眼”中的“事物本身”是什麼。康德把“
作為自身而在的事物”稱作“本體 noumena (拉丁語。 noumenon
的復數為 noumena。-- 京不特注)”,它也被用來表示“事物中的,
對於人的認識來說是不可知的,某些什麼 東西”--也就是說是人所無法認識的,既 然人類根本就不具備為達到一個對於世界
或者一個客觀對象的“完全認識”所必需 的工具。康德說,人的認識是以時間和空 間這兩個認識形式以及一個認識范疇(比
如因果律等等)的集合為先決前提的。對 於世界的認識是通過這些工具而被導出的 ,而這被認識了的“世界”卻不是作為本
體的世界本身(就是說,在無條件的或者 本體的 noumenal
意義 上的世界本身),而是顯示於那認識中的 人的感覺的“世界”,就是說,作為認識現 象的世界。既然人的認識是有條件限制的,
那麼人對於世界的描述也就不能說是完全 的,這樣,進一步說就是:關於“世界-事 物”自身,是不可說的。
在美學上同樣運行著一個“那不可說 的”的概念。人們恰恰可以把那可描述的 和“那不可說的”區分開。
比如說在一個畫面中加工了一個給定 的結構。人們可以在畫面中分析黃金分割 點等等,或者,人們可以評述在詩歌中詩
人使用的是什麼樣的風格、音韻等等。但 是這種評述只能是關於給定結構或者畫面 或詩歌的構建,而不是關於我們體驗圖象
或者詩句時所具的感情,比如說,年輕的 蘭波寫關於他自己獨創的詩歌語言:
“一開始只是嘗試。然後我寫下靜寂、夜、 那不可說的。甚至暈眩賦我以形象。”〔
注三〕
這個小小的,卻並非是不相關的關於 天才詩歌的例子可以讓人在一定程度上更 進一步去描述;你可能說,這文學形式是
散文化的,它以過去時通過一個有歧義的 意象語言描述詩人從前的行為,等等。但 是在結構之外還是有著別的東西,--在
那可以用描述性詞匯來轉達的東西之外, 在那主觀際性( intersubjective
)的元素之外。人們可以說,它是個人的 或者私下的體驗。〔注四〕
關於我在閱讀了這些詞匯之後心中的“ 泛潮”則是我所無法完全地描述的。我可 以用某種指向:迷幻劑為我帶來的唇角上
的微笑、一種對於詩人的內心體驗的驚異、 一種想要繼續讀下去的欲望以及諸如此類; 但是除了通過使用我所學到的、能夠大致
地和我在這處境之中所得的體驗相應的概 念來轉達之外,我不可能用別的方式來表 達。我能夠達到的,至多只是喚起那些聽
我敘述的人的通感。卻無法以任何方式擔 保那和我有著“同感”的聽者能夠鑒定出 他的體驗是否同一於我的,在原則上他沒
有可能具備進入我的體驗的必要“入口”。 體驗本身存在在那裡,而既然我無法將之 向他人完全地轉達,那麼它就有著“那不
可說的”的特征。
這裡,我們以一種稍有不同的方式來 理解概念“那不可說的”的運用。在美學上, 那不可說的指向那“個人的第一手的、原
則上私下的體驗”,這是作為體驗者的我 所無法向他人完全溝通的。
在有了以上的這些只能以隱喻的方式 來解說的“那本體上不可說的”的例子之 後。看來我們可以稍微容易一些地進入這
個問題:這個概念本身以其本原的意義所 標示的到底是什麼?在道教、佛教,特別是 禪宗佛教中,它被用來標示“道”,標示“
一切”,以及作為人的作用的最終目的的“ 悟”。
在下面我列舉一些大流的觀點,主要 是禪宗佛教和道教,但也稍稍提及主流佛 教的思想。我的目的不在於完全地論述在
不同的傳統之下的不同學說,或者它們得 出了怎樣的結論,這裡我所特別感興趣的 是,關於“那本體上不可說的”,以及關於
達到對於“那本體上不可說的”的認識入 口的可能性,它們是怎樣說的。
道教和禪宗相通的地方是,它們並非 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宗教(那些設定一個 或者許多人們能夠崇拜的神的宗教),同
時它們也不是什麼哲學的體系(因為在“ 人們是否接受它們的教義”這個問題上, 最終牽涉到一個關於信仰的問題,而不是
一個涉及理性的論証--見下面的闡述)。 人們將它們稱為“解脫”。“
它們的目的是使人脫離苦難而進入與世界 和生存之本原的內在本質的一致”。〔
注五〕
“道”所標示的是“一切存在”;斯賓諾 莎所說的“實體”和康德的“物自身”也就 是這個。道的特征是它不能被理解為我們
通常所理解的世界中事物。人們通常用來 達到認識的方式,根據道家或者禪家的說 法,是將“一個什麼什麼”從“其它的什麼
什麼”中區分出來,換一句話說,一個“甲” 被認識作為一個“甲”,就是把它在與“其 它”的聯系中限制出來,它被限制在一個“
甲具有它位置和功能”的范圍裡。比如說, 白紙上的一個黑點,這黑點被認識作黑點, 因為它是處在與白色表面不同的反差之中,
也就是說通過限制或者差異,“黑點”出現 在白紙上,而那認識者打算達到對於“白 紙上的黑點”的認識,那麼他自然而然就
焦注於他認識之中的“黑”而把“白”限制 其外。我想提及的就是認識的這個特征, 這裡我們將之稱為“差異化的認識”。
相反,如果我們所要著手進行的事情 是“認識一切”--這裡意味著,用上面的 例子的話,人不是僅僅將意識焦注於那黑
的或者那白的,而是同時焦注於黑白兩方 面--這樣我們的認識形式就失效了;恰恰 是根據了我們的差異化的認識形式,我們
不得不通過這“一個什麼什麼與其它的什 麼什麼之間的關系(差異關系)”來認識、 思考或者談論這個“什麼什麼”。這樣一來,
如果我們不能在我們的差異化認識形式中 以差異化的思維方式來網羅“一切”,那麼 我們就不能談論道,因為語言是建立在概
念的基礎上而成為單義明確的(不被誤解 的)交流工具的,就和思維一樣,語言總是 將人們所談論的現實中的一個部分差異化
出來而焦注於這“和不是這個東西的所有 其它東西不同”的“這個東西”。所以對於 道的認識是不可說的。
這個關系可以用著名的有關於道的幻 覺的類比來進一步闡釋。如果人們為此能 夠定出“對於道的幻覺”,那麼這“對於道
的幻覺”將是怎樣的呢?一個對於道的認 識差異於一個對於道的幻覺。道是“一切” 。這樣的一個設定必須顯示出“一切”,
而先於“差異”;但這樣一來在有設定之前 已經有了差異。(“差異
的”和“非差異的”之間本身就有了差異)。 〔注六〕
這理解的出發點是:既然你打算得到 一個對於“一切”的認識,你就必須脫離差 異化的認識形式而進入一種“同時焦注於
一切”,或者確切的表達,“根本就不焦注 於任何東西”的認識形式。你就必須不把 世界劃分成不同的對立面,必須不把世界
中部分看成有相互不同,因為這“不同”恰 恰就是表明了你焦注於“全部中的一個部 分”而不是焦注於“全部”本身。“全部”
或者道本身是非差異的、非劃分開了的。 它總是在那裡存在著,將之差異化了的是 我們人類--人觀察它,看見它的某種特定
的性質而非其它。
“不焦注於道的某個特定范圍”,這聽 起來容易,卻遠遠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 因此我們在這裡有三種各有其技術追求的
理解:解脫、悟(對於“一切”的體驗)和涅 磐(對於“一切”的本體性理解的經典印度 名詞)。
如果一個人能夠成功地擺脫對於存在 的任何一種劃分形式,那麼他就能夠達到 那“徹悟”;粗略地說就是涅磐體驗(這種
體驗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根據不同的體驗 維持有不同的時間;依據於人們所談的是 哪一種)。
(或許彼特森在這裡是說“入定”,在 許多丹麥語的關於東方哲學的書籍中沒有 把“最終解脫”的涅磐和一時坐禪的入定
區分開,這裡一概稱作“涅磐體驗”。我和 陀爾本﹒施羅特﹒彼特森談過關於涅磐經 驗的問題。這裡陀爾本﹒施羅特﹒彼特森主
要談論的是“那不可說的”,所以關於東方 玄學中的細節並不重要。--京不特注)
這樣關於涅磐體驗或者“悟”就有了某 種極其悖論性的麻煩了。我們能夠在認識 論的意義上把它定在“那不可說的”的范
疇之中--也就是說“那處於我們的語言、 思維和認識的彼岸的東西”。於是這樣一 個陳述“‘悟’是由‘知道那
在現實之中所不是的東西’構成的” 〔注七〕,就是一個純粹的在經驗內容
上否定定義;我們唯一能夠說的,就是它 所不包含的東西。
人們終於可以在這裡停止更深的探究 了,因為一個對於那些持相關觀點的人甚 至根本就會說,這樣一個否定的定義都是
不可能的。你定義那否定性的東西,就是 說你仍然定義了;而一個定義就是一個限 定,就是建立在差異的基礎上的。如果你
想理解道,那麼你就根本不能通過差異化 去理解。
比如說,如果你至少還能說關於那“作 為自身存在的現實”是要麼存在要麼不存 在,那麼你還是進入了這麻煩。大乘佛教
哲學家吉藏(549-623。隋唐僧人。大乘 三論宗創始人。--京不特注)在解釋普通
的差異化認識和“悟”之間的關系時如此 說:如果你談論關於現實之存在或者不存 在,那麼你就是處於一種語言的框架之中;
存在和不存在只是在這個語言的框架之中 作為相互對立面的時候才具有意義,--所 謂在語言的框架之中,也就是說,是在思
維或者差異化認識的范圍裡。那不可說的, 道的本體論,卻是處在這之外,或者說,在 這個范圍的彼岸。為了能夠理解現實的真
正相,你就不得不步出語言的區分功能,-- 在這裡也就是存在及其
對立面非存在之間的兩元論。〔 注八〕 這樣涅磐經驗就包容了對於全部
基本邏輯原則根本性的違背;--在這裡關 於邏輯矛盾律本體性的
解說就是:“一個事件(一個“實情”、一個 事實)不能同時地既出現又不出現”。〔
注九〕
(這裡所謂的“打破邏輯基本原則”和“ 非邏輯思維”等等,不同於我們所說的“邏 輯出錯”。它可以被含糊地解說成為“沒有
對錯之分”。--京不特注)
對於關於“悟就必須拋開邏輯原則”的 斷言可以延續為這樣一個問題:涅磐體驗 到底是不是可能的?從認識論的角度說,
對於涅磐經驗,到底是能夠找到這種或者 那種証據來確証它純粹理論地說是可能出 現的,還是我們僅僅只能想象它出現的可
能性?問題是關於對一個如此經驗的存在 的設想,它和一個關於信仰,或者關於一 個宗教斷言,或者關於一個哲學上說是“
為是而是( ad hoc)” 的陳述的問題到底有什麼區別?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在事先搞 清楚,什麼是認識?稍後我才更深入地解 決上面的這些問題。在這裡我可以通過對
於“什麼看起來可以算是認識”進行限制 而給出一個大致的圖案。認識首先是差異 化的。對於“某物”的認識,是某種可說的
東西,某種通過這“某物”與某些其它物之 間的關系而進行限制的東西,由此,認識 作為認識本身是不同於體(經)驗的。在對
關於美學中的“那不可說的”的闡述中我 們看到,比方說在一首詩中,詩歌的結構 是可以描述和轉達的,也就是說,是主觀
際性的( intersubjective), 不同於那美學體驗--第一手的、個人的、
私下的體驗。
如果這是牽涉到認識,就是說它作為 認識自身必須是可以被描述的,那麼,關 於對於涅磐體驗(如果這個體驗是以非差
異化和不可說為特征的)的可能性認識的 問題就等於是這樣一個問題:非差異化的 思維是不是可能?或者說,是不是有能夠
進入非邏輯的、非差異化的精神狀態的可 能(這裡不使用“思考”這個概念,既然現 在思考和“認識”一樣地被用謂詞“差異化”
來定義了)。
盡管那在認識論上是涉及了一個自相 矛盾的說法,如果一個人宣稱要為“處在 一個非邏輯的精神狀態是可能的”這樣一
個論題給出依據,卻並不說明由此就達到 一個証明“事實上處在一個非差異化體驗 的狀態(或者可以被含糊地稱作‘非邏輯
的思考’)是純粹不可能”的本體論的論証 。這只是意味了“處在一個非邏輯的精神 狀態”的本體論可能性是無法完全地明確
地被認識的。另一方面,我們是不是也就 永遠無法証明“非邏輯地思考是本體性地 不可能的”或者“完全沒有達到涅磐體驗
的可能性”,--既然我們無法知道這樣一 個論証是怎樣的?涅磐體驗或者非邏輯思 想,根本就是“根據其假設(
ex hypothesi)”處於我們對之的差異化認 識之外的,--這樣人就是無論如何都被關
閉在“進行差異化的論証”之外了。於是, 對於“達到徹悟”的可能性,我們既無法肯 定又無法否定。這就是說我們無法在談論
對於“道”的體驗的原則性的可能性上比 談論“道”的本體論談出更多了,--既然 那是“不可說的”,二者都是一旦“可道”
便“非常道”了,--既然“斷定一個非差異 化的體驗的存在”的可能性原則性地是處 在我們的認識的彼岸,也就是不可說的。
當我們談論那道家、禪家以及普通佛教中 所力求的那種對於“一切”的神秘體驗時,“ 認識”這個概念就根本不能被用上。
涅磐體驗被更進一 步闡述,就是作為對“主觀和客觀間的區 分”的取消〔注十〕。所以
我們無法認識道,既然道是對“那本體地 不可說的”的體驗(它的可能性存在對於 差異化的認識是一個自相矛盾,因此是不
可說的);我們也無法認識“那本體地不可 說的”自身( per se)(
道,“那無所不包的、非差異化的本體論” 自身,對此差異化的認識是無法找到一個 認識入口處的)。語言/思維是差異化的,
不能同時將它們的概念/注意力焦注於差 異的兩方面,而這個“同時焦注全部各方 面”則正是“道”所要求的。
問題在於理解什麼是道。那可以被我 們理解或者察覺到的“道”總是一個差異 化了的“道”:恰恰就是作為“那非差異化
的”,它是對於“那差異化的”的差異化( 於是也同時是“差異化的”;但是這裡,不 應當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個著名的“關於撒
謊者的悖論”上。--京不特注),總之是無 法走出語言上的區分功能。道在所有這些 之外,也在所有我這裡所寫到的東西之外。
人們可以被經驗誘惑,“經驗地”或者“ 後天( a posteriori)
地”說,某某聖人或者聖女有過這對於“道” 的體驗;或者幹脆說,他自己有過這體驗。 但這是沒有用的。這種說法至多只能是一
種“宣稱”,而不是什麼有意義的陳述,既 然這種“對於道的體驗”先天地、概念性地, 或者說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就是作為一種
自相矛盾和不可能(非邏輯/非差異化)而 被差異化了;同時,正如上面所寫到過的, 這卻又不說明它是“本體地不可能的”或
者“從來不曾有過”--只是如果有人達到 過,卻並不能記得它而已;思維中的記憶 也是差異化功能,並不能包容道。
於是我們不可能描述道。道是不可說 的。所以禪宗的基本原則可以用一句引言 來概括:
“那知道的人不說。
那說的人不知道”〔注十 一〕
[作者原注]
注一:參閱 Frederick Copleston, S.J.: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IV. Page 214-217.[回文中]
注二:參閱 Frederick Copleston, S.J.: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VI. Page 266-272. [回文中]
注三: A. Rimbaut. --亞瑟﹒蘭波《地獄中的一
季》。 [回文中]
注四: David Favrholdt: "Om graeser for
beskrivelse i aestet iske anliggender". page. 92(“關於美學性描 述的極限”)
[回文中]
注五: David Favrholdt: "Kinesisk filosofi".
page.57(“中 國的哲學”) [回文中]
注六: Alan Watts: "The Way of Zen".
[回文中]
注七: Alan Watts: "The Way of Zen".
[回文中]
注八: David Favrholdt: "Kinesisk filosofi".
page.87(“中 國的哲學”) [回文中]
注九:可參閱哲學辭典中 關於“矛盾律”的辭項。 [回文中]
注十: David Favrholdt: "Kinesisk filosofi".
page.92(“中 國的哲學”) [回文中]
注十一: Alan Watts: "The Way of Zen".
[回文中]
〔京不特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