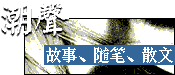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雷 默﹒
書 與 枕 頭
對於一個喜歡讀書的人,書和枕頭常 常是在一起的。一年四季,枕頭可以只 使
用一個,書卻是不斷更換的。看一個人最
近有沒有讀書,只要到他枕頭底下去翻一
翻就清楚了。
使
用一個,書卻是不斷更換的。看一個人最
近有沒有讀書,只要到他枕頭底下去翻一
翻就清楚了。還有一種人,將枕頭和書簡化成枕頭 就是書。一兩本書,放在床頭,倚著是看, 躺下是枕,倒也省事。這種人對生活一般 不太講究,吃啥穿啥住啥都無所謂,惟獨 讀啥不能馬虎,總是選擇自己喜歡符合自 己性情的書來讀。我就見過一個電腦迷, 床頭堆的就是這方面的書。我在學校讀書 時,有一次枕頭被老鼠咬壞,也幹脆用書 作了代替。奇怪的是,直到畢業,鼠輩們居 然沒有來“咬文嚼字”。將書當枕頭的另一 種情形就是在辦公室或旅途小眠,純粹的 實用主義,沒有意思。
我也見過枕頭底下一直放著同一本書 的人。
第一個是我的一個女同學。書是一本 屠格涅夫的散文詩,我和她一起在新華書 店買的。她說很喜歡,我一讀完她就拿了 去。隔了幾天,我問她讀完沒有,有什麼感 覺,她說讀完了,寫得很好。可是,兩個月 後,文明宿舍檢查時,我意外地發現書還 壓在她的枕頭底下。
我隨手翻開,原來我無意疊起的書頁 似乎未動過。
由此,我知道了她不是一個喜歡讀書 的人。之所以將這本書放在枕下,開始大 概是一種少女美好的感情表現,時間一長, 給忘記了。
第二個是我樓上的一個人。當時,我剛 來南京,住單位的集體宿舍。晚上沒事, 樓上樓下串門。其中一個人知道我寫詩, 就問我有沒有白朗寧夫人或雪萊的詩集。 我心一喜,沒想到這裡居然也有愛詩的人, 把書借給了他。幾個月後,我整理書籍,想 起這事,就問他書有沒有看完。他先是一 楞,突然反應過來,讓我跟他去樓上拿。“ 哎呀,我把它丟哪兒了呢?”聽著他自言自 語,我料想書是沒了。哪知他把枕頭一掀:“ 哈,我一直把它藏在這兒呢。”
很顯然,此人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詩友。 他跟我借書並把它遺忘枕下不過是一時心 血來潮。八十年代初,是一個全民文化補 習的時期。似乎人人都有一種求知欲,絕 大多數人都是曾經在枕頭下壓過一兩本書 的。
這都是十幾年前的事。
時至今日,有多少人還保留著在枕下 放一本書的習慣呢?有幾個少男少女還以 一本書來作為感情傳遞呢?就是附庸風雅 者,也將書擺進了漂亮的書櫥。
今天,誰要是還在枕頭下放一本書,肯 定是個書痴。
■
停電的感覺
下班回到家,伸手拉電燈開關。“噠” 一聲, 燈
並未亮起來。
燈
並未亮起來。我居住的地方平常供電很正常,所以 我一下子並未想到停電。
然而,當我確信停電時,我的心不知怎 的突然放鬆下來,感到一種很久未有過的 愉悅。象古代參禪的和尚一樣,有所“頓悟” 。
我從容地騎車去菜場,不慌不忙地挑 選著自己喜愛吃的東西,又心平氣和地與 人討價還價,節奏一下鬆弛了許多。平日 的那份匆忙和緊張象泥牛入海,委實不見 了。
回到家裡,擇菜、做飯,一切顯得很平 靜。黃昏的微光從窗戶透進來,漸漸退去。 隨之,黑暗慢慢溶解,彌漫了屋子。然而, 我的眼睛卻十分地明亮,找什麼東西總是 一拿就到手。眼睛的天性得到了充分顯現。
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呢?道理很簡單,平 日裡,每晚總有許多事等著我們去做,或 看電視或玩牌,或看書或玩電腦,所以,賣 菜、燒飯甚至吃飯都急急忙忙的。沒有片 刻寧靜,讓腦子放鬆。好啦,今日停電,什 麼事都沒了。好像一下回到了幾十年前, 在鄉村度過的油燈歲月。閑適的感覺突然 蘇醒,自是一種“見山不是山”的境界了。
妻子去街邊的雜貨店賣來了蠟燭,女 兒急切地將它點亮。頓時,屋子裡就有了 光芒,但與電燈光不一樣的,多了幾許飄 忽感。
女兒也顯得很興奮,手舉著蠟燭不停 地在屋子裡走來走去,好像賣火柴的女孩。 燭光忽閃忽閃的,房頂也就跟著忽明忽暗。 女兒驚奇地瞧著這魔術般的變化,圓圓的 小臉在燭光中顯得燦爛,富有光澤。
手持蠟燭的情景原本就很少,只是在 生日時才有機會。何況,那也是象演戲一 樣難以讓人進入真實情境。今日,這樣的 突然而又逼真,實在讓孩子難以自持。
此種情景,使我想起了“閑敲棋子落燈 花”古句。我指著燒焦的蠟燭芯子告訴女 兒,古人所說“燈花”與此相似,只不過那 是一種油燈。其實,蠟燭也是一種油,一種 固態的油。
這下,我理解了美國詩人加裡﹒斯奈德 為什麼棄繁華都市不居,而選擇華盛頓北 部山區,不要電燈、電話等一切現代生活 設施,過著現代桃花園式的生活。我真渴 望有一天也去體驗一下這樣的人生。
那是一種什麼滋味呢?
■
秋 虫 叫
時值秋分與白露之間,天氣還很熱。深 夜,約莫十二點多鐘。我搬張板凳坐到院 中,點支香煙,靜靜地享受一天裡最寧靜 的 光
陰。
光
陰。對面樓裡的燈一盞一盞地熄了,月亮 悄悄爬上了樹梢。空氣漸漸地有些濕了, 怕是有露水在樹葉上躺著,映出靜穆星空。 秋夜顯得好寂寥。
不知何時,我聽見“唧唧--唧唧”的虫 叫。好幾處草叢裡都躲著虫兒,聲音此起 彼伏,很有立體音樂的味道。
我完全被吸引了。正聽得入神時,“嗖” 的一聲,不知是蝙蝠還是什麼從不遠的樹 叢飛過,我一驚,抬頭尋時,什麼也沒見。
復又專心於虫叫,“唧唧……唧唧……” 我感到了空氣的微小震顫。黑夜似乎減了 些寂寥,卻添了幾份清幽。
前幾天,我也在深夜時分坐到庭院裡, 奇怪的是竟未聽到一聲虫叫。虫子是今天 才開叫?肯定不是。應該說是我的心今天 才有感應。幼時寫作文喜歡用“人聲鼎沸” 來形容人多熱鬧的場面,可如今卻是天天 人聲鼎沸,攪得耳根不清淨,難怪聽不到 虫子的聲音了。
我居住的地方在郊外,又是一樓,又喜 在深夜靜思,如此偶遇這機緣,聽得幾聲 秋虫叫。那些居在城裡的人,住在高樓裡 的人,十點鐘準時睡覺的人又如何有此耳 福呢?
小時候在鄉下,秋夜裡倒是天天聽到 虫叫的。鄉下虫子膽大,常常就在床底下。 叫聲象催眠曲,送我入夢。可是一覺醒來, 撒泡尿後,聽著虫叫,就怎麼也睡不著了。 於是拿了油燈,趴到床下來捉,或是爬到 媽媽床上去。想來有趣。
又想起南京大學張子清老師,學校分 房,他不撿好樓層,偏要住一樓,說是可以 在庭院裡蒔花弄草。於是常常讓研究生去 紫金山幫他挖土回來,喂那一院子的花草。 他雖居城裡,但肯定也會聽到秋虫叫的。 因為他有泥土和花草,並且也常常在深夜 獨思。
■
米 的 滋 味
一日晚上,十一點多鐘,突然想吃東西。 東找西找,翻出巧克力、餅幹什麼的,都沒 興趣。揭開鍋,還有些剩飯,不由眼睛一亮。 一碗泡飯,就著辣蘿卜頭,美味得不行。好 像幾天沒吃似的。其實,那天我去城裡閑逛,中午在麥當 勞開洋葷,嚼了一個巨無霸,晚上又
 和
一朋友喝酒吃菜,只是未食米粒罷了。
和
一朋友喝酒吃菜,只是未食米粒罷了。對米的這種依戀,北方人也許不能理 解。南方人栽培水稻的歷史已有幾千年。 那年,去武夷山,導遊告訴我,高高的巖洞 裡有幾千年前的稻谷。經過歲月的風蝕, 稻谷雖已炭化,但基本形狀依稀可辨。望 著幽幽的洞穴,我兀自發愣,覺得很是神 秘。那麼高的巖洞,古人是怎樣攀沿上去 的?難道是猿人的傑作?先人為什麼單單 將水稻種子藏於巖洞?是某種昭示?後來, 我在歷史博物館裡,見到了從古墓裡挖出 的稻粒,更覺得古人對於稻谷的感情較今 人尤甚。幾乎到了頂禮膜拜的地步。今天, 在我的家鄉,除夕晚上,人們用蒲包裝上 石灰,圍著稻倉打囤,希冀來年豐收,似乎 還保留了古人對稻谷的情愫。
南方人一直以米作為主食,一日三餐, 幾乎都離不開米,只把面食當作一種點綴。 今天的城市裡,早點比較豐富,但許多人 還是喜食米做的粑或蒸飯包油條。然而, 在我小的時候,大米卻是一種稀貴的東西。 不知是自然災害,還是什麼原因,一年盡 管也種兩季水稻,但大部分時日裡,我們 只能以大麥、野菜、雜糧填肚子,還常常吃 不飽。難得食上一頓白米飯,多是摻了青 菜、胡蘿卜、山芋或扁豆一道煮。新米剛出, 熬上一鍋米粥,那清幽之香,今天想起來 實在無法比擬。到了春天,青黃不接時,母 親常常將一小撮米放進紗布袋,紮緊置於 大麥面粥中,煮熟了我吃,自己喝麥湯。
那時,對於米的渴望,似乎成了我最大 的人生目標。常常想,哪一天象城裡人一 樣每月有二十八斤大米就好了。母親於是 就鼓勵我,好好讀書,跳出農門,到城裡去 食大米。今天的情形已經完全改變了,每 次回鄉,我倒背些大米回城。糟糕的是這 米的滋味已不如從前了,也許是天天食的 原因。
又聽弟弟講,現在種水稻,農藥比以前 用的多。
米的滋味,最憶是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