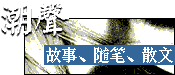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粟四維﹒
三伯父的照片
伯父就算不是父母吧,也是近親了。小 時候常聽同學提起他們的伯父,他的家如 何如何,他給了他們多少禮物等等、等等。 然而伯父這個詞對我 而言卻是個抽象概念。和許多所謂的外省
人一樣,父親只身隨部隊來台灣,海峽成
了天塹以後,就再也飛不回老家了。連父
親都不知道伯父的下場,在台灣出生成長
的我就更不會關心了。
而言卻是個抽象概念。和許多所謂的外省
人一樣,父親只身隨部隊來台灣,海峽成
了天塹以後,就再也飛不回老家了。連父
親都不知道伯父的下場,在台灣出生成長
的我就更不會關心了。從我有記憶開始,父親就從沒有安於 現狀過。他從不買菜,但每回我想吃些什 麼,他總會主動帶我到市場去。說真的,我 實在不想和他在公共場合一起出現。他一 到市場,一定先看看梨子蘋果之類。看到 小販說那是富士蘋果,他馬上吼了回去:“ 這是什麼富士蘋果,假的!根本是台灣自 己出的爛蘋果。”再隔幾天,看到了市場上 的梨,小販好心切了一片讓他嘗,他手一 揮,又用他那四川腔說,“什麼四季梨三 分利的,比大陸萊陽梨差遠了!”他喜歡抽 煙,在大陸貨還是禁忌的時代,不知從那 裡弄到一個大陸制造的煙盒,手一壓把手, 煙就出來了。他還滿自歡喜的告訴我,“大 陸做的,不一樣吧?”然而我發誓根本沒去 碰那東西,那煙盒就再也壓不出煙來了。 父親也就做個順水人情,把它送給我當玩 具了。有一天他從巷子口走回家,看見我 在樓梯口,坐在流動攤子上吃起蚵仔面線。 我本想告訴他這面線有多麼好吃,讓他也 有機會分享,但他沒等我開口,替我付了 錢,把我拉了回家,用他濃眉下如同黑暗 中從門縫透出光束般的眼睛盯著我說,“ 以後不準在街上買台灣人做的東西。”我 一直都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同樣是攤子上 的東西,臭豆腐他卻是趨之若騖。即使是 三十五、六度的大熱天裡,他只要一聽到 樓下賣臭豆腐那老頭的吆喝聲,即便是在 馬桶上蹲了半個多小時看報紙,他也會沖 出來,使勁地把那不怎麼靈光的玻璃門拉 開,向樓下大吼一聲,“臭豆腐,”然後就 隨便抽幾張新台幣往樓下跑。數分鐘後, 就看著他拎著一袋臭豆腐,邊走邊說,“兒 子,來吃。”他吃東西本來就不在乎什麼儀 態、儀表的,吃起臭豆腐來就更沒這回事 了,只見他張開大嘴,與其說吃,不如說是 猛烈地吸吮著帶著辣椒汁和酸白菜的豆腐, 接著就撕牙咧嘴地,像是拼命咬碎,又像 是舍不得往肚裡吞地似地,咀嚼著又燙又 辣的美味佳肴。
談到台灣的媒體宣傳,他更是嗤之以 鼻:電視上的政治評論,他說是愚民政策; 綜藝歌唱節目,他說是靡靡之音;廣告則 代表了社會腐化現象,新聞則是國民黨的 傳聲筒。總之,台灣在他的眼裡,根本是罪 惡之國,沉淪之島。更要命的是他口沒遮 攔的態度,確實給他帶來了不少麻煩。警 備總部在五、六十年代是人人談虎色變的, 而我父親三進三出,最後一回被人誣陷為 匪諜,幸虧承辦軍官是母親的老鄉,為人 寬厚,而他的四川土話也顯示出他的身份 是老粗而不是奸細,才逃脫了被槍斃的命 運。這些是都發生在我有記憶之前的事, 但後來聽父親和其他家人談起,總還是讓 我覺得自己的一生真是僥幸地被一位好心 人贖救了。不過,最令我難過的是有一回, 姐姐不知道為什麼偷偷地告訴我,
“爸爸是匪諜。”
我當然害怕這頂帽子扣到父親的頭 上,但更令我傷痛的是,為何父親成了一 個壞人?父親縱然經常無緣無故地打我, 但我相信他絕對是善良的。幾天後,姐姐 才又改口說,
“父親只是想家吧。”
我鬆了口氣。
※ ※ ※
然而,一直要等到二十多年以後,我也 在美國住了八年,我才能真正體會到父親 過去種種魯莽、不合常理的行為,只能用“ 想家”二字解釋吧。就在我入伍服役前沒 多久,父親從海外打了通電話回來,他不 知從那來得到的消息,說台灣快完蛋了。 這話我從來沒當真過,因為只要一有機會 他都會這麼說。但這次不一樣的是,他要 母親把房子賣掉,然後馬上移民美國。如 果母親不做,就是害了全家,把他用一輩 子的積蓄買下的房子,隨台灣的完蛋而付 之流水。在他的邏輯之下,為避免母親毀 掉他的一生於一旦,他的方法就是撂下一 句話,“你如果不賣房子我就不寄錢回家。”“ 家”,這個字在父親心中是模棱兩可的。家 的感覺可以強烈得讓父親即使在六十年後 的夢裡,仍上演著他和年歲相仿的侄子, 爬到樹上採桃子的故事;但卻也模糊得讓 他不以為養家是個死而後已的責任。然而, 我當時沒能體會到的是,父親定義的家和 我想要的家其實並不一樣。他不知道的是, 他心中的家已經在四十年代的動亂下,隨 著他到台灣而如殘雪般地消融了;而我要 的家則因他那不可及的家如夢魘般地斫傷 得永遠殘缺一角……
※ ※ ※
那已經是半世紀以前的事了。還和侄 子爬樹啃桃子的父親並沒有體會到祖父的 去世代表著什麼意義。
“祖父是個鄉紳,專門替人排難解紛的。”
這話父親也向我說了不下十幾回,每 回的表情總是那麼自豪。然而除了這話以 外,就再也沒聽父親說過有關祖父的事了。 大概在祖父出殯以後,父親仍然沒有停止 在桃樹林裡的遊戲,更別說接下來國民政 府從天的那一頭搬到隔江那棟白色的洋樓 房裡,除了稀奇以外又是怎麼回事。後來 家鄉來了許多連話都不會聽的外地人,有 些還穿著從沒見過的軍裝。不過這些久而 久之也就沒啥稀奇,反正不關己事,還不 如從小熟悉的幾個遊戲,癒玩癒有味道。 也許父親的一生也就是場遊戲吧,只不過 不同階段玩的不一樣。遊戲對在玩的人而 言是種生命,一如爾後父親每回和老板打 麻將,總是戰戰兢兢地,嬴也不是,輸更要 命。但對旁觀者而言,遊戲永遠只是浪費 時間罷了。記得有天早上母親突然問我,
“昨天晚上你爸爸還在和老板打牌的 時候,你是不是砰地一聲把門關上?”
我沒說話,也來不及想是不是該為自 己不禮貌的行為慚悔。如果是,那麼父親 只顧玩,不顧家人又算什麼,我心裡想。
“你爸爸陪著老板打麻將,聽到你的關 門聲,一邊打著,一邊出冷汗。”母親接著 說。
也許三伯父能在身旁勸他就好了,一 個半世紀以前,他看著父親盡在一些無意 義的事上消磨,他總有辦法以他的資歷和 學識指引父親一點人生的出路。做為兒子 的我只有承擔遊戲的代價。
“你三伯父是中央大學畢業的。”那時 的中央大學還在南京,沒遷到重慶。算算 時間,如果他還活著的話,而今已九十多 歲了,年歲上可以做我的祖父。
“你祖父和大伯父早死,家裡沒得吃的, 你三伯父就教我去考海軍官校。我當時連 初中都還沒畢業,連報考資格都沒有,三 伯父就從村子請了一個叫‘李傑’的人,高 中畢業,幫我……”
“報名?”我岔著問。
“哪裡?”父親又用那四川口音睥睨地 說,“不但報名,而且考試。所以你爸爸的 這個名字其實是那個人的;我是假的‘李 傑’。”父親眉飛色舞地大談他當初作弊找 槍手的經歷。
“那年海軍官校每省只錄取兩名,而我, 就是其中一名。”父親對考試的結果很是 驕傲。作弊的結果本來就不是自己的,但 如果結果改變了一生的命運,或即使僅僅 是一時的優越感,那總還是會因此自豪的。 待在學校一輩子的我在這點上總算能體會 父親的心思。
“我進入官校沒多久,學校就遷到了台 灣。”父親稍稍停頓了一下,接著說,“他 媽個X。蔣介石連一封信都不準我們寄回 去。”
“我在官校四年就只學會喊領袖萬歲。 還有就是一把手槍,告訴我們隨時準備為 領袖去死。
“你媽有沒有告訴你我被警備總部抓 去的事?”
“沒有。”
“嘿…嘿…這你就不知道了。”父親得意 地準備開始講述他的英勇事跡。“那年你 姐姐剛生下來沒多久,我還是個小少尉, 薪水連菜錢都不夠,還得付電費。不過我 想到了個辦法,我連了根線,就把電偷來 了。”
“你沒被查到嗎?”
“當然被人檢舉了,”父親睜著眼說,“ 連海軍總部都來查,說我破壞公共安全。
“呵呵…”父親捂著他的笑嘴,“你媽媽 當時嚇得臉都白了,抱著你姐姐都說不出 話來。”
“那你當時怎麼辦?”我問。
“我把來的人罵了一頓,說他們是國民 黨的走狗。本來想打他們,後來被你吳叔 叔阻止。吳叔叔塞了點錢給他們,他們才 走了。
“沒多久,我被派到船上,就在哨站門 口,兩個年輕軍人向我走上來,問我是不 是李傑,我說我是,他們就說我們的長官 請你過去一下。我什麼也沒想到,就拎著 包包跟他們進了一個屋裡,屋裡坐著一個 少將,陸軍的,他又重復問我是不是李傑, 我也照實回答。他從頭到尾看了我一遍, 皺皺眉頭,到桌上拿了一疊資料給我,我 看到上面印了‘機密’兩個字,寫著:
查李員生性玩劣狡猾,屢次散布污蔑 領袖之言論。今與匪勾結,欲將挾持XX艦 駛往匪區,令速將逮捕,交付審判,以儆效 尤。
“那怎麼辦?”我緊張地問道。
“那張少將又看了看我一眼,”父親氣 定神閑地繼續他的故事,“對我說,‘我看 你這個人老實得很,怎麼會做這種事?’我 就跟他說,‘什麼挾持不鞋子的,我根本不 知道這件事啊!’張少將接著告訴我,‘現 在有人要陷害你,你呢,就當做什麼都不 知道,走出門口後,什麼都不要提。’要是 當時沒有張少將一句話,我早就被槍斃了。”
父親說完瞇著眼睛,搖著那根翹著的 右腿,嘴巴似笑不笑地閉著,像是在想什 麼,可是又更像是什麼都不想。我不知道 該說些什麼,過了半晌,他接著說,“要不 是你三伯父,我早就在四川和我侄子、和 你麼爸在一起,也不會在這個鬼島上被人 耍了。”父親的眼眶紅了,可是我沒敢上前 問他怎麼回事,因為上回我問他的時候, 他只說了聲,“小渾蛋,滾開。”
第二天早上,我在垃圾箱找一本不該 丟掉的筆記本的時候,意外地發現一張撕 碎了的老照片。我好奇地把它拼了起來, 原來是張學士照,黑白的,照片的色澤非 常熟悉,就如同母親高中時留著赫本頭的 那張一樣。不,應該說更黃一些。我翻過背 面,有著蒼遒的鋼筆字跡,以簡體字寫著:
“四叔留念,侄道榮敬上。”
※ ※ ※
父親在台灣的幾十年一直嘗試著和在 大陸的親人聯絡。頭先的二、三十年自然 是徒勞無功,一直等到鄧小平開放之後, 他才輾轉從在美國的舅舅那兒和大陸聯系 上了。先是他弟弟,我們管他叫麼爸。聽說 他向父親要了很多錢,起初因為海外關系 被關在牛棚,吃了不少苦,後來又因為海 外關系當上了當地的人民政協副主席。接 著,父親和他年歲差不多的侄子聯絡上了, 從他侄子那兒,才知道我三伯父在文革期 間因為胃疾而死了。三伯父生前的最後一 個決定就是把女兒嫁給了一個隨軍入川的 共產黨員,也因此,父親的侄女才免於文 革的迫害。當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再配 合三伯父鼓勵和幫助父親就讀海軍官校的 故事,我不得不佩服三伯父的眼光。
在我看來,父親的生命除了麻將之外, 就是等著不知道多久才可以等到的家書, 他就是等著家裡的人來信告訴他,回家的 時候到了。記得那是八十年代末,父親臨 時在台灣住了三十多年之後,不知道從那 兒聽說台灣快完,就堅持要把我住了一輩 子的公寓房賣掉。我當時已經是個大學生 了,“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但 是我對這個家卻連個發言權也談不上。父 親常常鼓勵我多找些同學到家裡玩玩,但 等到他覺得時候到了,他該回老家、該把 我們的家賣掉的時候,這些就都不提了。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這個家也滿足了我不 少虛榮心。有段時間父母和姐姐都不在家, 所以只有我一個人住著,有個同學到家裡 來,還開玩笑地警告我,別住這麼大的房 子,當心被鬼抓走。我當然沒被他的話嚇 到,反而因此高興了好幾天。這倒也是,要 不是別人的評論和後來租房子的經驗,我 還真不知道在台北市能住上四十多坪的公 寓,還稱得上是幸運的事。不過這些後來 都成了過往雲煙了。我們把房子賣了,就 隨便在對面的國民住宅裡租了間房,差不 多只有原來的一半大,因此該賣的就都賣 了,不能賣的也都給人了。反正父親的意 思是再過四年就移民美國,這四年就將就 點住著。父親年歲比我大上三、四十,但似 乎比我還不明白,人生能有多少個四年。 新屋的房東不準有寵物,所以我只有把Happy 送走。這個家只有我可以把Happy馴得服 服帖貼地。小時候有一次母親要替我蓋被, 它馬上驚醒,對著母親張牙舞爪。對此,母 親是厭惡、嫉妒、讚美、又覺得好笑。不過 這回Happy卻連我也不聽了,就在他的新 主人來接它的時候,他突然從我的懷裡跳 走,奮不顧身地往街口沖。我沒法,第一次 不是快樂淘氣地追著它跑,在躲過幾輛車 之後,總算把它制服、送上計程車了。Happy 手伏在關緊了的車窗,焦慮失望地盯著我。 上天沒有賦予動物流淚的能力,我那時才 知道,這是他對人類的恩賜。而父親只在 巷子口看著我尷尬地、身不由己地把Happy 捉上了計程車,事後才說,
“我老早就告訴你把它扔掉,你看你在 街上捉它多危險!”
送完了Happy,接著就要把家騰空。 我再也沒什麼力氣負責這項任務,父親又 剛好不在,所以一切大大小小的事都得由 母親處理。平常羸弱的母親這時卻顯得堅 強了。也許對他而言,搬個家根本是件小 事吧。整個過程他不多說話,只有在接近 尾聲的時候像是發表一份大膽的評論,“ 總比在大陸逃難的時候強多了吧。”等到 把家搬完了,母親鬆了口氣,彷佛也是完 成了一樁大事,但我卻彷佛意識到另外一 種前所未有的感覺油然開始。趁著新屋主 還沒搬進來的前一天晚上,我偷偷地潛入 了這個又屬於我的家、又不像我的家的地 方。大概是住在同一間公寓裡一輩子,對 空間的感覺已經麻木了,我頓然體驗到這 間公寓是不著邊際地大,大到我不知道應 該在什麼角落立足。牆上的壁燈本來就不 亮,此刻照著空盪盪的屋子就更顯得晦暗 無力了。印象中,屋子裡總是有些東西的, 所以此刻我第一次體會到了空的力量,輕 飄飄地,但卻難以承受,我實在受不了地 自己一個人嚎啕大哭了起來,尖叫著,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要讓我沒有 家?”
“現在飯廳的空間太小了,到時候把飯 廳和廚房打通,整個空間就顯得大多了。” 我突然聽到一番討論聲接在一陣跳躍輕快 的腳步聲之後,我知道是他們來了,趕緊 吞嚥了最後一把淚水,腆地從他們的身 邊擦過。雖然我知道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 有機會進入這個本來屬於我的空間,但還 是慚愧地不敢往裡頭多望一眼,就匆匆地 把門帶上了。我知道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 男子是不應該這麼樣失態,所以從那次起, 我就再也哭不出來了。
房子賣了之後,不知道是什麼怪異的 力量讓我沒事就注意“吉屋出售”的招牌, 雖然我不是買主,也怕別人知道我現在是 沒有家的人。做了這種無意義的事大約兩 個月左右的時間,台北的房價漲了十倍, 我才死了這條心。
搬完了家,開始了新的生活,台灣的社 會也開始了新的氣象。一直認定自己是知 識分子、還在念大學的我,不時地閱讀報 紙,一會兒蔣經國說,“不接觸、不談判、 不妥協,”後來又換著說,“時代在變,環 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一會兒又傳說蔣經 國病危,最後,終於開放到大陸探親了。我 思索著這一連串政治局勢的變化,又習慣 性地預估開放探親對台灣可能造成的影響, 也同時想著自己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做些什 麼。正在我看著報紙想著問題的時候,突 然一陣驚怖的敲門聲,
“快點!快點!”父親焦急地喊叫著,像 是忙著要去做什麼事,可是又像是找不到 件實實在在的事做。
“怎麼了?”我也緊張地問。
“國民黨準我們回大陸了!”
“那好啊,你就可以去大陸瞧瞧了。”
父親看了我一眼,似乎沒聽清楚我說 些什麼,繼續說,“我要去你媽的抽屜把存 摺找出來。我幹了一輩子,總不會連二十 萬都沒有吧。”
“你要那麼多錢幹什麼?”只要父親手 上有錢,他總會盡快地把它花掉,即使打 麻將輸掉都行。
“幹什麼?!我要帶回大陸!”
“你去大陸觀光需要二十萬台幣嗎?” 我有點奈不住性了。
“你渾蛋!”父親讓我吃了一驚,“這些 錢是我賺的,我為什麼不能花?”
“你能不能用點大腦做這件事?你難道 不知道我們家缺錢嗎?”我頂了回去。其實 我早就想要這麼做了,因為我慢慢發現父 親和我的關系,親情越來越淡,剩下來的 就是“力”了。過去年紀小,力氣也小,也 不想當個不孝子,所以只有在他面前唯唯 諾諾,但現在家也沒了,什麼也沒了,要打 架也絕對不輸他,所以膽子就大了起來。
“你想要阻止我,我就殺了你。”父親 的話,和講話時兇狠的表情在別人看來一 定會嚇壞了。
“你敢!”母親突然沖出來岔到我們中 間。父親用他那曾經是軍人的手臂往母親 的肩膀一扯,母親沒防著這一層,摔倒在 地,卡在飯桌下零亂的桌腳之間了。
“我告訴你,不要以為你有母親替你撐 腰,你就不必怕我了!”父親瞠著眼,嘴角 顫抖地說。
“我跟你拼了!”母親從桌角間掙紮了 出來,用手肘撐了下身體,就在地上往父 親的腳撲去。父親就像座山一般,一動也 不動,很快地把母親甩開以後,就順手拿 起擺在桌上的不鏽鋼茶壺,往我的頭上砸 下。我什麼念頭也沒有,像是幹一件司空 見慣的事一般地用手臂擋住他,接著就把 他抱緊,讓他一動也不能動。等到父親冷 靜了些,我才鬆開手說,
“你要回大陸你就回去,我也不稀罕你 跟我在一起,更不稀罕你的錢!”
父親在地上還爬不起來,看著天花板, 眼眶逐漸地紅了,
“你知道人生最慘的是什麼嗎?”父親 問我,我撇過頭看著窗外的天空,他接著 說,“妻離子散。”
※ ※ ※
“各位旅客,歡迎您乘坐中國西南航空 第麼麼七四號航班,從香港直飛重慶,機 上有五名乘務員為您服務。。。”我沒想到 回大陸是這麼容易的事。陳懷生為此犧牲 了生命,有人為此犧牲了青春。入境櫃台 上幾個穿著綠色制服,像是軍人又不是軍 人的官員看著我的藍色護照,明顯地和他 們習慣見到的港澳台胞証長得不太一樣。 他們用我十分熟悉但永遠也沒聽懂的四川 話、交頭接耳地不知在商量些什麼。大概 即使改革開放已經行之有年,但這些曾經 為社會主義祖國把關、嚴防某些人回大陸 的衛士們,似乎搞不懂我為什麼要從太平 洋的另一端,飛到中國大陸的西南內地。
“美國人。”這是我唯一聽得懂的三個 字,是其中的頭教導屬下,我藏在膚色底 下真實的身份。不久,承辦的官員沒有表 情地望著我,恨不得多看我一眼,四、五秒 鐘的時間,讓我局促不安。“砰!”那官員 在護照上蓋了入境許可,我到了中國。
我不太敢往接機的地方看,只顧著轉 動行李的輪軸整齊劃一地輪唱著,迎接一 袋又一袋、永無止境、從他鄉遞來的包裹。 等到行李領到了,我往入境的大門走去, 心情開始緊張了。我邊走邊找父親的蹤跡, 但等候的人群裡沒有一個我熟悉的面孔。 等到我接近了人群,才看到一個牌子,大 大地寫著我的名字,我趕緊趨向前去。
“您好,我是李治平,您是…?”舉牌的 是個瘦削的中年男子。
“治平,我是你大堂兄啊。”他激動地 握著我的手,一一將來接機的人介紹了一 遍。
“四叔近來身體不好,要不是醫生特別 警告他不能離開家亂跑,他一定會親自來 接你。他還告訴我們你的身高、體重…嗯, 相信你一定比以前瘦了些。”堂兄稍稍地 看了我一眼,繼續說下去,“他還特別交代 我們你的頭發梳成什麼樣子,在左邊分叉, 然後噴上厚厚的發膠,讓人感覺頭發油撲 撲地、給人很有精神的樣子。我們都笑他, 那有人八年頭發都不變的,呵呵。”
“父親在這兒一切都還好嗎?”我不由 自主地問道。
堂兄向我解釋了一下父親回大陸以後 的狀況,“四叔基本上都還好,只是猛吃 辣椒,勸都勸不聽,他說台灣的辣椒不夠 辣,吃得不過癮。
“你不曉得,有一回可能是辣椒吃多了, 他突然喊著胸口疼,我們趕緊帶他進醫院, 還不到醫院的時候就暈了過去,把我們給 急死了。我們告訴醫生,你爸爸是台胞,在 這兒沒有家,醫生才緊急處理。還好,過 了大概四十多分鐘醒了過來,你堂姐看到 他醒了,高興得都哭出來了。
“你知不知道他醒來第一句話是什麼?” 堂哥問,我搖了搖頭,他接著說,“他就問 我們,‘我剛才是不是死了?’我們就笑他, 要是死了,現在還會說話嗎?
“不過你父親很堅持,他說他一定是死 過了。他說他迷迷糊糊地看到了你和你姐 姐,好像就在面前,他想去握住你們的手, 可是怎麼都摸不著。沒多久,他還來不及 和你們說話,你們就不見了,也不知道你 們在哪裡。”
我們一路上聊著,四十多分鐘的路,彷 佛十分鐘就走完了。到家了,父親已經和 其他親戚站在門口迎接。他看到是我們到 了,主動走上前來。那會兒重慶的天氣陰 沉沉地,但是父親還是戴著一副褐色的太 陽眼鏡。大大的眼鏡遮住父親的臉,讓我 幾乎想不起來父親八年前的模樣。從前父 親的牌友都稱讚他的頭發,即使上了歲數, 還是那麼烏黑。但現在的頭發卻在鬢角顯 出絲絲的白花了。不過頭發整整齊齊,一 看就知道是剛剪過的樣子。所以雖然泛白, 他的頭發仍然是父親臉上唯一讓我可以找 到他昔日風採的剩餘物。父親的右手握著 根拐杖,不自由主地顫抖著。一位大約四 十多歲的女子站在他的左邊,扶著手,不 時地注意父親的步伐。也許因為父親知道 有人扶著他吧,縱然他的步伐顯得顛撲, 他一點也不低頭,直通通地朝著我走來。 他看到我只是微微地笑,從頭到尾把我打 量了一遍。而我透過鏡片看著父親的眼睛, 一種在我生命記憶中從沒有經驗過的慈祥 感動了我。我流下了八年來從來不肯輕易 釋放的眼淚,生疏地喊了一聲,“爸爸!”
晚餐桌上擺著生魚片、鐵板鱈魚、酥炸 生豪、、、一些我以為在四川內地不可能 吃到的佳肴全在桌上了。
“三個月以前你爸爸聽說你要來就吩 咐我把菜準備好,還親自開菜單,全是你 在台灣愛吃的菜。我就說嘛,魚要當天買 的才新鮮,他就天天嘮叨。”其中一位親戚 撅著嘴,而父親則在一旁像小孩子般地輕 輕地笑著。
“還有五糧液,三個月以前就買好了。 你父親還和我們辯,說菜不能先買,酒總 可以先準備好吧。”另一位親戚好心地關 懷著,“你們在美國吃不吃得到五糧液?我 們想喝一口,但誰敢把酒瓶打開?”大夥兒 聽到這兒都笑了。
“明天還有節目,”父親開口了,“我們 一塊兒到朝天門!”
“朝天門”,這個彷佛聽過、但卻一點 也不熟悉的地方,不知有什麼特殊。我們 的車子沿著江邊在山路蜿延,頓然間,江 面豁然開朗,“嗚…嗚…”惟恐不驚動天地 的汽笛聲讓我明白,朝天門是個熱熱鬧鬧 的碼頭。
“抗戰勝利之後,你三伯父就送我到這 裡,唷,就是你現在站的位置,”父親心平 氣和地說著。我感覺到站穩了腳跟,仔仔 細細地向遠方望去,嘉陵江從左手邊向著 長江、也是夕陽的方向,沒有聲音、深長細 勻地流著。眼前就是長江,順著下去,不就 是到了東海,然後就可以接上台灣、美國 了嗎?
父親語調一轉,接著說,“哎呀,你不 知道,人山人海!”父親的四川腔調把這四 個字說得鏗鏘有力,似乎要奮力把聲音蓋 過萬頭鑽動的人群。
“為什麼?”我好奇地問。
“大家都趕著要回家呀!”父親大概沒 有意識到他那“回家”二字說得清楚地讓 我覺得陌生,所以還沒等我反應過來,就 繼續說,“那時抗戰剛剛勝利,碼頭每天都 擠滿了人,有些人還邊擠邊喊著,‘不讓老 子回去,我就跟你拼了’。我那時候要跟著 官校師生到南京開學,你三伯父催著我, 我也緊張得很,既怕脫離了部隊,又怕拎 在身上的那口大皮箱被人扒走。其實那口 皮箱除了幾件簡短的內衣褲之外,就只有 前一天夜裡我的侄兒送給我的筆記本。我 那時連張船票都沒有,三伯父就同大副說 了些話,讓我上了船,但是只能在甲板,不 能讓船上的軍官發現,所以整個行程我都 是躲躲藏藏地,不知道該在什麼地方安身。” 父親又開始發揮他說故事的本領,“你三 伯父和船上的人談好了以後,我們就站在 你現在站的位置,三伯父握著我的手,告 訴我一有什麼事一定要寫信回來。唉,我 第一封寄回家的信,已經是三十年以後的 事了。”
“當時我的侄兒也在碼頭上,他站在你 三伯父的身後,像是在躲我的樣子,一會 兒問你三伯父是不是該買些清涼油讓我帶 著,一會兒又吆喝小販買些解渴的,一會 兒又著急地望著停在江邊的船。”
父親稍微停頓了一下,“那時要是跟不 上往南京開的船,情況就不一樣了
……”
父親痴痴地望著江的另外一邊,不動、 也不作聲。堂兄攙著我的手,對我說,“治 平,你不曉得四叔知道你來有多高興。昨 天你醉倒以後,他和我們還繼續吃飯聊天。 他平常吃完飯都侃個沒完沒了,但昨天卻 不多說話,只有在嘴角保持著微笑,我們 趁機開他的玩笑,他就像個剛討媳婦的新 郎官一樣害羞,想還嘴,但卻又不知道要 怎麼說。”
“這是要蓋啥子?”父親指著在碼頭右 方、一片大約有社區壘球場那麼大、施工 中的大樓問堂兄。
“聽說是個大型購物中心。”
“這些在我離開的時候都沒有的。”父 親評論著。
堂兄看到父親又停止了說話,就轉過 頭來,“當初要沒有你三伯父逼著你父親 讀海軍官校,他就沒辦法到台灣、也就沒 有你了。”堂兄無意識地重復父親過去經 常講的話。
“你三伯父也是從這兒坐船到南京念 中央大學的。那時候的大學生不得了。” 堂兄雖然看來謙虛沉穩,但說這話的當口 還是掩蓋不住驕傲的神色。
“你三伯父回到重慶,在當地還是個新 聞。他人長得高高瘦瘦的,非常英俊,好多 女孩子追他呢。唉,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紅 衛兵造他的反,他受不了一連串的打擊, 得胃病去世了。
“我們弟兄三個人,因為成份的關系, 都沒機會好好念書,所以看到你拿到博士、 在美國當大學教授,實在覺得非常安慰。” 堂兄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我也常常告 訴我女兒,要好好念書,學習他的祖父還 有小叔你,為我們李家爭光。”
“嗚…嗚……”一陣汽笛聲吸引了堂兄的 注意力。他往停在江心的客船望去,也和 父親一樣沉默了。過了半晌,他像是發現 了什麼似地從提包裡拿出了一張照片,我 習慣性地把照片翻到了背面,上頭有著十 分熟悉的字跡,寫著,
“治平留念:三伯父遺照,堂兄道榮敬 上。”
我再仔細一看,這不就是父親撕毀的 那張嗎?不對,眼前這張照片的眼睛似乎 有著更多歲月刻劃出的深沉。我提高照片, 對著嘉陵江和長江合圍成的那座小山上望 去,離山不遠處就是那艘客船,晃悠悠地、 一點也不在意客船上急著要回家的遊子, 反正是早是晚,總會到達目的地的。
“當初要保存這張照片並不容易,那些 紅衛兵要是看到我們家裡有張學士照,那 我們肯定會被鬥爭的,”堂兄慎重地說,“ 不過我還是不聽我愛人的勸告,私底下留 了兩張,一張在幾年前寄給了你父親,另 外就是這一張了。”
※ ※ ※
這張照片隨著我回到了美國,半夜裡, 我怎麼也睡不著,我告訴自己這不過是時 差的緣故。不管怎樣,我點起了桌燈,桌上 三伯父的照片還沒收起來。我望著他細致 的眼神,豐厚的嘴唇似乎想要開口告訴我 什麼,可能是另一段故事吧。我還沒等著 他說,也還來不及向他傾吐我心中從來沒 有向他人說過,但一直想要同他說的話, 突然一陣香味讓我分了心,像是從好遠好 遠的地方傳來,又彷佛是一種很久很久沒 聞過、但卻曾經那麼熟悉的味道。
“哎呀,不是賣蚵仔面線的歐巴桑推車 過來了嗎?”一個興奮而又幼嫩的聲音對 著樓下喊著。
“不,那是你父親愛吃的臭豆腐吧。” 三伯父無言地對我說。。。
第二天早上,我睜開眼睛,恍恍惚惚之 間,看到天花板上吊著的風扇,就像剛起 錨的船身後的槳一般,有力但卻緩慢地轉 動著。我側過頭來看著熟睡的妻子,搖著 他說,“咱們去吃臭豆腐吧。”
“拜托,你做給我吃,這是美國,不是 台灣。”翻個身,她又繼續睡了。
“噢,是啊,”我這才真正清醒,“當初 在台灣沒有認認真真地吃,把臭豆腐的味 道牢牢地記在心上,現在想吃都吃不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