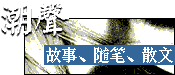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沈 方﹒
讀 書 雜 記
◆買書記趣
讀書的人當然喜買書。天長日久,日積月累 ,家裡難免搞得到處是書。不管 有用無用,書架越放越滿,越疊越高。無論到那 兒,在熙熙攘攘的鬧市、綠樹掩 映的城市一角、或者平靜安逸的小城鎮,能找到 一家書店,不管大小,無疑是一 塊世外桃源。早先的書店,沒有實行開架,要買書是一件 很吃力的事。遠遠地站在櫃台外 面,櫃台玻璃下陳列的書籍有限得可憐,不得不 伸長脖子張望書架上密密麻麻的 書脊,要翻翻哪本書得看營業員的臉色,換得多 了連自己都不好意思。現在的書 店都是開架,站在書架前一本一本地瀏覽,耽半 天也一眨眼過去了,簡直是一種 享受。很久以前,在鎮上的小書店裡,我看到兩 本新書,一本是《葉紫選集》, 一本是《草葉集選》。營業員沒讓翻閱,而我又 孤陋寡聞,不懂書的內容,結果 買了《葉紫選集》,那當然也是一本好書。但僅 有的一本《草葉集選》就這樣錯 過了。過了一段時間,知道是楚圖南翻譯的惠特 曼選集,心中十分後悔,況且又 不知道什麼地方有賣。後來打聽到,中學圖書館 買了這本書,我托當教師的朋友 去借出來。一年以後,朋友來要書,說不歸還書 ,圖書館規定要照價加倍賠償。 我實在愛不釋手,沒辦法只好照章辦理,賠了三 塊錢。這本書,我保存了很長時 間,直到買了《草葉集》全譯本,才把它送給了 一位同樣愛書的朋友。
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和福州路上的書店, 是我神往的地方。因為去上海的 機會不多,我還和南京東路新華書店建立了郵購 關系。第一次郵購,買了一本勃 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五分冊--法國 的浪漫派》。讀了一遍,內心有 一種充實而又得意的感覺,自以為跟那些文豪、 詩人近了一層,現在想來膚淺得 可笑。去上海出差了,急沖沖趕到南京東路新華 書店,象是去朝聖,尤其是二樓 的學術書苑真是一座大雅之堂。有一年,上海舉 辦第一屆上海書市,我和一位朋 友結伴前往,白天去上海展覽館看書,晚上住在 貴州路一家嘈雜的小旅館裡,用 不多的錢買了一些以為很稀罕的書,有《人論》 、《人心與人生》、《葉賽寧詩 選》、《雪萊詩選》、《彭斯詩抄》等等。回到 家裡,輕易不示於人,猶如武林 秘籍。
有機會去北京已是九十年代的事了,我幾乎 摸遍了東四一帶的書店,那真是 勝地,大都是著名出版社的讀者服務部。近年去 北京,東四那邊不去了,跑得多 的是三聯韜備圖書中心、風入鬆書店。在北京逛 書店,一般都有收獲,種類齊全, 新書及時,非其它城市能比。而且,北京的書店 還有不少冷門書、舊版書,這更 是其它地方不具備的。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 學主流》是1982年版,當初 我只買了第五分冊,1995年在琉璃廠配齊了 整套六冊。有趣的是,在琉璃廠 中國書店,竟然買到了杭州古舊書店1985年 影印版《湖州府志》。在書價上 漲的今天,無疑是價廉物美的幸事。
至於杭州,雖然近在只尺。以前反而去得不 多,這幾年,有了西湖六公園的 三聯書店,跑得勤一點,每逢去杭州開會、出差 ,少不了要去逛一逛。我還專程 找熟人,去三聯書店的書庫裡淘書。翠園的圖書 市場,過於繁雜,對零售生意店 家又不肯打折,去過一次之後,沒有再去。解放 路的新華書店,變化不小,也是 讀書人的好去處。另外,作家協會開在湖濱的現 代書店,雖然略嫌小一點,但也 不錯,每次去多多少少有所收獲。
文化出版是越來越發達了,書店也開了不少 。有一些小書店,雖然不顯眼, 但常常特色鮮明,能看出店主的經營思想。在廈 門中山路上,我發現了一家設在 二樓的書店,沒有堂皇的門面,臨街只有一個樓 梯口,上樓一看,好書琳琅滿目, 別有洞天。前一陣子,中央電視台《讀書時間》 節目介紹香港的書店業,好些書 店也是開設在二樓的。看來這是市場經濟時代的 普遍現象了。但不管怎樣,書店 多了,出書豐富了,買書方便了,總是讀書人的 福氣。怕就怕沒有太多的錢買書, 其實買書也是一門學問,不懂書的人,給他一萬 塊錢也買不來好書。愛書者家中 滿壁的書,不知是多少年來,化了多少時間,跑 了多少路,費了多少心血才經營 而成的。絕非是一朝一夕一蹴而成。這樣,藏書 當然比金錢更重要了。我常年訂 閱一份《文匯讀書周報》和《讀書》雜志,象股 市上的股民們看股票行情一樣去 讀。要買書不能不了解書評介紹和出版動態。漸 漸地,經驗豐富了,才能正確地 買書、讀書、藏書。
根據自己的愛好,我主要買三種書,第一是 急於想讀的書,第二是將來要讀 的書,第三是可能要讀的書。成套的書盡量少買 ,大部頭的書一般不買,流行的 書絕對不買。時常讀的書,可能還需要買兩本。 一本美國小說家卡佛的《你在聖 佛蘭西斯科幹什麼?》,我就買了兩本,一本放 在家中,一本拆成散頁隨身攜帶, 在工作、開會之余抽空閱讀。在忙碌的人生,偷 得片刻空閑讀讀書,這是最大的 樂趣,唯有讀書人才能享受。恐怕也是讀書人僅 有的自得其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