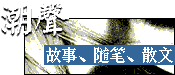秋夜枕邊閑讀,睡意漸濃之際,一首美國當代著名詩人威廉斯的《春日寡婦怨》吸引了我的注意。讀來使人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The Widow's Lament in Springtime | |
Sorrow is my own yard where the new grass flames as it has flamed often before but not with the cold fire that closes round me this year. thirty five years I lived with my husband. The plum tree is white today with masses of flowers. masses of flowers loaded the cherry branches and color some bushes yellow and some red but the grief in my heart is stronger than they for though they were my joy formerly, today i notice them and turned away forgetting. Today my son told me that in the meadows, at the edge of the heavy woods in the distance, he saw trees of white flowers. I feel that I would like to go there and fall into those flowers and sink into the marsh near them. |
我的庭院是哀愁 那兒初生的嫩草 依舊灼灼欲燃 像往常一般 可是今年卻以 冷冷的火燄包圍我。 我跟丈夫共度了 三十五年。 今天李樹一片白 滿樹累累的花朵。 累累的花朵 曾壓低櫻桃樹枝 而今替不少灌木叢染色 一些染紅 一些染黃 可是我心中的悲哀 比它們強烈 因為它們雖一度是我的歡娛 今天我向它們注目 轉頭卻將它們忘記。 今天兒子告訴我 在遠方 鬱鬱林木邊緣 青草地上 他看見 一棵棵白花樹。 我覺得非常想 去那裡 陷入花深處 沉入樹旁的沼澤裡。 |
如果把第一句反復默念幾遍,你是否會想起哪首中國古典詩詞?是不是歐陽修的《蝶戀花》中“庭院深深深幾許”的句子?都是春日、庭院,孤婦,懷舊,皆以哀怨庭院來開頭:
庭院深深深幾許?
楊柳堆煙,
帘幕無重數。
玉勒雕鞍遊冶處,
樓高不見章台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
門掩黃昏,
無計留春住。
淚眼問花花不語,
亂紅飛過秋千去。
用花、草、樹木來反映投射幽怨心情,是中國古詩詞的特點之一,也是這兩詩的共同之處。美國詩歌傳統中很少這種怨婦心態描述,威廉斯的前詩描寫的也不是怨婦而是寡婦。而且,同樣的空幽庭院,春草花木,在東西古今詩人筆下,展現出不同的色調。威詩中青草轉化成冷冷的火燄,雪白的梨花,紅黃相間的櫻桃樹,強烈的感情色彩和對比,表達了一個貴族寡婦懷念亡夫,心灰意懶的心態。而歐陽修的詞,則是典型的中國古代貴族婦女深閨寡居,感怨漂泊無定的男人,又無力掙脫封建枷鎖。特點是陰柔、纏綿、朦朧。比較一下威詩中嫩草灼灼燃燒著冷火,和歐陽修詞中楊柳成煙似帘幕重重,可以看出這種差別。
然而,威廉斯的這首《春日寡婦怨》雖然被幾乎所有的選集列為當代美國名詩經典,但它與美國,以致整個西方詩歌傳統有很大的區別,而且很少見到類似的作品。反而更接近中國古典幽怨詩詞傳統,讓人懷疑他這首詩可能受了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影響。粗略翻翻書,威廉斯果然寫有《致白居易之魂》等詩,証明他很早就讀過中國古典詩詞而且多受影響。威廉斯是當代美國影響力最大的詩人,其風格以口語為主,力求擺脫英國及歐洲傳統,重視可觸可感的事物而不寫抽象的思維。其詩語調親切,自由體短行,用字淺白自然且典雅,與現代主義詩人艱深復雜、寓意厚重相悖。這些特點,大概也是他能接受中國詩詞的原因之一。
從文化背景上來看,閨怨詩詞的條件是女子處於弱者的不利地位,受封建道德和體制約束,深閨便是她的一生。而男人卻可以漂移不定,遠走四方,多妻多妾。另一個特點,是這種閨怨大多是陰柔纏綿愛情,雖被棄或被忽略,仍愛意不減,渴望成為男人的真寵。這兩個特點,在西方文化中顯然不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那麼突出。可能是西方詩歌傳統中沒有‘閨怨詩’的文化原因。另外,西方文化審美比較直觀,東方審美強調朦朧,因之具體的懷念戀情表達也相應有較大差異。威廉斯和歐陽修這兩詩還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從男性的角度來揣摩、表現女性心理情感活動。威廉斯這首詩是為他母親而寫的。中國古典閨怨詩也多為男性代筆。當然還有李清照這樣的女詩人的傑出代表。而西方詩歌中,則看不到女詩人這種閨怨詩。也是中西詩歌傳統的一個不同之處。
概括地說,詩歌作為一種表達人類情感、思想的文學形式,在所表達的具體對象上,可以有很深的文化根源。不同文化所獨有的社會現象,可發展出相應的體裁和格式。另一方面,人類生活有基本的、共同的主題或環境,構成不同文化的共有基礎。只是由於思維方式,審美意向以及情感表達方式的不同,而形態各異。共同的主題或環境,使不同文化的交流成為可能。而各異的表達方式,構成了文化差異的多姿多彩。比如,同樣是寄幽思於庭院,草木,花卉,山水,便可以有威廉斯和歐陽修的不同風格。而對離別的相思,又是人類共同的情感。所以我們能夠理解,欣賞兩種不同的表達,比較其異同。
回到東西詩歌的主題和表達的異同上來,還可以舉出一個有趣的例子。膾炙人口的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裡,在開篇的第一章中有一首人人皆知的歌謠,它也是《紅樓夢》的主題,就是“好了歌”。表達人世無常,有生必有滅,功名福祿皆虛幻的觀念。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巧的是,愛爾蘭著名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葉芝也有一首異曲同工的名詩,《又怎樣》( "WHAT THEN?" ):
His chosen comrades thought at school
He must grow a famous man;
He thought the same and lived by rule,
All his twenties crammed with toil;
'What then?' sang Plato's ghost. 'What then?'
After certain years he won
Sufficient money for his need,
Friends that have been friends indeed;
'What then?' sang Plato's ghost. 'What then?'
All his happier dreams came true --
A small old house, wife, daughter, son,
Grounds where plum and caggage grew,
Poets and Wits about him drew;
'What then?' sang Plato's ghost. 'What then?'
'The work is done,' grown old he thought,
'According to my boyish plan;
Let the fools rage, I swerved in naught,
Something to perfection brought';
But louder sang that phost, 'What then?'
在校時,他的好友都認定
將來他必然成名;而他
也以此自許,按部去實行,
三十歲以前工作何辛勤。
“成名又怎樣?”柏拉圖的幽靈吟道
“成名之後又怎樣?”
他寫的一切都有人研究。
過了幾年,他就賺夠
充足的錢,供自己需求,
也贏得真像朋友的朋友。
“研究又怎樣?”柏拉圖的幽靈吟道。
“研究之後又怎樣?”
他一切的美夢完全實現:
一座小古屋,妻子,兒女,
長李樹和橄欖的幾畝田;
詩人名士都圍在他身邊。
“實現又怎樣?”柏拉圖的幽靈吟道。
“實現之後又怎樣?”
“壯志已遂,”晚年他回憶,
“且按少年時的預想;
讓愚人去發狂,我從不遊移,
且美滿地完成了一件東西。”
但柏拉圖的幽靈癒吟癒激越:
“美滿之後又怎樣?”
這首詩借用柏拉圖的觀念,認為自然世界不過是理念的影子,人的建樹沒有什麼了不起。比較一下《好了歌》,可以看出這兩者有相當共同的主題,即芸芸眾生所為之追求不止的東西,都是毫無意義的。葉芝的詩也分四節。第一節寫功名,第二節寫名利,第三節寫家產子女,第四節寫老來的成就感。雖然不完全與《好了歌》的四節嚴格合拍,但主題基本一致,所寄予的事物也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其主題的文化底蘊。一個是道家無常思想,一個是柏拉圖的虛無哲學。拋開這些不同,仔細吟誦賞析這兩首來自完全不同文化的經典詩歌,你會發現人類深層心理上的共同感念、疑惑、思考。生死、功名、財富、家庭、子女等一切人類基本的現象,永遠是人類無法回避的思考對象,也是藝術所表達的基本對象。文化的不同,在於其表達方式的差異。
而從藝術欣賞的角度來講,這種表達方式的差異,卻往往具有決定審美取向的意義。在一種特定語言文化中長大的人,該種文化通過種種直接間接的途徑積澱在一個人的思維方式、情感過程,和審美觀念之中,決定了其藝術審美定向。不言而喻,一個在中國文化中熏陶長大的人,讀歐陽修的詞,與讀威廉斯的詩,會有截然不同的審美情趣感受。中國古詞那種格律與韻律帶來的心理生理審美反映,是讀英文詩歌所難以有的。反之也一樣。由此推論,從小在雙語平衡的環境中長大受教育的人,這種差異可能會小些?不過,很難想象這種完全‘平衡’的雙語環境。
一個間接跨越這種特定文化審美局限的方法,是對比欣賞兩種語言的同一對象表達。就是說,讀中國古典詩詞及其英文譯作,以及英文詩歌的漢語翻譯。這並不能‘克服’那種審美上的文化差異感,但卻可以提供一個機會去理解、體驗這種差異的本質和其具體現象。比如,如果你覺得讀英文詩歌沒有讀中文詩詞那種美感,或者英文翻譯遠沒有原文的韻味,你可以讀一下英文原詩的漢語譯作,從另一個方面去體驗一下漢語譯文與英文原文的差異。這樣會對漢英詩歌審美的差異有一個更深切的體會,也有助於理解與欣賞不同文化的詩歌,以及其他藝術表達形式。當然,審美情趣是可以培養的。對不同文化詩歌的欣賞能力,也可以通過提高該語言文化的修養,和系統學習該文化的詩歌傳統來培養。不過,這種對‘外來文化’的審美欣賞,比較難以達到本族文化審美的層次。
前文中,兩首英文詩都給出了中文譯文。現在不妨讀讀所引中文詩詞的英文譯文。可惜的是,手頭沒有歐陽修《蝶戀花》的英譯。不過,在流行的英譯中國古詩詞版本中,可見到歐陽修的類似作品。選一首《阮郎歸》的英譯。至於《好了歌》,常見的有數個英譯版本,楊憲義夫婦的譯本比較忠實於原意,另一個由王池成(音譯)翻譯的版本比較有韻味。一並列出,細比較之下,會有不少啟發,不過不在這裡討論之列。如前所述,列出漢文詩詞的英文譯本,意在提供一個體會中西詩歌異同的途徑。
| 歐陽修☉阮郎歸 | Green Jade Plum Trees In Spring |
|
南園春半踏青時 風和聞馬嘶 青梅如豆柳如眉 日長蝴蝶飛 花露重 草煙低 人家帘幕垂 秋千慵困解羅衣 畫樑雙燕棲 |
Spring comes early to the gardens Of the South, with dancing flowers. The gentle breeze carries the sound Of horses whinnying. The blue Green plums are already as large As beans. The willow leaves are long, Eyebrows. Butterflies whirl in the Long sunlight. In the evening the Mist lies heavy on the flowers. The grass is covered with dew. Girls in their transperent dresses, Indolent and lascivious, Lounge in their hammocks. Swallows, two By two, nest under the painted caves. |
這種譯文更有些接近所謂創意英譯。翻譯並不完全照扣原文,不太受學院派翻譯的框框限制,而更是譯者對原文理解基礎上的一種再創造。多由詩人兼詩歌翻譯家所作。
《好了歌》兩種譯文:
Yang Hsien-Yi & Cladys Yang 的版本: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to riches and rank each aspires;
The great ones of old, where are they now?
Their graves are a mass of briars.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silver and gold they prize
And grub for money all their lives
Till death seals up their eyes.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dote on the wives they've wed,
Who swear to love their husband evermore
But remarry as soon as he's dead.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Yet with getting sons won't have done.
Although fond parents are legion,
Who ever saw a really filial son?"
Chi-Chen Wang 的譯文:
We all envy the immortals because they are free,
But fame and fortune we cannot forget.
Where are the ministers and general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Under neglected graves overgrown with weeds.
We all envy the immortals because they are free,
But gold and silver we cannot forget.
All our lives we save and hoard and wish for more,
When suddenly our eyes are forever closed.
We all envy the immortals because they are free,
But our precious wives we cannot forget.
They speak of love and constancy while we live,
But marry again soon enough after we are dead.
We all envy the immortals because they are free,
But our sons and grandsons we cannot forget.
Many there are, of doting parents, from ancient times-
But how few of the sons are filial and obedient!
《好了歌》翻譯的一大難題是“好”和“了”。因為在隨後的對話中,跛足道人闡釋了‘好’和‘了’,點明‘好’和‘了’是這首歌謠的主題。與歌謠裡的‘好’和‘了’遙相呼應。如果在歌謠的翻譯中沒有給出相應的詞,便會有與後面的解說脫節之感。從這個角度來講,後一種翻譯取“ FREE ”和“ FORGET ”作為“好”和“了”的對應語,起碼從格式上與原文對應得好些。有興趣者可以參看兩種譯本後面的對話。
不同文化文學藝術欣賞的困難,在詩歌中尤甚。詩歌是一種凝聚了特定文化精髓的高度凝練的語言藝術表達。不同文化詩歌又有其特定的格律。這種內容的凝練和形式的專門化,使得跨文化的審美欣賞較為困難。不過,人類文化所具有的共同主題與環境,使我們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越過這種隔膜,去領會,欣賞人類文化的多元之美。
作者注:
The Widow's Lament in Springtime 的譯者是鐘玲。
What then? 的譯文選自余光中的《英美現代詩選》
歐陽修《阮郎歸》英譯取自《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by Kenneth Rexroth
(本文為秋夜不眠之胡思亂想,不是學術探討。謬誤之處,請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