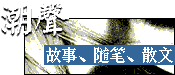這話最初是從一本圍棋雜志上看到的。某位日本棋手震懾於當年聶衛平對東瀛棋壇的橫掃,潛心拜讀“三耳先生”自傳《我的圍棋之路》,試圖為日本人總結出失敗之由。他的結論是:聶衛平棋藝的境界與他當年在北大荒那段風高雪惡的蹉跎歲月有關,較之尋常生活優渥的日本棋手,聶君遂別有一股“生命的厚味”蘊蓄其中。
“厚味”,這是一個圍棋術語。與“尖”、“飛”、“雙”等著手性術語不同,它屬於那種戰術性術語,然而又比“立二拆三”或“厚勢不圍”之類戰術性術語更能體現一位棋手的戰略素養。比如初入棋枰者多半知道“金角銀邊草肚皮”的棋理,待到棋藝稍上層樓,就會琢磨“高手在腹”的道理了。這“高手在腹”,籠統地說就是指圍棋的大局觀。高手的棋,即使如馬曉春這類常被人目為輕靈飄忽的棋,也總有某種頗難一言道盡的“厚味”(非指厚勢)在裡面,使你無法率爾施以重拳。追求效率的天才棋士吳清源前輩也曾被人(當然是那些失敗者)譏刺為“品格不高”,因為吳先生的棋形乍看上去“總覺得薄”,只有高明誠懇如武宮正樹者才願坦然承認:這正是吳先生力量之所在,因為吳清源的所謂薄形中總有一股“厚味”蓄勢其裡,它不僅可以成功地化解對手的攻擊,也能反過來始終給對方施加無形的壓力。可見,有此一帖厚味,不僅標志著棋藝的拓展,一般說來也使弈道脫離了區區棋理的拘囿,從而進入更廣闊的生命空間。也正因此,這份滋味便只有弈道漸入佳境者方能咀嚼品評,就像只有對生命有著淳厚理解的周作人先生才深諳苦茶妙趣一樣。
曾聽說某老丈為女兒挑女婿,總是擺下一盤棋,以觀察對方的忍耐力、明智心和貪婪欲,換言之,考較對方的生命形態。老丈是明哲的,他借此果然為女兒們找到了如意郎君。你想了解一個人,和他下盤棋最是簡便,通常也最不會瞧花眼,對此我深信不疑。我第一次產生這個認識還是在九年前,那次是看人下中國象棋,一位我相當尊重的知識分子正與人在楚河漢界上廝殺。我素來認為這位先生是個對些微小事相當放得開的豁達君子,雖然一位這樣的君子未必下一手好棋本來也無可奇怪。果然,他的棋勢相當不妙,我站在一邊,盡管也觀棋不語地冒充雅人,但心下卻覺得這盤棋已至山窮水盡之境,而唯一的轉機只可能出現在下一盤上。對方車馬炮三軍合圍,正以大兵壓境之勢對他困守在單車獨士象危城中的老帥欲行非禮。棋早已無可觀瞻,我便轉而欣賞起弈人來了。只見他眉頭緊鎖,以一種摻合了沮喪與惱怒的頑強兀自不依不饒地呆看著棋盤,頻頻長考。於是我看到了不輕易言敗的極端表現,只是,當所有人都能憑藉不會出錯的常識看出此際的棋勢只可能是“貓捉老鼠”時,他單方面認定的“老鼠玩大象”還有多少意義?必要的頑強當然也是生命厚味的內涵之一,但它與不識時務、不知進退的執拗顯然屬兩個概念,將些微挫折看得過於滯重,只能表示出生命意味的脆弱和輕薄。這裡,正是這位先生在棋盤上體現出的那份超出必要的頑強,讓我窺出其生命的薄形。若繼續圍棋世界的比喻,這裡的生命形狀還有愚形之感。
如果說圍棋的厚味因圍棋本身的競技性而較難讓不明弈理者感到美感和說服力,我們且試著如那位日本棋手那樣,把話題延伸到人生層面上。正如圍棋中的厚味總是相對於薄形而言,生命的厚味也便與輕倩浮躁的人生形態相對應。具有此厚味者,大抵比常人更多地體驗到生命的嚴苛,隱忍力也較常人為優,因而言談舉止間總讓人感到一股從容,一份淡雅,一種機智,一帖瀟洒。這樣的厚味當能讓人泰山崩於前而不驚,從而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墮志,以一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磊落豪邁應付紛擾繁復的人間世。與之相對的另一幹人,由於對生命意義不甚了了,是以也就無法給人生提煉出任何有意味的生命情境。他們的人生大棋總是走得險危脆薄,或不事修煉,盲目進取,或謹小慎微,專意忍讓,致使前程到處布滿脆生生的陷阱。小失意必為大煩惱,淺得志輒成大成就,舉手投足每如影戲中人,徒見影像斑駁,全無內蘊深藏。因此,“生命的厚味”便可視為人生的勢能,它並不像圍棋中的厚勢那樣常有致人死地之效,事實上它並不以攻擊性見長,但卻能有效地擢升個體生命的生存境界;作為泛泛生命的人格背景,它甚至不妨是謙退的,然而又永遠不會把自己的生命之路逼向懸崖。一種厚味的人生總是體現出從容淡遠之境,它不以看破紅塵自居,卻又長著一雙睿智的紅塵之眼。它是真正男子漢的人生,也是通體洋溢著母愛的人生,說厚味而不說厚實,正在於後者是憨厚的東西,前者卻與某種生命藝術有所沾丐。
我曾用心觀摩過宋張擇端名作《清明上河圖》,在經常性地對畫家的宏偉構思、非凡功力深表欽敬之余,有時也不無困惑。湊近細看那林林總總八百多位畫中人的舉止聲貌,發現其中竟十有八九似為遊手好閑的無賴小民,個別還易使人想起《水滸》裡那個纏著青面獸楊志的潑皮牛二。正如巴爾紮克的偉大不在於為後人塑造了多少慷慨激昂之士一樣,張擇端的不凡之處也同樣不在於他為我們留下多少值得圈點的偉人,希冀以人物的偉大來折射作者的不同凡響,只能是一種具有原始拜物教孑遺的幼稚幻想。作為一名現實主義畫家,張擇端不妨只以準確忠實地反映出汴京眾生相為己任,而不必另有他求。於是,我們便相當難能地看到了這樣一群比《東京夢華錄》或宋徽宗題簽過的所有文人畫都更為真實的祖先:他們或無所事事地在城根袒腹嚼舌,或呆頭呆腦地在橋頭傻看風景,或旁若無人地在橋下交通要道處呼朋引類,或愣頭青十足地在鐵匠舖裡把弓拽得滿滿……對畫作諦視良久,我們儼然能聽到畫中人的擾攘喧嘩聲,如果換一個時空,這類喧嘩在我們兇險的文革時期,似乎也是司空見慣的。我極為認真地試圖在其中找到某位我們在傳統文人畫中所熟悉的高人逸士形象,一位吹簫書生,或某個垂釣老叟,然而歸於徒勞。我只在畫面一角窺見一獨自在屋宇內作沉思狀的中年人,但他那雙投向窗外的眼睛到底是在為形而上問題苦惱還是為形而下的柴米油鹽而勞心,則殊費疑猜。與尋常中國文人畫的區別在於,張擇端的藝術興趣系乎世相人情,而那些飽讀詩書的文人型畫家則總忘不了在作品裡寄托一己的抱負和感慨。由於我無比佩服畫家的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及高超的描摹人物才能,我的失望也就更趨沉重。從《清明上河圖》中固然可以看出北宋國都汴京的極度繁華,卻仿佛也能窺得大宋朝最終亡於異族之手的底裡消息。一群只有十分鐘未來的市民,其生命形態之脆薄,較之“隔江猶唱後庭花”的商女,似有過之而無不及。後者至少還在從事--即使是被迫地從事--與藝術相關的活動。
生命的厚味,看來不完全是個人的修養,它還關系到民族的素養。有時我會不由自主地想到顧準先生,他完全具備魯迅先生推崇的中國人的脊樑,然而卻又很難作為中國人的代表。正如國民中偶然出現幾位穆鐵柱般,我們無法因此得出中國人的身高都在日長夜大一樣。
(1995.2)■〔寄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