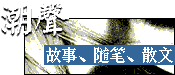歌唱讓我如此接近大地和勤勞質朴的人民,在漫長的路途中,讓我去關照和自潔自己的心靈,去實踐生命中美好的幻想。
我出生在粵北山區一個名叫翁城的古鎮上。我的父母生下了五個小孩,我居於中間,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正因為這樣,我的整個童年和少年都在嬉戲和幻想中度過。我的母親是供銷社食堂的服務員,是一個勤勞樂觀、善於理家、只會寫自己名字的人。父親是郵電局社線員,由於父親的工作是修理鄉村的電話線路,所以我家是小鎮上唯一一個擁有電話的家庭。每當暴風雨來臨的深夜,家裡的電話鈴總是急劇地響起,然後父親就會穿上雨衣消失在雷雨中,有時候會幾天不回家,聽媽媽說,是到深山裡檢修線路去了。還好,父親這一輩子除了從電線桿子上摔下來的一次重傷外,沒有發生過別的意外。童年時,郵局是我最大的樂園。在那些從各地寄來的信件中,我最早發現,除了小鎮以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我當時的念頭就是希望將來有一天象這些信件一樣從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個地方。
時間到了1978年忽然有一個遠房的親戚從香港回來,從此家裡有了一台小三洋錄音機,還有許多香港的磁帶。我聽得最多的是許冠傑的歌曲,那時候香港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我也從收音機裡聽到了香港的電台以及後來的美國之音。也就是說我的整個少年時代都在這種資本主義傳媒的熏陶下成長,對這一切更是如痴如醉,也變得不愛上學。直到初中,唯一讓我感興趣的學科是物理,尤其是電學。在那個時候看得最多的書是《無線電》。在父親的支持下,到了初三我已經可以維修收音機和錄音機,而且還能到把收音機的靈敏度提高到極限,以至於白天也能收到香港的電台。從此學校對我再也沒有任何吸引力,我便開始與比我大的人來往。這時候結識了一個從縣城調來的電影院青年美工,從他那裡第一次接觸吉它。直到最後棄學,在小鎮上開了一個電器維修店。那一年我剛滿十六歲。
在少年時對我產生較大影響的是我姐姐。她是小鎮上第一個女大學生。姐姐從小就是一個體育健兒,小學五年級就離開了家鄉。她經常到各地進行比賽,每次回來都會給我們講各地的見聞。並時時鼓勵我努力上學,能從小鎮上走出去。少年時的我還有一個愛好就是畫畫。姐姐一直想使我成為一個畫家,在她考上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系以後,每次回家都給我帶回大量的畫冊。姐姐總希望我能考上大學,但我腦子裡想到的只是掙錢,這也是姐姐對我最大的遺憾。她總是說我胸無大志、貪圖享受。在她眼中我是一個聰明而庸俗的人。直到我高一棄學,姐姐終於不對我的前途抱有任何幻想。
從86年到89年這三年裡,我趕上了一個掙錢的機會。那時侯家用電器在農村大量普及,我便利用自己對電器的了解開始做起了倒賣家電的營生。在那三年裡我倒賣了大量的劣質家電,掙了不少農民兄弟的血汗錢。這時的我再也沒有質朴的心靈,整天巴結地方稅務、工商,偷稅漏稅、花天酒地。心裡除了掙錢沒有任何理想。整天沉迷於港台庸俗的下三爛流行音樂,以及那裡透露出來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
這樣的生活一直到了89年春夏之交,我從來沒有象那幾天那樣關注政治,也從來沒有象那幾天那思考生命、青春、人生的價值。正是那樣的學生喚醒了我麻木不仁的靈魂。從那時起,我開始反思自己所做的一切,從而做出了我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次選擇--放棄我所擁有的一切,離開小鎮到廣州求學。盡管父母反對,但我很快說服了他們。父母的偉大就在於他們總是尊重兒女的選擇。從此,我便住進了廣州美術學院的學生宿舍,因為那裡有我中學的同學。我和他們一起上課、聽各種講座,那段日子是我在廣州最充實的時光。經過一年的準備和學習,我在91年春天回到家鄉參加高考補習,但最終還是落榜。
因為這次的失敗,我再一次對自己產生了懷疑,經常對酒當歌,為了謀生,便開始在一家廣告公司做設計,這段時間彈琴唱歌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在92年春天,我認識了一個美國人,在他的住所裡我聽到了他用彈吉它並掛著口琴唱出的美國民謠,他還向我介紹鮑勃。迪倫,以及美國六十年代的民歌運動。遺憾的是,我們沒認識幾天這個美國人就離開了中國。在這段時間,我白天上班,晚上在一家酒吧唱一些嘩眾取寵的口水歌,以博得觀眾的掌聲。時間一長,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些生意人的豪飲作態,終於在夏天產生了離開廣州的念頭。當時就想背起吉它到全國走走,在朋友的百般挽留下,我還是一意孤行,終於在1992年10月20日過完我23歲的生日坐上開往北京的火車,開始了我音樂道路上第一步。
“這一次我離開了家越來越遠/往後的事該如何去面對”這首《越來越遠》可以說是我民謠之路的開山之作。對於前途我無時不在思索著,在開往北京的列車裡,我無法入眠,窗外的黑暗象迷一樣無法洞穿。我感到這一次的出行,將是一次永遠無法回頭的旅程,盡管我的身後有我的善良勤勞的父母,和我那難忘的童年生活,以及太多的牽掛。但是,列車有節奏的震動聲卻不停地吸引和催促我,看著周圍熟睡的陌生人和車窗上自己的鏡影,我只能用一行淚水來強忍著這時候的心情。
一種空前的自由感突然的到來卻讓我膽怯。這時候的自由不再是一個字眼,一個概念,而是一股巨大的旋風,一股把火車推進黑夜的力量。過了長江,過了黃河,過了所有陌生的村莊,終於在10月22日的早晨到達了北京站。這是二十多年來我坐過最長時間容量的火車,也應該是徹底改變我生命軌跡的一次拋引。
我的行李很少,只有一個小帆布包,一把六十元的“紅棉”吉它。由於南北方的溫差,我把包裡的衣服全都穿上了,這時小包也就被卷成一團帆布與吉它綁在一塊。隨著行色匆匆的人群我走出了北京站,那時侯北京站一帶的景色很破舊。伴著淒迷的細雨,我在出口處足足站了一小時,看著不斷有人群從一個地下出口出來,後來才知道那是地鐵口。面對著這個我完全陌生的城市,我真的無所適從。多年以後,我在《過路人》中唱到:“在火車站的過道上/他這樣的模樣/沒有人願意多看一眼/過路的人啊/總是匆匆地走遠。”是啊,有誰會去搭理一個陌生的過路人呢?看著手中剛買的地圖,卻找不著一個可以去的地方,這時候的地圖對我又有何用呢?在這個沒有親朋的城市裡,哪兒才是我落腳的地方?我真想回到列車上,讓火車繼續往前開,永遠別停止,讓我永遠在旅行中,那該多好啊!那一刻,我真的膽怯了。為了更好地躲避寒雨,我走下了地鐵站,誠惶誠恐地買了一張五毛錢的票,第一次坐上了地鐵。經過一陣擁擠以後,有許多人下去了,我便在一個角落裡坐下。後來我發現這輛車在不斷地繞圈,同一個站名過一段時間又出現。太好了!既然火車不能一直往前開,那就讓我在地鐵裡繞吧,一圈,一圈,一圈,……。我的心裡開始溫暖了。地鐵緩解了我突然著陸的失落心情,我不再那樣沮喪,便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做了無數次殘缺不連的薄夢後,我再一次醒來,這時,我終於可以安下心來看手中的地圖,安排下一步我該去的地方。當時最想去的地方是中央美院,找了很久才在地圖上找到美院的地址。最後決定在前門站下車。當我一出站才發現夜幕已快降臨,遠處的天安門城樓被一片灰色籠罩著。我懷著復雜的心情走過廣場,很奇怪,當時一點都不激動。也許這個地方太神奇,我對她一點陌生的感覺也沒有。我一直走,後來穿過王府井,卻怎麼也沒有找到中央美院。最後在實在累得不行了,加上一天沒吃東西,便找到一家蘭州拉面館,花了六毛錢吃了一碗拉面。這家在華僑大廈對面的拉面館後來成了我在北京的最愛。而當時我並不知道它的北邊就是我日後賴以生存的地方--中國美術館。
剛到北京的那段日子裡,我一直住在美術館附近的小旅館地下室裡。那時美術館剛好有一個大畫展--東京富士博物館藏品展,全國有很多藝術青年都趕來觀看。當時我對美術館這一帶欣賞不已,心想:“等我沒錢的時候就在這兒賣唱吧。”過了將近一個月後,我帶的錢所剩無幾,馬上就要面對生存的問題了。還好,對這個問題我並不在意。雖然人生地不熟,但憑自己的真誠和能力,在這兒混碗飯吃還是不成問題的。
我第一次在美術館賣唱是92年11月13日,那天下午天氣並不好,陰沉沉的。我背著琴來到美術館售票窗口旁的那排銀杏樹下,把琴取出,說實在的,當時心裡還是忐忑不安的。畢竟是第一次,我不知道會有怎樣的結果。當過路人用奇異的目光看著我的時候,我真的有點不好意思,甚至還想打退堂鼓。“怎麼能這樣呢?再大的障礙都必須消解掉,就當這些人不存在了。”就這樣經過短暫的心理鬥爭後,我終於閉起了雙眼,唱起了當年市面上流行的歌曲。很快就有很多人圍過來,我一口氣唱了七、八支歌,但是觀眾卻不明白我是什麼意思。最後我終於厚著臉皮對大家說:“下面我唱最後一首歌,希望大家給我一些幫助。”在我唱完歌以後,很多人便往我琴袋裡放錢,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成功了。在收攤的時候有兩個大學生模樣的女生過來跟我說話,強烈地要求我到她們學校--北京工業大學去。說他們學校有很多彈琴的男生,在她們的真誠邀請下,我難以推辭,便跟著她們回到了學校。當天晚上北工大的幾個學生七湊八湊地在學生會的一間房子裡給我搭起了一張床。大學生們的真誠讓我感動不已,那一夜我終生難忘。後來我在《那時侯的心情》唱道:“無論你在哪裡流浪/都有關心你的朋友。”在我七、八年的街頭賣唱生涯中,讓我感動的事層出不窮。我記得在94年春天,我每次在美術館,總有一個看上去比較貧窮的老頭和他的老伴常來聽我唱歌,就坐在我的身邊。而且每次都在我琴袋裡放一些錢,但過一段時間後,我發現只有他一個人來聽歌,後來才知道老伴已經去世了,一年後我從外地回到美術館,卻再也沒看見那個老頭了。還有一件事是,有一次一對中年婦夫,帶著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從美術館出來。在我對面停住了,小女孩堅持要聽我唱歌,後來小女孩叫她的父親給錢,他的父親從錢包裡掏出五元錢給她,而這時小女孩卻毫不猶豫地把錢包從他父親手裡拿過去,並取出一張一百元的錢放在我琴袋裡。還有一個人他叫王順義,是一個被人稱為“傻子”的小伙子,他是我七八年來的忠實聽眾。只要我在美術館唱歌他就會蹲在我前邊,並幫我把被風吹走的錢撿回來。人們認為他是低能兒,是因為他的智商停留在四、五歲兒童的水平。但我卻認為,他是全中國最清醒的人,他的智力也絲毫沒有問題,他會唱我所有的歌,而且能說出很智慧的話,“現在歌迷少了,球迷多了”,“你應該多寫新歌,但老歌也不要不唱,老歌不唱以後就會忘了”,“不要讓記者報道你,要不然一報道,你家人就知道你在街上賣唱,就會把你抓回去。”如果有人說這個人是傻子,我倒認為說這樣話的人是弱智,我更願意把他稱作我的精神導師--永遠清醒,永遠不通世故,永遠熱愛生活、那怕是單調平凡。我就是這樣在美術館把我的生活問題解決了,有一次我認識了一位住在圓明園的畫家。從那以後,我便離開了北工大,住進了圓明園福緣門2排3號,從此開始了我的創作生涯。寫下了第一首歌《圓明園》:“月亮在高空/你卻在這裡/人間的滄桑你視而不見/百年的孤獨讓你如此淒涼/圓明園/你在哪裡。”
如果說生活就這樣簡單地解決了,那麼藝術的創作卻並不那麼容易。當時我並沒有什麼方向,所寫的歌也盡是一些個體感受,無非是迷茫、壓抑或者憤怒。這些東西並不能代表藝術本身。個人的生活折射出來的情感有時候卻是那樣蒼白,雖然自己的痛苦能夠感染周圍能夠與你同感的人,但畢竟是狹隘的。這樣的東西在92年到93年的市面上大充其道。那些哭天罵爹的憤怒和傷感也確實是那時候年輕人的主要情懷,我也無疑也被這樣的東西的影響著,總想在自己的傷疤裡能夠再挖點什麼出來,這無疑是一種投其所好的病態。當時那些人標榜的那種生活狀態現在看來是如此的可笑而且軟弱無能,這樣的東西卻被台灣的商人炒作得如天神來臨。當時我聽到這些,確實跟著他們一樣地痛苦、一樣地憤怒、一樣所謂反叛。但是這種表現卻只是一種麻醉,或更確切地說是一種麻木,一種自作多情痛苦之後的墮落。哎呀,這樣的東西要它們幹嗎呢?我有了這樣的想法自然就和這些人、這樣的音樂不合流。盡管當時組建樂隊是一種時尚,但和這樣的人在一起,我深深地感覺不自在。尤其是當時簽約成風被功利目的驅使的那群人,那時候北京的PARTY表面上看似紅紅火火,但其實只是供洋人消遣的娛樂。因為那時候北京並沒有酒吧和那麼多娛樂場所,而且這樣的演出跟老百姓也沒什麼關系。就這樣一群趕時髦的北京青年和一些獵奇找樂的洋人合在一塊,便成了那段時間令現在很多人懷戀的“精神生活”,而大罵現在時代的庸俗和精神貧乏。是的,現在的洋人再也不會對那些鬼哭狼嚎的東西感興趣了,找樂的地方多了,三裡屯、朝陽公園的酒吧多得海了去了。你要想唱歌就好好地扒洋人的磁帶吧,把《加洲旅店》唱得比貓頭鷹還好,要想掙更多的錢就回家練基本功,做一個合格的棚虫,生產更多的合格垃圾。除此之外還是死了音樂這一條心吧。如果有人說:餓死你,狗日的詩人,那麼還可以再加一句:餓死你,狗日的搖滾佬!
“藝術不能當飯吃”,這是許多還未發跡的藝術青年經常討論的問題。藝術家不是神仙,生存總是重要的。不能靠官僚,又不能指望商人、洋人,那怎樣活著呢?在這時我把手指指向一個地方--人民群眾,離你的生活最靠近的人民。只有那些質朴而有良知的人才是藝術家的衣食父母,才是最可靠、最有判斷力的。試想一下,全中國的老百姓每個人給你一分錢你就有可能成為一個百萬富翁,但問題是你有沒有資格去拿這一分錢,老百姓願不願意把這一分錢給你。除此之外那些所謂家財萬貫的藝術家都是騙子,這句話一點也不過分,那是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商人們無時不在鼓吹他們的“天才論”,而且這樣的“天才”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會象放煙花一樣煙霧繚繞,其實都是跟勞苦大眾毫無關系。那些都是混淆是非的鬼把戲。誰能把這些東西早日看穿,誰就能同人民支持的藝術更靠近。“時刻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是一句做人的真理。
曾幾何時,我何嘗不是在這樣的問題裡找不到道路呢?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些最底層的人是如何對待他們所喜歡的人的。那是在1993年5月上旬,我無意中參加了一次被官方認為是非法集會的活動,並在那裡唱歌,結果在回去的路上被警方拘留、收容了兩個多月。在昌平的收容所裡,我被當成盲流關押,在那兩個多月裡,我天天與那些生活在這個城市最最底層的人同吃、同睡、同樣地絕望。還好,警察並不認為我是盲流,對我還算客氣,所以免去了很多皮肉之苦。就連那些靠吃垃圾箱裡掏出來的食物為生、露宿街頭的人,也會把他們手裡僅有的一點食物分給我。在那年的春夏之交,我的內心被這些人深深地震動著。在那個有足球場大的院子裡,我和全北京的三無人員、流浪漢、乞丐一起迎來日出、目送夕陽。在警察的組織下,我每天黃昏都為幾百上千的人唱歌。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下,人們只有在歌聲中感受到自由。沒有經過煉獄的人是不會看見真正的光明的。我記得那些聾啞人,雖然他們不能聽到我的歌聲,但當他們知道我的身世和我來到這裡的原因,卻從他們藏得很嚴實的手絹中把他們僅有的錢給了我,在那時,我的淚水卻再也忍不住了!而他們也和我一樣熱淚盈眶。在沒有語言的表白裡,我再一次看到了人性的正義和善良的光輝。我與這些人可能再也不能相見了,但他們每一張臉卻深深地印在我的生命裡。我不為這樣的人歌唱為誰歌唱呢?
1993年6月16日,我被遣送回原籍。兩個車皮六百多人在京廣線的那個方向我和所有的盲流在一群武警的看押下離開了北京。經過一夜的路程,在第二天早晨到達了鄭州。我在幾個新疆人的包庇下和他們一起被當作新疆人趕下了火車,重新獲得了自由。這時候的自由象飛鳥的羽毛一樣光亮和實在,過去的一切象一場噩夢,過去的一切象海洋一樣一言難盡。雖然這並不是什麼災難,但畢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在鄭州火車站的站台上我身無分文,再加上一夜沒吃東西,我便開始在站台上收撿從列車上掃下來的殘余食品,吃上了我這一輩子認為最好吃的半個面包,然後象乞丐一樣向陌生人要食品和香煙。即使這樣我內心裡依然是充實而溫暖的,在自由的光芒下是無盡的感激。我在站台上呆了幾個小時後,搭上了從成都開往北京的列車,一路逃票回到了北京。為了繞過檢票口,下車後我沿著鐵路走到東便門,最後回到了我的朋友們中間。
經過這一次的洗禮,我看清了社會最底層是怎樣的狀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運是和什麼樣的人聯系在一起的,也知道了今後要怎樣去面對無望的生活。在北京小住了一個月後,我終於決定離開北京,到各個城市去賣唱、去發現更多的未知。在朋友的讚助下,我買了一張從北京到烏魯木齊的車票。帶上吉它,開始我吟遊祖國各地的生活。“我要做的事是從這一站到下一站/當你發現你已經是個自由的人/怎麼會忘記那時侯的心情?”我從北疆到南疆,一路賣唱,一路搭順風車,到處都有熱心幫助我的人,雖然我總是身無分文,但從來不為此而發愁。那些不求報答的善良人都是我生命中永遠無法忘懷的。我只有不停地為他們歌唱才無愧於這樣的人。在離開新疆以後,我沿著絲綢之路到了敦煌、嘉峪關、蘭州、西安,然後到了成都、樂山、達縣、重慶,最後回到了北京。在將近四個月的旅途裡,我經歷了一幕幕難忘的街頭賣唱生活。在每個陌生的地方面對陌生的人群,我卻有著並不陌生的感受和場面。在93年的冬天到94年的春天,我在北京完成了《越來越遠》、《小魚兒》、《小康夢》等到目前我還願意並且永遠願意唱的歌曲。
在94年初,我從大量的洋唱片垃圾中找到了最有意義和最值得學習的東西,那就是鮑勃﹒迪倫的前三張專集。成了我那段時間的精神食糧,我夜以繼日地聆聽和研究,盡管我聽不懂他的歌詞,卻被聲音深處的精神內涵以及一把吉它伴奏的純民謠形式所吸引著。同時也堅定了我追求這種純民謠風格的音樂方向。我曾與朋友戲言說:“這哥們幹的事怎麼和我那麼相象?”,並揚言要成為中國的迪倫。為了這個目標,我瘋狂地搜集他的資料,盡管當時市面上有關迪倫的介紹少之又少而盡是那些該死的“死亡金屬”還有“殼郎屎”。我通過朋友從國外找到了迪倫的歌詞還有各種資料,還引進了口琴架。從資料上顯示迪倫的音樂的根基是黑人的民間音樂,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通過迪倫我還發現了更多有價值的名字:伍迪﹒格斯裡、彼得﹒西格、羅伯特﹒約翰遜等等。在通過對這些人的研究中,我發現了所有的民謠先知們都是自覺地通過社會的底層生活來控訴各種暴力機構,比如迪倫的《誰殺死了戴衛﹒莫爾》和伍迪﹒格斯裡的《流浪漢的搖籃曲》、彼得﹒西格的《花落何處》。他們教會了我民謠的功能性與社會性,就這樣我開始冷靜地去觀察和思考社會的各種因素,來豐富歌詞創作的思想內涵寫成了《烤白薯》這樣的作品“夜已深沉/風也停了/寂寞的街道/看不見路人/賣考白薯的兄弟/回到了冰冷的被窩裡/安睡吧/不必嘆息!總有一天你會到天堂/就沒有警察和工商”。這些話又何嘗不是用來安慰我自已的呢?因為我在街上賣唱那多年來,那一天不擔心被警察抓走,那一次被抓後口袋裡的錢不是被罰個精光。在這裡我並不是要咒罵警察本人,更何況哪個警察的出身不是平民老百姓?
我在美術館唱歌七、八年以來,第一次被警察幹涉是在93年3月份,當時美術館展覽羅丹的雕塑。人很多,我也在那一段時間經常去賣唱,有一天下午我坐在欄桿上剛唱了幾首歌就有兩個警察過來,二話不說就往我吉它上“”的踏了一腳,制止了我的歌唱,並強行地把我帶回派出所。面對暴力,我除了沉默和強忍淚水還能怎樣呢?我就是一塊肉任你們宰割吧!還好,警察看我面善老實,除了罰錢並沒有把我怎樣,一番恐嚇和警告後便把我放了。如果警察總是這樣幹涉,那我是不是就不去街上賣唱了呢?不是,起碼我不以為我做錯了什麼,而且我也沒有防礙交通,擾亂社會治安,為了我心中的藝術我幹嗎不賣唱?你想那些走私犯為了錢,連坐牢都不怕,何況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呢?這樣想我就不害怕了。一年被罰個十回八回的沒什麼,總得來說我還是賺的。
就這樣時間一長警察的態度也有所溫和。有一件事情很能說明問題,那是最近發生的,在99年8月20日我在美術館剛剛唱了半個多小時,這時有兩個警察開著摩托車過來了,我一看這架勢只好停止唱歌,警察下車後走到我面前說:“幹嗎呢?你哪的?哪的?身份証!身份証!”我趕緊掏出身份証,雙手遞過去,警察一看是外地身份証,便說:“有暫住証沒有?”“沒有,我是來旅遊的。”“旅遊的?別逗了,你可有名了,收拾東西跟我們走一趟。”這下壞了,我的前途又充滿了未知,而且正是國慶前清理三無人員的危險時期。但我並不害怕,大不了又被收容,回到昌平沒準還能看見那些老朋友呢,把93年的經歷重演一遍就是了。奇怪的是,這一次我被帶到了所長室,裡面有七八個警察在空調下乘涼,“又是你,你的膽子怎麼那麼大?你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以前抓過我的警察沖我說,這時候那個看我身份証的警察卻不象剛才抓我時那樣兇,還遞給我一支煙說:“別怕,別怕。”然後對其它警察說:“這哥們在美術館唱了好幾年了,原來我做便衣那陣子老去聽他唱歌,唱的真棒,人家這是憑真本事吃飯,也不知道是那個缺德的打110了,不管怎樣我得去把他抓回來呀。”這一下我心裡踏實了,這時候那個警察接著說:“你唱的歌都是你寫的吧?”“是的。”“那好!給我們唱唱你寫的歌,你要能把我們唱哭了,或著逗樂了,算你有本事,怎麼樣。”我心想唱哭了可能不太容易,但逗你們樂,還是沒問題的,便抄起家伙唱起了《樣樣幹》。唱完後所有的警察都樂了,有好多警察也從別的屋過來,這時我與他們也就象老朋友一樣有說有笑,警察也是人嘛。後來抓我的那個警察對所長說:“過兩天咱們去靈山把他也帶上,讓他給我們助助興。”並問我願不願意去,我當然願意去了。最後那個警察把我送下樓並給了我兩包煙,還叮囑我這段時間風聲比較緊多注意點,如果生活實在有問題他可以幫我聯系到酒吧去唱,還鄭重的叫我大後天準時來派出所一起去靈山。8月23日早上我準時到達派出所與三十多個警察一起坐警車到達靈山。在吃飯時,那個警察把我隆重地介紹給所裡的同事,並叫我在酒桌上唱《樣樣幹》唱完以後掌聲如雷。最後警察還對我說:“來一個《烤白薯》,給我們唱一唱這個醜陋的社會!”唱完,所有的警察都沉默了。等到第二天,派出所的正所長對我說:“楊一,你在這多住一晚上吧!明天我們所裡還有三十多人要來呢。”並叫老板好好地招待我,打從那次以後我和很多警察都成了朋友。這就是歌唱的魅力,藝術的力量,她應該是能感化所有人的靈魂的,藝術家如果沒有批判與關懷心靈是不能可得到人們的支持和尊重的。
如果說我從那些民謠英雄那裡學會了歌詞內涵的表達,那麼對於音樂我認為應該把根紮在中國的土地上,就這樣我也開始把自己的目標轉向了搜集和研究中國的民間音樂。在1994年5月份,我再一次離開了北京,這一次離開北京與上一次不一樣。上次是吟遊,而這一次我是去尋找那些閃亮的音樂、是向那些勞動人民拜師學藝。就這樣我背起了吉它、帶上錄音機,從北京出發到達了西安。然後深入陝北的延安地區、安塞、綏德、米脂、榆林、神木、府谷等等。這一次我第一次聽到了純正的民歌,那種震撼一點也不亞於我聽到的任何一種音樂。從此我深深地愛上了陝北的民歌、以及歌聲後面蘊涵的氣質。在羊馬河的一個名叫胡家塘的小村裡,我聽到並看到了一個純粹的民歌大師的風貌。那是一個六十多歲的歪嘴老農,他自制了一堆打擊樂器,並輪換著各種樂器為我唱出了最動人的歌謠。後來我把他的錄音放給我北京一個對音樂有很深感受力的朋友聽,他當時便被錄音機裡傳出來的聲音感動得趴在地上痛哭流涕,並大喊著說:“我為什麼以前聽不到這樣的聲音?”。為了這個我崇敬而不為人知的民歌手,我從陝北回來後寫了一首名叫《上路吧,朋友》。從那以後,陝北成了我音樂上的家園。從94年到96年我每年夏天都要回陝北,最後一次我是騎自行車幾乎走遍了整個綏德地區的村莊,為的就是能聽到更多的民歌。我想,與那些真正的民歌手相比我真的相差得太遠太遠了。因此只能寫一首《傻乎乎的老楊》來嘲諷與提醒自己,永遠是勞動人民的學生。“想要象老農那樣歌唱/自己先看一看/五音都不全/傻乎乎的老楊。”對於人民我學一萬年也不夠。正是歌唱讓我如此接近大地和勤勞質朴的人民。
(1999年12日12日)■〔寄自廣東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