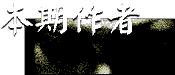城市裡的人
廠裡一砸錠,大家就曉得好日子過到頭了。沒有砸錠的時侯日子過得也捉襟見肘,但每天一早上班,鈴聲響了下班,做夜班的車間也是燈火通明,有班在上著,心裡就充實,心裡一充實,日子就過得有滋有味,這是大家都有的體會。機器開著的時侯,是生產得越多,虧損就越大,這是一個讓人捉摸不透的怪圈。錠砸了,人員就要減少,這叫水到渠成,是明擺著的事情。工人下崗不叫失業,有個正確的說法叫下崗分流,很顯出國情的特殊性。
劉珂和虞志明都是棉紡織廠的工人,恰巧又都是砸錠的那個車間的,這叫禍不單行。按理說夫妻兩個同在一個單位的,就算要下崗也是只能下一個的,但虞志明心中沒底,砸錠的決定一宣布,他的心裡就空落落的。原先,虞志明是在廠部上班的,搞的是宣傳工作,具體崗位是幹事,也是神氣過一段時間的。胸前掛個照相機,經常跑到車間去採訪,還常常在市報發表一些消息之類的文章,雖然也就是豆腐乾那麼大的一塊,但畢竟是把手寫的文字印成了鉛字的,這在廠裡也算是鳳毛麟角了,虞志明走進走出別人見了都是要喊他一聲虞秀才的。虞志明也是聽出其中的不懷好意的,但他不計較,虞志明是不會跟一般人計較的,虞志明在心裡說你們不服氣你們也寫幾塊豆腐乾給我們看看呀?他和劉珂就是從那時開始談得戀愛。劉珂是廠裡的先進,曾經得過好多次廠裡的操作能手稱號。虞志明老是給劉珂拍照片,拍出意思來了。開始的時侯,劉珂的小姐妹,包括父母都是不太讚成的,說虞志明工人不像工人,幹部不像幹部,要是劉珂嫁給了他,有的苦頭吃了。劉珂聽了只是笑笑,聽得多了,也就說一句話:“我也是一個小工人,也是吃苦的命。”當事者昏了頭,旁人再多話就顯得有點背時了。再說虞志明實在也是挑不出不好的地方的,沒有不良嗜好,不抽煙也不喝酒,這是很讓劉珂心動的地方,棉紡織廠男人不如女人多,男人們就好像很神氣,個個都是煙、酒、茶俱全的“三好學生”。劉珂無法想象以後跟一個一身煙酒氣的男人如何同床共枕。她嫁給虞志明的時侯,城裡的大學生已是一拎一大把了,憑劉珂的相貌人品本來是可以找一個更好一點的,劉珂卻認為虞志明已經很不錯了,人無完人,誰能料到虞志明日後真有出息呢?劉珂母親是見過一些世面的,她斷定虞志明是那種碌碌無為之輩,差不到哪兒去,更好不到哪兒去。她對劉珂說有你哭得時侯。劉珂也依然是笑笑。
虞志明和劉珂結婚時沒有整套的房子,廠裡給了一間集體宿舍。虞志明在新婚之夜對劉珂說:有了你,我就擁有了整個世界。這樣的甜言蜜語是很能打動女孩子的心的,劉珂自然也不會例外,她相信只要有愛情,生活苦一點實在算不了什麼。夫妻倆在螺螄殼裡做道場,日子過得津津有味。還有了愛情的結晶,取名虞亦珂,意思是這個女兒既是虞志明的也是劉珂的。
劉珂長得小巧,說不上特別漂亮,但很耐看,屬於那種越看越想看的女人,尤其是她的一雙眼睛,笑起來時瞇著,彎彎的月亮似的。虞志明在回答劉珂因為什麼愛她時,虞志明說是因為看到了劉珂的眼睛,就再也沒有力氣了。劉珂又問虞志明最愛她身上的什麼?虞志明的回答還是眼睛。於是,劉珂也曉得自己的眼睛是很迷人的了,她在看人時盡量不去看對方的眼睛,特別是面對男性的時侯,她怕別人誤解,她看人時的那種眼光富有挑逗性。
虞志明在廠裡進行第一次改革時就充當了試驗品。他所在的宣傳部門被並到另一個綜合部門,人就不需要那麼多了,虞志明是沒有大學文憑的,這是很讓虞志明吃虧的地方,但也沒有辦法,頭頭總是願意自己手下的人拿得出手的,兩個幹事,大學畢業的留用,高中生虞志明就下到車間去了,這一下,就為以後埋下了禍根。本來,虞志明是可以選擇到其它車間的,但他跟劉珂一商量,劉珂怕虞志明精神上壓力太大,就提出到自己所在的車間來,這樣,兩人在一起也好有個照應。開始他們上的是三班倒,後來劉珂去找了車間主任,說兩人都輪著倒班,女兒沒人管了,主任就說兩人中的一個做長日班,劉珂就選擇了讓虞志明上日班。虞志明在廠部的時侯是愜意慣了的,一上三班倒,人也瘦了,脾氣也見長了。主任通知他改上日班時,他還是一副落難秀才的委曲樣子,劉珂見了心裡就有些難受。劉珂勸虞志明去參加自學高考,說這是大勢所趨,要想有個好一點的工作,沒有文憑看來是不行了。虞志明不聽,說他相信自己的實力,就是大學生也未必比他強到哪裡去。劉珂聽虞志明這麼說,就有些詫異地看著他,她沒有想到虞志明夜郎自大到這個地步。她在心裡說:你有什麼實力?你的實力不就是拍幾張照片,寫幾塊豆腐文章。但這話就是打死她也不會說出來的,這話是她的好朋友王婷跟她說的。王婷說這是劉珂的悲哀,說劉珂是被虞志明這個鬼迷了心竅,總有一天會讓劉珂吃不消的。
劉珂勸了虞志明一次就不再勸第二次了。劉珂想我不指望你當官發財,只要我們娘兒倆一日三餐有保証,這個要求總不算奢侈了吧?
廠裡在大會堂召開職工大會,虞志明和劉珂都參加了。往年在這個時侯,虞志明都是要背著個相機跑上跑下的,對著主席台嚓嚓亂撳一氣,然後,再到下面的人群裡來拍,他專找漂亮的女工拍,紡織廠女工本來就多,他是籮裡拍花,越拍越花,也不見有什麼作品在攝影雜志上發表或在一些攝影展覽中展出。而不過時隔幾個月,今天,他也只能坐在台下聽從命運的宣判了。
上級來人宣布了砸錠的決定,對砸錠車間的工人分流也提出了大致的去向,自然是下崗的佔多數。上級領導在讀完紅頭文件後又借題發揮了一下,動員大家要轉變觀念,要有效益的觀念、競爭的觀念、開放的觀念、大局的觀念,總而言之,要有市場經濟的觀念。劉珂第一次聽到這麼多的觀念,想記也記不全。領導又說工人階級要勇於進取,要站在改革的前列,砸錠是為了保証棉紡織廠脫困的大局,做出局部的犧牲正是為了大踏步的前進。他說,我有兩句古詩要送給大家,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上級領導講完了,接下來是廠長講。廠長還沒有開口,眼睛就紅了。大家看了都有些心酸。最後,廠長沒有講話,只是雙手抱拳給大家作了個揖。虞志明說廠長是老甲魚,好像這事與他無關一樣。劉珂不這樣認為,她覺得廠長也不容易,砸錠又不是廠長能左右的事情。況且劉珂關心的是下崗的事,對廠長講不講話,講什麼話沒有多大的興趣。坐在劉珂旁邊的王婷悄悄地對劉珂說怎麼樣?開始甘盡苦來了吧?劉珂用手去掐王婷的大腿,說你這張烏鴉嘴,少觸我的霉頭。王婷說我是烏鴉嘴,我最見不得你那寶貝老公不可一世的樣子了,這一回,看他怎麼跟你交待?劉珂說還能有什麼交待?下崗又不是他自己要下的,大家都下了,我們又能怎麼樣?王婷說你是操作能手,總不會也說下就下了吧?劉珂嘆一口氣說,我這個操作能手是老黃歷了,現在機子差一些的都是打工妹在做了,好的呢也輪不到我,打工妹肯吃苦又叫得應,誰還願意用我們這幫老的。這一砸,怕是砸得差不多了,打工妹也可憐,千裡迢迢跑出來,說回去就要回去了。王婷說你還是可憐可憐你自己吧,飯碗都要敲掉了,還在悲天憫人。劉珂問王婷有什麼打算?王婷說沒有,先在家裡休息一段時間再說,做了這麼多年,還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這一回要睡它個天翻地覆,砸錠也好,砸爛一個舊世界,再砸出一個新世界。劉珂苦笑了一下,說我們都是舊世界的人,這舊世界一砸,我們不也一道砸進去了?王婷說不一定的,總要有人參與新世界的建設的。王婷又說,不過,我看來是不太可能進入新世界的重建了。
劉珂和虞志明從廠裡走出來,面面相覷。走了一會,兩人停在路邊不走了。劉珂說你說我們要不要找找廠長?虞志明說要找你去找,我是不會去找的。劉珂的臉色有點難看,虞志明說現在去找也沒有用,不如過幾天再去找也不遲。說著,兩人就騎上車子離開了廠區。
虞亦珂自從會走路以後就住到外婆家去了,到周末才回自己的家。劉珂母親見一家三口擠在一個房間裡,就主動提出讓亦珂住到自己那邊去,雖然房子也不是很大,總算是成套的。劉珂徵求虞志明的意見,虞志明懷才不遇,早已是英雄氣短,也沒話好說。亦珂就住過去了。這等於跟全托沒有兩樣,那邊也不要劉珂給的錢。做娘的說這點錢不如你存起來,你們總不能在這個房間裡住一輩子吧。劉珂聽了心裡有點不痛快,從眼下的情況來看,有這樣一個房間住已是很不錯了。王婷跟她說過,愛情是愛情,生活是生活,是不一樣的,要過稍許好一點的生活,光有愛情是遠遠不夠的。劉珂是不會聽王婷一套一套的理論的,既然結了婚,老公又是自己選擇的,是苦是甜也只能自己品嘗了,鞋子買來了,實行三包的可以去調換,嫁了人了,這個人總不能說換就換吧?
虞志明和劉珂回到家,劉珂要動手做飯,虞志明說別做了,我們到街上去吃。劉珂說你發財了?虞志明說慶祝一下從今以後我們就都是自由的人了。劉珂說我看你是腦筋搭牢了,人是自由了,飯碗也敲破了。虞志明很大氣地說天無絕人之路,不就是下崗嗎,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不了從頭再來。劉珂看虞志明有點活過來了,就依了他。兩人走到街上,劉珂問虞志明到哪去吃?虞志明說我知道不遠的一家酒店羊肉很不錯,價格也不貴。劉珂聽了心裡就有些感動,劉珂是最愛吃羊肉的,只是平時她買菜時總是買一些老公女兒喜歡吃的菜,從來不買羊肉吃的。劉珂曉得了虞志明今夜的心思,也是想讓自己開心一點,就主動用手臂去挽虞志明的腰。夫妻倆走在路邊桂樹的陰影下面,在別人的眼裡,一點也看不出這是一對剛剛下崗的棉紡織廠工人。
虞志明點了一只羊膀子,一碗羊肉湯,這是為劉珂點的,他只為自己點了一只家常豆腐。劉珂很少進飯店,也不太會點菜,偶爾進一次飯店也是虞志明點了算的,這次似乎也不例外。菜上來了,劉珂就覺得有些不對頭,虞志明說我點的就是這樣的,沒有上錯。劉珂瞥了虞志明一眼,用手去抓羊膀子,卻燙得她一下子把手縮了回來,虞志明說這是剛烤好的,很燙,你用濕巾裹著啃好了。劉珂就用濕巾裹著啃咬起來。味道確實很好,她邊嚼邊喝羊湯,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虞志明看劉珂啃得差不多了,就要了一碗飯就著家常豆腐吃了。劉珂啃了一只羊膀子,喝了一碗羊湯,又要了一塊南瓜餅吃了才罷休。她用紙擦拭了一下滿是羊油的嘴唇,對虞志明說你吃飽沒有?虞志明點點頭,兩人結了賬走出飯店,都有些意猶未盡。虞志明說要不要到湖邊去走走?劉珂用眼睛去看虞志明,仿佛在說:你給我吃了羊肉是不是又有非份之想了?虞志明說你看我幹嗎?但兩人的心裡都在想著他們的第一次。
虞志明和劉珂談戀愛的時侯只要劉珂上早班就天天去湖邊,好像有說不完的話。終於有一天,他們沉默了。大家都覺得話已經說得差不多了,要做接下去的事情了。這時,天色已晚,湖畔的燈光也暗了下來,很曖昧地照著動盪的湖水。他們坐的堤上已空無一人,此時此刻再不做點什麼似乎有些對不起這良辰美景了。虞志明就擁吻了劉珂。虞志明在和劉珂接吻的時侯聞到了劉珂嘴裡的好聞氣息,就象堤上的青草一樣的氣息。劉珂的身子已經軟了,由著虞志明的嘴在自己的唇上吻來吻去。過了這一夜,兩人的關系就急轉直下了,虞志明得寸進尺,先是動手動腳,後來看劉珂半推半就,索性長驅直入。劉珂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就稀裡糊塗地把自己交給了虞志明。事後劉珂想之所以自己沒有拒絕,是因為自己也在等著這一刻。這一刻既然來了,就只能讓它順其自然了,擋是擋不住的,也是沒有太大的必要非要去擋的。劉珂不是一個開放的女性,但在這件事情上的表現是很有些實事求是的。
兩人回到家裡,彼此心照不宣地洗了就上床了。因為是集體宿舍,房間的隔音條件不是太好,兩人在床上活動時總免不了有些壓抑。對門有一對新婚夫妻,在晚上經常會有聲音從門縫裡鑽出來,第二天早上見了就都有點不好意思,後來聽習慣了,大家也就見怪不怪了,反而有點羨慕那對夫妻了。虞志明對劉珂說你不要聽這聲音,這可是人性的釋放。劉珂不以為然,說鄉村路上的豬狗牛羊隨時隨地狂呼大叫的,也是在釋放人性?虞志明覺得劉珂不可理喻,人是人,畜生是畜生,怎好混為一談的?劉珂說對呀,正因為人和畜生不一樣,床上做得事也才會不一樣啊,要是都一樣了,人不也變畜生了。在這個問題上虞志明是說不過劉珂的,況且虞志明有自己的小算盤,他是想通過對門的實際事例讓劉珂知道,人性的壓抑是多麼的不人道,我們在白天已經壓抑得太多,不應當在夫妻生活上再人為地受到壓力。劉珂說要做到這一點也不難,只要我們有了獨門獨戶的房子,我也釋放釋放人性,保証不會讓你失望。虞志明聽劉珂這麼說,就不響了,劉珂的要求並不過份,但虞志明無法滿足她的這個要求,既然連這個要求也滿足不了,虞志明又如何讓劉珂在沒有屏障的前提下釋放人性讓虞志明同時享受人性的淋漓盡致呢?
一下子清靜了下來,劉珂和虞志明都顯得有點措手不及,次日一早,他們就醒來了,劉珂穿好了衣服才想起從今天開始再也不用按時上下班了。她在床沿上木然地坐了好久,脫下穿好的衣服又躺下了,卻再也睡不著。平時上班總是感覺睡不夠,鬧鐘響了,也是能多睡一分鐘是一分鐘。現在可以酣睡了卻沒了睡意。劉珂復又起床,在鏡子前慢慢地梳理著頭發,她的心裡忽然就充滿了悲哀,從今天起我就是下崗工人了。虞志明從後面看著劉珂,劉珂的背影線條十分豐富,睡衣從瘦削的雙肩溜下去,在腰際形成一個明顯的弧形,腰部以下又開始有節制的膨脹,然後恰到好處地收攏,順下去的是筆直的雙腿,因為是夏天的早晨,劉珂沒有穿睡褲,腿就張揚地裸著,白中帶著一點瓷色,散發出玉一樣的光澤。劉珂梳頭時雙手向上舉起,睡衣的雙袖滑落下來,露出藕似的臂膀。虞志明不止一次地欣賞過妻子妙不可言的身體,那無聲的肢體語言曾經令他神魂顛倒。從這個背影,誰都無法相信劉珂已是一個年過三十,有一個五歲女兒的婦人了。虞志明慶幸自己,雖然失去了工作,卻有一個百看不厭的妻子。
劉珂似乎已經知道虞志明在背後偷偷看她,她緩緩地轉過身,淚流滿面。虞志明嚇了一跳,他騰地一下從床上彈起來,摟住劉珂的細腰。劉珂在丈夫的懷中抽泣著,虞志明輕輕地拍著劉珂的後背,虞志明知道,自己現在能做的只有這樣了。
吃過早餐,劉珂跟虞志明說她要去父母家看女兒,問虞志明去不去?虞志明說不去了,他想好好在家休息一下。劉珂也不勉強,好像早就知道他不會去似的,。劉珂的父母一直不滿意虞志明,平時虞志明就很少去,接女兒也都是劉珂去的。現在他下崗了,倘若去了,如何面對?
劉珂出了集體宿舍的大門,坐上了公交車,方向卻不是父母的家,而是去了人才交流市場。以前上班,準確地說昨天上班,劉珂還是騎自行車的,人才交流市場離這兒比較遠,劉珂想坐坐公交車,節奏慢一點,順便也看看窗外的風景。說實話,上班掙錢不多,時間卻是很死板的,遲到一分鐘也是要扣錢的,那時匆匆忙忙的卻也沒有感到太不方便,現在鬆馳下來了,反倒不習慣了。劉珂靠窗坐著,上班的高峰已過,車上顯得有點空了。劉珂從車窗外望出去,發現高樓一幢接著一幢,劉珂想這些高樓是什麼時侯建起來的呢?她在電視上還見過在離湖邊不遠的地方也建起了不少的別墅。劉珂無法想象真會有那麼多的人有那麼多的錢來買幾十萬甚至於上百萬一套的房子,這是劉珂連做夢也不敢想的事情。
劉珂在人才交流市場下了車。劉珂從未來過這兒,因為劉珂從未想過自己也會說下崗就下崗了,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竟然也是眼睛一眨就跨入了下崗工人的行列。而且她也從未想過人才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但可以肯定不是象自己這樣只讀過高中,只會操作織布機器的紡織廠女工。劉珂走進市場,發現裡面的人不少,也有一些單位在設攤招聘。劉珂一家一家地看過去,招聘的條件自己一樣也夠不上,光憑學歷就挨不上人才的邊。劉珂走到市場工作人員辦公的地方,見裡面有幾個人在聊天,她找準了一個女的,劉珂想大家都是女的好說話一點,劉珂將自己的情況跟她說了,那女的瞄了劉珂一眼,說你什麼時侯下的崗?劉珂紅著臉說是昨天。那女的說才昨天啊?這兒下崗半年一年的都排著隊,高不成低不就的。劉珂說我無所謂的,只要有工作就行。那女的又問劉珂今年多少歲了,劉珂回答三十一歲。那女的就很有興致地說一點都看不出來的。你用的是什麼牌子的護膚品?是資生堂的?劉珂說我從來不用的,我只在冬天用百雀靈的。那女的就有點泄氣,說劉珂是天生的好皮膚,說話的口氣好像劉珂的皮膚好也有錯的樣子。女的邊說邊從窗口遞出一張表格叫劉珂填,劉珂沒有帶筆,女的說台子上有,劉珂就走到一邊的台子上,俯下身子填表。當劉珂再次將表遞進窗子時,那女的看了幾眼,就說你才是高中生啊?口氣很有點不屑。劉珂的自尊就有點傷害了,她反問那女的,我填錯了嗎?女的說沒有填錯,我是說高中生是不算人才的,所以我們是不受理高中生的檔案的。劉珂問像我這種情況的應該到哪去找工作呢?那女的大約因為劉珂皮膚好但又夠不上人才的邊而有點幸災樂禍,她興高採烈地說你可以到職業介紹所或勞動力市場去看看,那兒或許會有你合適的工作。劉珂又問了職業介紹所與勞動力市場的地址,慢慢地走出人才交流市場。劉珂走出市場時頭一直是低著的,好像由於她不是人才市場認定的人才就很慚愧似的。
劉珂繼續坐上公交車去職業介紹所。那兒的情況似乎要比人才交流市場好一些,招聘的工種也多了起來,五花八門的都有,對學歷的要求也不是太高,大部份工作只要具備初高中文化就可以了,有些還只要求是熟練工。劉珂的強項是織布機的操作,這方面的招聘卻幾乎沒有。劉珂找到一家賓館的招聘攤位前,賓館正在招一些電氣、暖通方面的技術工,劉珂問有沒有服務員的空缺?招聘的人說現在的服務員都是經過專業培訓的,年齡上也有一定的要求,又問劉珂以前在什麼賓館做過,劉珂搖搖頭,對方說你沒有任何工作經驗,很難的。劉珂就有點掃興,正要離開攤位,對方叫住了她,問她除了做服務員還有沒有其他的意向?劉珂說只要有事情做就行。招聘的人說我們那兒缺一個保潔工,你想不想做?劉珂一下子沒有聽清保潔工這三個字,問什麼工?對方重復了一次,這回劉珂聽清了,問保潔工是不是就是打掃衛生的?對方說也可以這麼說。工作量不是很大,就是在大堂裡來回拖地,包括清掃大堂邊的一個洗手間,聽起來好像不大好聽,其實做任何工作都是一樣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貴賤之分的,況且這活也不需要什麼技巧,只要勤快一些就可以勝任的。劉珂決定應了這份工,就填了表,招聘的人說最好能早些上班,如果沒有問題最好明天就上班,他問劉珂有問題嗎?劉珂說沒問題,我明天就可以上班的。
劉珂走出職業介紹所,有一種旗開得勝之感。劉珂想其實下崗也不是什麼洪水猛獸,只要肯吃苦,一碗飯總有得吃的。劉珂沒有直接回家,她想先到那家賓館去看看。劉珂老早就聽說過這家賓館的名字了,只是一直沒有進去過。這家賓館好像是三顆星的,在城裡不算最好,也算是不錯的一家賓館了。劉珂坐車到了賓館,發現坐公交車從家裡到賓館只需轉一輛車,中途轉車也不用離站,就在站上等下部車,應該說還是很方便的。劉珂從外面看賓館,很氣派,大堂看上去很高,很寬敞、亮堂。劉珂想,從明天開始我就要在這裡上班了。她本想進去先睹為快的,但走到門廳邊上又改變了注意,她折回身子決定早些回家把這個消息告訴虞志明。
劉珂回到家,虞志明卻不在,劉珂想不出虞志明會去哪裡。虞志明的父母家在郊區,他無事一般很少去的,自己父母家就更不會去了。劉珂這時才感到肚子餓了,她燒了一碗面條吃了,就打開電視機看電視,邊看邊等虞志明回來。
劉珂在家等虞志明時,虞志明正在報攤上買了一大堆過期的晚報,每份只要一毛錢。他拿著這一大迭晚報到了湖邊找了一個有樹蔭的草地,一份一份地翻看報紙的招聘廣告。以前,虞志明是很不屑看這種招聘廣告的,認為這是報紙在賣狗皮膏藥,他是要讀要聞版的新聞的。想不到此一時,彼一時,現在跟他關系密切的是自己曾經看不起的狗皮膏藥了,自己一向奉若神明的要聞卻沒有興趣去翻了,不過一天時間,就來了一個大轉彎,真是連虞志明自己也想不到的。虞志明邊用一枝原珠筆在報上劃來劃去,邊在心裡嘆息人生的無常。報上倒是有招聘記者的,但都要求大專以上學歷,虞志明這才感到自己的所謂實力在學歷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虞志明在過了期的晚報上尋找工作未果,心中充滿了惆悵。他一張一張地將報紙撕成條條,用剩下的最後未撕碎的一張報紙包了,然後塞進了湖畔的垃圾箱。在將碎報紙扔進垃圾箱的同時,虞志明也感到了自己今天的希望也一起被垃圾箱的口子吞噬了。他坐車回家,一路都顯得有些無精打採。直到快到家門了,才強打起精神,虞志明想我是一家之主,如果我也象一根霜打的茄子,這個家就要跨了。
虞志明走進家裡,劉珂已做了飯等著他了,劉珂笑著說我們的家長到哪視察去了?虞志明說我到湖邊去走走,好久沒去湖邊了,原來那兒的風景是很漂亮的,我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以後我們應該多去走走看看。劉珂替虞志明盛了一碗飯,又替自己盛了一碗,說先吃飯,待會我有好消息發布。虞志明說你還有什麼好消息?莫非你去摸了彩票中了獎了。劉珂說也不是一定要有錢才是好消息的,志明我跟你說我找到工作了。虞志明停住手中的筷子,象看一個陌生人一樣地看著老婆。劉珂說你幹嗎用這種眼光看我?你沒見過美女啊?虞志明蹼哧一笑,說劉珂你是美女不假,可你什麼時侯學會變戲法了?只有變戲法的人才會在一天之間變出好幾樣東西來的。劉珂說你別笑,我是真找到工作了,我告訴你上午我沒有去看亦珂,我到職業介紹中心去了,我明天就去上班。虞志明問到哪兒上班?劉珂說是到一家賓館,劉珂說了這家賓館的名字,虞志明說我曉得的,是一家三星級的涉外賓館。劉珂說我在賓館的商務中心做營業員。劉珂沒有告訴他她做的是保潔工,劉珂太知道虞志明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臭脾氣了,劉珂想好了,等自己做一段時間再告訴他真相,到那時木已成舟,他也沒話好說了。
虞志明說還是你有能耐,劉珂,我覺得很對你不起,我一個大男人成了一個窩囊廢,讓你受苦了。劉珂說志明你不要這麼說話,我們是夫妻,有難要同當的,如果真象別人說的那樣夫妻是風雨同舟,落雨逃走,哪還叫什麼夫妻?你也不要急,先在家裡休息幾天,然後再到職介所之類的地方看看,有合適的事情就找一個來做做,不行再跳槽,現在我們不比從前了,你不是說過的,我們是自由人了。好在我們以前積攢下一點錢,還能領一點下崗工資,粗茶淡飯不會有問題的。虞志明說我總覺得我很沒有用,你媽媽說得是對的,你真是要吃苦了,哭的時侯要到了。劉珂說志明你再說這種話我要不高興了,這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媽媽現在還不是在幫著我們?如果她不幫我們帶亦珂,我們還要難做。
夫妻倆邊說邊吃,一頓飯很快就吃完了,虞志明自高奮勇要洗碗,這在兩人的生活中還是不多見的。虞志明說你明天要上班,今晚早點休息,養足精神,頭一天就給上司留下一個好印象是相當重要的。劉珂說我也想通了,下崗就下崗,換個活法而已,說不定就時來運轉,過上好日子了。
次日,劉珂起了個大早,看看時間還早就到菜場把菜買了,告訴虞志明她中午就不回來吃飯了,要他自己做飯吃。穿衣服的時侯,劉珂徵求虞志明的意見,虞志明建議劉珂穿一套中式服裝,最能顯示劉珂的身材,又素雅大方。劉珂也正有此意,再說,劉珂除了這一套服裝還穿得出去,其它也是沒有什麼上檔次的衣服的。這套中式服裝還是劉珂與虞志明談戀愛的時侯去一家專做旗袍的店舖定做的。在量體裁衣時,服裝店的老板就不停地夸獎劉珂的身材好,最適合穿旗袍了,還建議劉珂做一件旗袍,劉珂雖然很希望有一件旗袍,但她知道穿旗袍的時間畢竟有限,就忍痛割愛了,只做了一套計劃中的中式服裝。這套服裝是劉珂做姑娘時做的,現在結婚這麼多年了,穿著還是如此合身,可見劉珂的身材之好。
劉珂到賓館時,人事部的人還沒有上班,她問了總台的服務員,搞清了人事部的樓層和房號,就在一邊站著等。總台服務員打量著劉珂,問她是不是來應聘的?劉珂點點頭。服務員說你的衣服真好看,劉珂腆地笑了笑。服務員又說我叫傅小花,大家都叫我花花,你也叫我花花好了,說不定以後我們就是同事了呢。劉珂感激地看了花花一眼,心裡想這個名字怎麼跟寵物似的。花花說你可以到那邊去坐著等的,他們很快就會上班的。劉珂說謝謝你,我就站著好了。花花說你往門口一站,要迷死男人了。劉珂的臉有點紅了,花花說開個玩笑,等你上了班也是要穿工作服的,跟我一樣,沒有特色。劉珂看出來花花是一個愛說話的女孩子,頂多二十一、二歲的樣子,說話時,一雙大眼睛就一閃一閃的。劉珂喜歡這個多嘴的女孩子,只是想自己不過一個掃地的,如果花花曉得我是來掃大堂的,恐怕就不會對我這麼熱情了。
劉珂到了人事部,接待她的正是昨天在職介所見過的的那位招聘人員。從他的自我介紹中曉得他姓李,是人事部的經理。劉珂就叫他李經理。李經理見到劉珂時也有點吃驚,心裡想這樣一個魔鬼身材的女子去掃大堂真是有點可惜了。李經理把負責大堂的經理叫來,將劉珂交給他,說從今天開始由她負責大堂的衛生,要大堂經理具體交待劉珂做哪些事情以及應該注意的事項等。劉珂到更衣室換了特制的工作服。和總台不一樣的是保潔工的服裝在顏色上是有區別的,一看就曉得是要低一個檔次的。
劉珂到大堂時,特意到總台哪兒跟花花打了個招呼。花花一見,說你幹這個啊?劉珂笑著點點頭。花花說也好,都一樣,反正都不是人幹的活兒。劉珂當作沒聽見,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半天下來,劉珂發現,保潔工這活一點都不難,比做擋車工要輕鬆多了,也不用動腦子,只要低著頭把地拖乾淨就行。拖完一遍可以到休息室休息一會。就這樣周而復始,象一個機器人一樣,倒也少了許多煩惱。劉珂在拖地時是不允許東張西望的,她利用直起腰擦汗的功夫觀察過大堂,發現在大堂一側的茶座邊上擱著一架鋼琴,大堂很高,上面是透明的玻璃,陽光經過過濾照進來,顯得十分柔和,大堂裡到處都是綠色植物,就象身處一個花園。劉珂對這個工作環境頗為滿意,在大堂上班最為令人頭痛的是撞見熟人,劉珂對這一點有些無所謂,劉珂想我認識的人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到這種賓館來的,再說就算撞上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人只要想通了真是什麼事情都好辦了。
花花上的是早班,交接班後她到休息室來找劉珂,要跟劉珂聊天。劉珂笑著說我是頭一天上班,你這樣會敲了我的飯碗的。花花說你不用怕,我是來告訴你幹活的竅門的,早、中、晚尤其是晚上是賓館的高峰,這個時侯你出去拖得勤一點,平時你稍稍延時一點沒人會說話的。劉珂說謝謝你。花花一笑,就露出兩顆雪白的牙齒,劉珂說花花你是不是屬兔子的?花花說你會看相?劉珂說不是的,因為我也是屬兔的,劉珂一笑,固然也有兩顆白牙露出來。花花說那你跟我同年?劉珂說我要笑死了,我都要比你大整整一輪,大十二歲。花花的眼睛就盯著劉珂不放了,說一點都看不出來。又問你用的是什麼護膚用品?劉珂說我不用的,我只在冬天用百雀靈的。花花說百雀靈是什麼東西?哪個國家進口的,很好嗎?劉珂笑出聲來,說花花我要幹活去了,你還是回家問你媽去,你媽一定曉得百雀靈是哪個國家進口的。花花說我先走了,隔天我要請你去喝茶的。劉珂說隔天的事隔天再說吧,我真的要出去拖地了。
負責大堂衛生的有兩個人,一天份兩班,劉珂在交接班時見到了自己的同事,是一個男的,這是劉珂沒有想到的,總以為打掃衛生的事總是要女的做才合乎情理,現在看來,這生活裡的事也不是有完全一定的規矩的。做著做著規矩就形成了。劉珂換了衣服回家,才感到拖一天的地也是很吃力的,真是有點腰酸背痛了,她用手揉著腰肢,進了家門虞志明依然不在,劉珂想他可能去職業介紹所了,也沒放在心上,先在床上躺了一會,才起來做飯。劉珂打開冰箱一看,早上買的菜原封不動,說明虞志明中飯沒有在家裡吃。劉珂燒了兩個人的飯,又把菜洗了切了,只等虞志明回家就動手炒菜。房間裡是不能擱煤氣灶的,炒菜就要到門外邊去,好在住集體宿舍的大多是單身漢,炒菜的人家不多,要不然,樓道裡要煙霧繚繞了。
直到天黑,虞志明還沒回來,劉珂炒了一個菜先吃了,看了一會電視,睡意就襲來了,她實在熬不住了,就先洗了上床睡了,不一會,就睡過去了。
虞志明開了門,見劉珂已躺在床上睡著了,就躡手躡腳地把門關上,站在床邊欣賞著妻子的睡姿,劉珂睡著的時侯雙腿彎曲著,一只手搭在腰部,一只手懶洋洋地擱在枕頭邊,眼睫毛在一顫一顫地動著。虞志明很少這樣聚精會神地看過妻子的睡態,也許是以前自己不懂得珍惜,現在生活起了變化,才曉得親人的重要。
虞志明洗腳時碰響了盆子,劉珂就醒了,她睜開眼,見是虞志明回來了,就說你還沒吃晚飯吧?我給你做去。虞志明說我已經吃過了,你繼續睡吧,幹活是不是很累?劉珂說你真的吃過了,你是在哪兒吃的晚飯?虞志明說我也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也找到工作了。劉珂說是真的,在哪裡上班?虞志明說是一家報社的廣告部,是我從前認識的一個記者介紹我去的,收入根據廣告提成。劉珂說這可得好好慶祝一下。虞志明說不忙,等我拿到了第一筆提成再慶祝不遲,現在你需要做的是睡覺。劉珂說你要先抱我一下我才睡的。虞志明就過去抱劉珂,劉珂象一只貓一樣地偎在虞志明的懷中,很快又呼呼地睡著了。虞志明知道劉珂是真累了,他輕輕地將劉珂的頭放到枕上,在妻子的唇上吻了一下,淚水就掉了下來。
虞志明確實是在一家報社的廣告部工作,但沒有廣告就等於沒有工資。現在的媒體廣告基本份為兩大類,一類是大的報刊電台電視台以及實力雄厚的廣告代理公司,他們幾乎控制著廣告市場的絕大部份份額。還有一類就是小報小刊和那些二、三流電台電視台,他們的廣告來源全部是要依靠廣告部人員死乞白臉去拉的,拉到多少算多少,完全是處於一種無序而沒有保障的狀態。虞志明所在的報社廣告就屬於後者。在人員眾多的廣告人員中,一個月拉不到一筆廣告生意而分文沒有的是家常便飯。現在的廣告難拉是因為媒體的問題,真要做廣告的企業看中的是大媒體,他們寧可只吃好桃一只,也不吃爛梨一筐。而一些實力相對差一些的企業要做廣告又沒有足夠的資金,往往是廣告做了,錢卻收不回來。有一天企業倒了,廣告費也就一筆勾銷了。
虞志明知道憑自己的關系要拉到廣告是一樁不亞於攀登珠穆朗瑪峰一樣艱難的事情,但事已至此,虞志明已別無選擇,他想也許事情並不象自己想象的那麼糟糕,或許風水輪流轉,真會有一個高人在暗中相助,使我走出困境,從此柳暗花明呢。
日子的流水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很平靜地淌著。每天早晨,虞志明穿戴齊整了出門去,還挾著一只流行的黑色小包。劉珂不上早班的日子就繼續在床上睡覺。一到周末,女兒虞亦珂回來,房間裡就充滿了歡聲笑語。亦珂顯得很健康,她已經上幼兒園了,每天由外婆外公接送,給老倆口的生活增添了無窮的樂趣。亦珂似乎已經習慣了在外婆家的生活,對自己家裡既沒有衛生間也沒有陽台的房間顯得很不習慣。常常是星期天就要逃回外婆家裡去。虞志明夫婦倆樂得給老人一個人情,後來索性是亦珂星期六才回家,只過一夜就回去。劉珂從心底在譴責自己,但上班實在是太累了,虞志明也往往是一到家就攤倒在床上不想動彈,估計是出力又不討好。如果劉珂上的也是早班,一回家就只想睡覺,連夫妻生活也忘了是什麼滋味了,有好幾次,二人中的一個來了興致,但還沒漸入佳境,另一個就睡著了,弄得醒著的一個也索然寡味。劉珂想是不是自己已經老了,都說女人三十似虎,怎麼自己對這事總是提不起興致來呢?古人說飽暖思淫欲,我們吃也吃飽了,睡也睡暖了,如何就沒有強烈的要求呢?想來想去,劉珂想這都是活兒幹得太累了,精神太緊張了的緣故。劉珂覺得自己是找到了症結所在了,就要對症下藥,星期天跟老公女兒去湖邊喝喝茶,體驗一下休閑的生活,到了晚上固然起了變化。劉珂很為自己的調節能力而得意,虞志明自然也是曉得妻子的用苦良心的,盡可能迎合妻子的挑戰。
沒過幾天,賓館裡發生了一件事情。
這天劉珂剛一上班,花花就跟她說昨天晚上出事了。劉珂問出什麼事了?花花說有一個女的鑽進客人的房間沒多久,那女人的先生就上去了,結果就大打出手,我們都估計那女的先生是知道這件事情的,起先我們以為他們夫妻倆演雙簧,後來才曉得女的是個下崗女工,是瞞著他先生出來做的,先生自然是不肯做縮頭烏龜的,他一定跟蹤他妻子很久了,不然,他不會吃得這麼準的,一次就逮個正著的。
花花一口氣說完,也不看劉珂的臉色有點不大好。劉珂是聽花花說那女的是下崗女工臉色才有些不好的。聽花花說完,劉珂說這種事也難說誰好誰不好,說完就幹活去了。花花不曉得哪兒說得不好,看著劉珂離開,就很無趣地笑了一下,低頭做自己的事情。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命中注定,劉珂這一天一定要遇上一件事情。這天劉珂上得是夜班,吃過晚飯,她本想去找花花解釋一下上班時自己的心不在焉,但一看花花很忙就沒有過去,只是專心地拖自己的地。這時,鋼琴旁已座著一位穿黑衣服的女子,她每天幾乎都是穿同一件衣服,劉珂想也許她是有好幾套黑衣服的,只是因為她喜歡,所以才天天穿黑衣服的。劉珂願意上夜班,可以免費聽黑衣女子彈奏鋼琴。她和虞志明也曾夢想過為亦珂買一架鋼琴的,這對於他們來說當然是徹頭徹尾的夢想了,一來他們沒有這麼一大筆錢;二來就算買了鋼琴往哪擱?總不至於擱到集體宿舍的樓道上吧?
女子的雙手稍稍在鋼琴上空懸了一會,就很用力地按了下去,悠揚的琴聲就響起來了。劉珂欽佩一切對藝術有特長的人,她覺得他們真是了不起,一枝毛筆在他們的手中能龍飛鳳舞;一件樂器在他們的手中能彈奏出比流水更好聽的音樂。什麼時侯我的亦珂也能享受這些高雅的東西?也能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個?
劉珂在音樂的節拍中拖著賓館大堂的大理石地面,她沒有想到,今夜,在聆聽鋼琴奏出的美妙音樂聲中,有一個男人的目光始終在注視著她。這個名叫沃的男人已經在賓館大堂裡連續出現好幾個晚上了,每次來,他都會坐在一個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裡,從他坐的位置,又能看到大堂的中心,劉珂拖地的大部份時間都在他的視野之內。
劉珂象往常一樣,拖了一遍就到休息室去了,她知道自己是不宜在大堂久留的。她剛走進休息室,沃就跟了進來,劉珂嚇了一跳,說先生你是不是走借地方了?沃說我沒有走錯地方,我是沃。
劉珂一聽是沃,就呆住了。沃是劉珂的高中同學,是劉珂眾多追求者中攻勢最猛烈的一個,只是劉珂咬定青山不放鬆,在學校期間堅決不談戀愛,最後連沃也沒有碰上劉珂一指頭。後來沃考上大學,大家就再也沒有了聯系。劉珂不知所措,說沃你到這裡來做什麼?沃笑著說這兒是賓館,只要有錢是誰都可以來的,你難道不曉得就連毛主席住過的賓館現在也對外開放了。劉珂說我在上班,請你快點兒離開這兒吧。沃說劉珂你怎麼可以做這事的,這種事不應該是你劉珂做的。劉珂說我做什麼事情都與你無關,你走吧,老板見了會炒我的。沃說劉珂你不要怕,你會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的。劉珂說你真的應該離開這兒了,我求你了。劉珂說這話的時侯聲音已經顫抖了。沃說我會走開的,但你必須答應我你下了班要給我幾分鐘,我要曉得你為什麼會在這兒做的。劉珂說我答應你,這下你可以走了吧。沃說我這就走,我就坐在大堂裡喝茶,我等你下班。劉珂說你別等,我要很遲才會下班的。沃說我已經問過了,你不會太遲下班的,我會等你,我要不了幾分鐘的。
沃說完走出了休息室。劉珂一下子坐到在椅子上,全身無力。她一直以為自己在這裡做是不會遇見熟人的,想不到半路上冒出來一個消失多年的沃。過了不知多久,劉珂走出休息室去大堂拖地,她不時地去偷看鋼琴那邊,卻沒有見到沃,劉珂想也許沃已經走了。
劉珂下夜班已是午夜,她回家的車子有一路已經停了,因此她必須走上兩站路才能坐上另一輛車,這樣一來,她回家化在路上的時間就要超過四十分鐘。
劉珂從賓館大廳出來,左右看了一下,就發現沃站在一盞古色古香的貢燈下面。沃走過來,問劉珂回家要化多少時間在路上,劉珂想了想大約二十分鐘。沃說我保証你按時到家,現在,你跟我上車。劉珂說上車?上誰的車?沃說上我的車,我送你回家。劉珂說我不用你送的,我坐公交車。沃說你答應過我給我幾分鐘的,我不會耽擱你時間的,半個小時以後你就會到家了。
劉珂就跟著沃上了車。這是一輛很豪華的車,劉珂是叫不上牌子來的,要是虞志明,就會很內行地說出這是一部什麼牌子的車。車子緩緩滑出賓館停車場,向湖邊駛去,在一處綠樹濃蔭下停住了。沃說,好了,我們就在這兒消費掉你給我的幾分鐘。沃說劉珂你得告訴我你為什麼到這兒來做的原因。劉珂說沒有什麼原因,我在這兒做工度日,僅此而已。
沃說:“劉珂,你不要瞞我。你的事情我知道一些,我沒有別的意思,我只是想幫你。”
劉珂說:“你是什麼人,你有什麼資格幫我?我為什麼要接受你的幫助?”
沃說:“劉珂,我們是同學,就憑這一點,我們也是應該相互幫助的。”
劉珂說:“我過得很好,我不需要任何幫助。我憑力氣幹活掙錢,我不需要別人的施舍。”
沃說:“劉珂,你誤會了,沒有人要向你施舍什麼。作為一個老同學,我向你了解一下你的情況應該說不算過份吧?”
劉珂沉默著。
沃說:“如果你實在不想說,我不勉強你,但是劉珂你一定要記著,在這座城市裡有你的一個朋友在牽掛著你,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電話,你如果有事一定要給我打電話。”
劉珂接過沃遞過來的名片,裝進隨身攜帶的小包裡。沃說你坐好,我現在就送你回家。在快到劉珂的家時,沃說劉珂你沒有告訴我實話,這麼多的路你坐公交車只要二十分鐘?除非你會飛。劉珂說我們已經不是同一路人了,以後你不要再來找我了,謝謝你送我回來。劉珂下車時,對沃說了這些話。
劉珂走近家門,見虞志明剛從廁所沖涼回來,就問你怎麼弄得怎麼遲?虞志明說廣告明天要發出,今晚在校大樣,就遲了。劉珂也不太清楚報紙發廣告是怎麼回事,只說累死了,匆匆洗漱了就上床,卻發現虞志明已睡著了。
第二天,按規定劉珂倒班,她趕到賓館時,已遲到了,前一夜她下班已是午夜,早上又睡過了頭,真是一步遲了就步步遲了。路上又連吃好幾個紅燈,到了賓館遲了十多分鐘,這在劉珂到賓館上班以來是從未有過的,她一路跑著從員工進出的門沖進去,人還沒有跑進更衣室就開始解衣服的鈕扣了。等她氣喘著走進大堂,花花站在總台後面在對著她擠眉弄眼。
花花就是這樣,總喜歡跟劉珂開玩笑。劉珂沒有心思與花花打招呼,急急地開始拖地了。花花說劉珂你不要這麼賣力好不好?沒人會多發錢給你的。劉珂邊拖地邊問大堂經理巡視過沒有?花花說巡過了,還問我劉珂怎麼還不來。劉珂說這下死定了,我要被炒魷魚了。劉珂在心裡罵那個該死的沃,都是這個沃攪出來的事體,要不然,我也不會這樣沒心思的。正想著,大堂經理在叫她的名字了,劉珂的心就懸在空中了。她走到經理身邊,囁嚅著說我昨天是夜班,所以,早上起床有點遲了,加上路上又堵了。經理說誰要你說這些了,是總經理找你,你馬上上去一下。劉珂嚇出一身冷汗,連腳步都邁不動了。花花說經理你不要嚇劉珂,她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這份工的。經理說是誰在嚇劉珂?總經理有請總可以上去了吧?劉珂說我這就去。
劉珂到了總經理辦公室門口,心一直是狂跳著的,劉珂想就是我當了操作能手上台領獎時心也不是跳得這樣快的。劉珂站了一會,才敲響了房門。裡面有人在說“請進”,劉珂就大著膽子推門進去了。劉珂是從沒來過這兒的,劉珂以前總是這樣想:我是一個保潔工,與總經理隔著十萬八千裡,我最好是連認也不要認識總經理。
總經理問你就是劉珂?
劉珂說是我就是劉珂。
總經理說劉珂你把頭抬起來,難道說我很可怕嗎?
劉珂就把頭抬了起來。總經理說從今天起你不用在大堂拖地了。劉珂一聽,腦袋就大了,劉珂鼓起勇氣,迎著總經理的目光說:“總經理,我昨夜是做夜班,所以早上起床遲了,加上路上又堵了,我不是有意要遲到的,您可以扣我的工資,但請您千萬別炒我。”
總經理說:“你早上遲到了嗎?”
劉珂說是的總經理我早上確實遲到了。
總經理說既然你遲到了就應當扣錢,但這不是我管的事情,這件事情應該由你的上司負責。我要通知你的是從今天開始你不用在大堂拖地了,你告訴我你想做什麼?你又能做什麼?
劉珂說我還是做我的大堂保潔工吧。
總經理說除了保潔工呢?
劉珂說我只會做保潔工。
總經理說不見得吧?我看你就先做大堂副理的助手吧。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總經理打電話把人事部經理叫進來,要他帶劉珂去辦一下有關的手續。劉珂覺得這一切就象在演戲一樣,自己和總經理都是演員,這樣的事情是只能在電視裡才能見到的。劉珂搖搖頭,不是那種否定的搖頭,而是不相信一件突如其來的事情的那種搖頭。劉珂問那大堂今天的衛生怎麼辦?人事部經理說這你就不用管了,我會另外安排人做的。
劉珂換上了一套合身的西裝,跟著大堂副理進行實習。花花跑過來,說劉珂你一定是好人有好報的。劉珂說我也不曉得是怎麼回事,我總覺得這事有點蹊蹺,難道說真有從天上掉餡餅的事情?我想肯定是有人從中做了手腳,可是又會是誰會做這樣好的手腳呢?花花說不管它三七二十一,你先做著你的大堂副理助手,我看你的氣質,做個大堂總管也是篤定的。
這個助手做起來也並不難,也就是接接電話,聯絡聯絡上下左右的人。只是劉珂一向說慣方言的,現在一下子要改說普通話倒是有些不太習慣。這樣做了若幹天,劉珂將自己的事情跟虞志明說了,虞志明也顯得很高興,劉珂問報社那邊的廣告怎麼樣,虞志明含糊其辭,劉珂估計情況不是太好,又不敢多問,怕傷了虞志明的自尊。
劉珂的心情比起掃地時要好得多了,首先是穿的服裝就不一樣,都說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現在看來這話一點都沒錯。再加上劉珂現在是坐著上班,這一坐一站,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劉珂的笑用花花的話說本來就要迷死個人,現在,她是常將微笑掛在嘴邊,整張臉看上去就更加生動。
劉珂坐大堂大約十多天以後,接到了沃的電話。沃說劉珂我是沃,你先別掛電話,不然,我可是要投訴你的。劉珂沒辦法對著話筒發火,依舊笑容可掬。沃說劉珂你習慣新工作嗎?劉珂說我很習慣,如果你沒有其他的事情我要掛機了。沃說劉珂你下班後我可不可以請你喝一杯茶?劉珂說我從來不接受這種無聊的邀請。沃說我不是無聊,我是沃,是你的老同學沃。劉珂說我真要掛機了。沃說劉珂你難道真的不想知道餡餅是怎樣掉到你身邊的嗎?劉珂的心頭一陣豁然,劉珂想也許這事真得跟沃有關,要不然怎麼我前一天碰到了沃,第二天就換工作了呢。劉珂說你說吧。沃說下班後我在賓館停車場等你。劉珂掛了電話,心神不定起來。她看看表,離下班不足半個小時了。她趕緊給虞志明所在的報社廣告部打電話,回答說虞志明已經不在廣告部做了。劉珂問他怎麼會不做了呢?對方說我是新來的我也不是太清楚,可能是沒有客戶的緣故吧。反正我們這兒進進出出是常事。劉珂擱下電話,心裡忽然一陣一陣地涼,她想虞志明既然不在報社做了,怎麼不跟我說呢?那他現在天天搞得這麼晚回家,一回家又累得倒頭便睡,倒底在做什麼事情呢?劉珂心亂如麻,有點後悔答應沃了。但下班時間很快就到了,再要給沃打電話已沒有時間了,而且劉珂的身邊也沒有沃的電話。
劉珂走出賓館,就看到沃正站在他那輛流線型的車子旁,劉珂向他走去,沃就看到了她飄逸的身影離自己越來越近。沃拉開車門,做了個請的手勢。劉珂坐進車內,沃快速跑到另一邊上了車。車子很快就離開了賓館。沃看了一眼劉珂,劉珂的雙眼瞇著透過擋風玻璃望著前面。沃說劉珂你沒事吧?劉珂說我沒事,我很好,你有什麼事情就直說,我不習慣捉迷藏的。沃說我說了要請你喝茶的,我們邊喝邊說好不好?時間不會太長的。
車子在一家較偏僻的茶樓門前停下了。沃說,這兒的環境很幽靜,很不錯的,我們上樓去,可以看到湖水的。劉珂跟著沃上了樓,環境固然十分幽雅,裝飾古典,臨窗擺放著茶桌,茶桌與茶桌之間又用雕花木窗隔開來。沃在一張臨窗的茶桌旁,先請劉珂坐了,然後才自己坐下。沃就是這樣,總是處處顯出很有教養的樣子。在劉珂還是棉紡織廠的擋車工時她會以為這是一種做作與酸腐,在她坐了大堂之後她改變了這種看法,她也認為一個有修養的男人應該是這個樣子的。蓋碗茶是藍色花紋的,這是劉珂喜歡的顏色,茶是綠茶,水很清澈。因為時間還早,茶樓裡除了沃與劉珂再也沒有其他的茶客,顯得寧靜而安詳。夕陽從窗口射進來,正落在劉珂的臉上和身上,沃看著劉珂,在心中說,真是一個畫中的人,窗子就是畫框,背景是遠處的湖水和近處的柳樹。
劉珂說:“我來了,你好說了。”
沃說:“對對,我好說了。我說劉珂,我聽你們老總說你很勝任你現在的工作的。”
劉珂說:“你也認識我們總經理?”
沃說:“認識的認識的。我們是好朋友。”
劉珂說:“這麼說是你在背後搗的鬼了。”
沃說:“這不算搗鬼,劉珂,事實証明你可以做好比保潔工更重要的事情,這就是我看到的現實。”
劉珂說:“我感謝你的栽培。接下去你還會扔什麼樣的餡餅給我呢?”
沃說:“餡餅不是我扔的,是你應得的。劉珂,讓我們平心靜氣地說說話。讀書時我確實追求過你,也確實對你的拒絕一直耿耿於懷。但這並不妨害我們成為可以信賴的好朋友。“
劉珂說:“你又何必,你這樣做,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沃說:“我不要結果,我只要能看到一個好的過程就足夠了。劉珂,我曉得你一直過得很苦,你也有理由過好一點的生活的。我實話告訴你,我是你們賓館的董事,我現在不缺錢,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給你很多的錢,但我曉得你是不會開口的。我只是不願意看著我曾經那麼深愛的女子過著這樣苦的日子而於心不安。你一定要告訴我你心裡的苦。”
劉珂臉朝窗外,聽著沃說話,眼淚就無聲地流了下來。
沃遞給劉珂一張紙巾,劉珂擦掉淚水,端起蓋碗茶啜飲了一口。她說:“我下崗了。我愛人也下崗了。我們幾乎失去了所有的生活來源,我到賓館掃地是瞞著我愛人的。我告訴他我在這兒是做商務中心的營業員。他現在在一家報社的廣告部做,但我剛才給他打電話,接電話的人說他已經不做了,我不曉得他到哪兒做了。我覺得很吃力,也覺得心裡很慌,我怕會發生什麼事情,我也不曉得以後會怎麼樣。我們連房子也沒有,我想給女兒買一架鋼琴可是我又沒有錢。”
沃說:“你知不知道他供職的是哪家報紙?”
劉珂說了那家報紙的名字。沃說:“我知道這家報紙,發行量不大,拉廣告很難的。拉不到廣告就會自動炒自己的魷魚。但話又說回來,如果能拉到足夠量的廣告,提成也是很可觀的。”
這時,天色已暗了下來,茶藝小姐上樓端來幾根蠟燭,整個樓上就被燭光搖曳著了,是一種十分浪漫的情調。茶藝小姐問沃可以上菜了嗎?沃說你先下去,等會我告訴你。沃對劉珂說我請茶樓老板到附近的餐館點了幾個菜,如果你同意,我們就在這兒吃一點,權當是晚餐。要是你覺得不妥,我就叫他們把菜給退了。劉珂說菜都送來了再退回去不是浪費嗎,這樣好了,這頓飯我請。沃興奮地說你請你請。然後大聲對著樓下說:“小姐,上菜!”
菜端上來了,竟然是羊膀子、羊雜碎,還有一小盆手抓羊肉。劉珂的眼裡閃爍著驚喜而慌亂的色澤。沃說:“你喝不喝酒?”劉珂說:“我不喝酒。我要吃羊肉了。”
劉珂用手抓起一塊羊肉,不好意思地看了沃一眼,沃用鼓勵的眼神對著她。劉珂就大口地撕啃起來,邊啃邊說:“你也吃啊。”
沃說:“對,我也吃。反正說好是你請客的。”
沃看著劉珂滿手滿嘴的羊油,不停地為她遞著紙巾,又不停地為她面前的茶碗續水。
劉珂邊吃邊問沃:“這家茶樓的生意好像不太好,怎麼到現在還沒有茶客上來?”
沃說:“大約是這家茶樓地處偏僻的緣故吧。不管它,我們吃我們的,難得這麼清靜。民以食為天,吃是最要緊的。”
劉珂從洗手間出來,難為情地對沃說:“你吃得這麼少,都讓我一個人吃了。”
沃說:“你喜歡吃就多吃一點。我記得你讀書時是最喜歡吃羊肉的。”
劉珂說:“這個嗜好就一直沒變過。”
沃說:“你回家跟你愛人說,叫他到報社廣告部去上班,報社裡管這事的副總編是我的一個朋友。”
劉珂說我試試看,他這人自尊性強,我也不敢多說他。
沃說:“不是說大丈夫能屈能伸嗎?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總有一天會好起來的。”
劉珂說不早了,我得回家了。劉珂叫茶藝小姐上樓結賬,一問多少錢,茶藝小姐就報了一個數,劉珂脫口而出:“怎麼這麼貴的?”
茶藝小姐一臉微笑,說:“沃先生今晚包下我們茶樓了。”
劉珂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以為沒有茶客是生意不好,卻又是沃在搗鬼。劉珂說:“我就是做一個月也付不起這頓茶錢的。”
沃說:“那你就欠著。”
劉珂說:“我這一輩子從不欠人的,莫非真要一個銅鈿憋死英雄漢。”
沃笑出聲來,說:“是英雄就更要能屈能伸了,勾踐不也是臥薪嘗膽才笑到最後的?再說來日方長,下次你回請我喝一次茶就是了。”
兩人下樓,坐進沃的車,劉珂問沃在哪上班?沃說什麼時侯你來看看就曉得我在哪上班了。沃發動車子,又說:“其實是你不把我放在眼裡,上次我給過你一張名片的,上面有我辦公的地址的。”
劉珂想起沃真是給過一張名片的,也不知道塞得哪去了。又不好意思說出口。沃像曉得劉珂的心思似的,從名片盒裡又取出一張,遞給劉珂,說:“這一張你可別再沒見了。你真要有事找我,連電話也找不到的。”
劉珂將名片放好了,說不會了,我還欠你一碗茶的。
說著車子就上了城區最繁華的街道了。突然,劉珂看見一輛三輪車的車夫背影,這個背影劉珂是那樣的熟悉。她將雙眼貼在窗玻璃上,叫沃放慢了車速,夜色中,這輛三輪車似乎不堪重負,騎得很慢。沃的車以慢速超過去了,劉珂看見了騎車的虞志明,上身只穿著一件背心,脖頸上圍著一塊毛巾,下面穿著的一條褲子腳一直挽到了膝蓋。他的上身前傾,努力蹬著,每一下,看上去都顯得異常費力。汽車已經遠遠地把三輪車拉在了後面,直到隱入夜晚的燈光裡。劉珂淚臉如雨。她想起有一次她和虞志明坐三輪車,在上一個斜坡時,車夫騎得很沉重,到坡上時,不得不跳下車用手拉著三輪車上坡。虞志明說我們下車走走,等過了坡再上吧。劉珂同意了,虞志明先下車,劉珂正要下車,虞志明說你別下了,我拉你。虞志明從車夫手裡接過龍頭,讓車夫邊走邊休息一會,虞志明騎上車,拉著劉珂緩緩地上坡。這時,劉珂就看到了虞志明微微前傾的上身,每踩動一下踏腳,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氣。虞志明邊騎邊說,其實騎三輪也沒有什麼不好,累是累一點,出一身大汗,洗個熱水澡,睡一覺就恢復了,是很有利於身體的運動的。劉珂說那你做踏兒哥算了,看你一副白面書生的樣子,是該好好鍛煉鍛煉了。三輪車夫在這座城市被稱作踏兒哥。大家叫慣了也沒有覺得什麼不好。虞志明說,等到有一天我下崗了,我就來踩三輪,不瞞你說,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靠踩三輪車發起來的,他現在不光買了房,還買了車開出租了。我現在是捧著一塊雞骨頭啃啃沒有多少肉,扔了又覺得可惜。劉珂說你也是說說的,真要你踩三輪,還不累死你。虞志明說我是還沒到那個份上,真要到那個份上,我無所謂的,關鍵還是你,人家在背後說劉珂的老公是踏兒哥,你還不是要惱怒。說著,三輪就上了坡,車夫從後面一路小跑跟上來,說這位師傅騎車蠻地道的。虞志明跳上車得意地對劉珂說如何?連師傅都表揚我了。
沃將車子停在一個僻靜的路旁,等劉珂的抽泣稍許平息一點後說:“劉珂,我老早就有一個想法,現在說給你聽,你幫我出出主意。我們公司在城西投資開發的一個小區不久就要開盤了,廣告投入肯定少不了,加上其它的一些企業形像宣傳,每年的支出也是個不小的數目。我考慮再三,想自己搞個文化傳播公司,一則肥水不流外人田;二來,還可以承接外頭的業務。我分析了一下,中國的廣告業還是大有發展潛力的,只要做得好,如果能在創意上有新的突破,應該會有機會的。當然,真要搞好,除了投入,最要緊的是要有人。我想過了,讓你愛人供職過的那家報紙副總過來,另外再公開招聘一些專業人員。形式還是以股份制的好,要不然,又是搞不好的。”
劉珂已經停止了抽泣,她說:“這些生意上的事,我是不懂的,你還是聽聽你自己人的意見。”
沃說:“我想叫你愛人過來幫我。你不是說他以前是在企業搞宣傳的嗎?又會拍照。對這一套他應該熟門熟路的。如果你們有些錢,也歡迎入股,多少都行,當然,前提是如果你們信得過我。他來之後可以當副總監,協助總監的工作。蠃了是大家的,虧了算我的。”
劉珂說:“我們無功哪能受祿?再說他這半瓶子墨水,也不曉得行不行?”
沃說:“行的。你要相信他,給他機會。我就一向很相信自己的,現在要是給我一個市長當當,我也一定當得象模像樣的。”
劉珂說:“我回去以後跟他商量商量。入股的事就免了。我們確實沒有多余的錢,再說,我也不想讓他輕輕鬆鬆就掙了錢,以為有了依靠就困裡床壁了。”
沃說:“隨你。不過,你要給他打打氣,要他振作一些。相信我,劉珂,房子會有的,鋼琴也會有的。”
劉珂一笑,雙眼就瞇了起來,她說:“你送我回家。”
沃看著劉珂的眼睛,一陣心跳。這雙眼睛,曾經那麼讓他如痴如醉,曾經讓他徹夜徹夜地無眠。沃發動車子,車子很快地滑出樹的陰影,消失在夜色中。
虞志明直到午夜才精疲力竭地回到家裡。他先到廁所洗了一下,然後放輕腳步,開門進屋,正要躺下,電燈亮了。劉珂睜大雙眼仰臥在床上看著他。虞志明以為妻子想要那個,可自己實在累得不行,他說,我今天很累了,改天吧。
劉珂說:“報社廣告部的情況怎麼樣了?你從來不跟我說,我還是不是你的老婆?”
劉珂的聲音裡有少有的嚴厲。虞志明迷迷糊糊地說:“還行吧,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
劉珂一把掀掉蓋在虞志明身上的薄毯,說:“虞志明,你準備騙我騙到什麼時侯?”
虞志明一下子清醒過來,問:“你瞎說什麼,我什麼時侯騙過你了?”
劉珂說:“那好,既然你沒有騙我,我問你,廣告部的事情是不是很難辦?”
虞志明點點頭,說:“是難辦。這張報紙發行量小,拉廣告真是很難。”
劉珂說:“現在有一個機會,你想不想做?”
劉珂將路上沃的計劃跟虞志明說了。劉珂說:“沃是我們賓館的董事,他要公開招聘主創人員,我向他推薦了你,我還聽他說他準備叫你們報紙的副總編過來做總監。我想這樣也好,你們比較熟悉,容易共事。”
虞志明有點心動地說:“這樣當然是最好不過了,你們那位沃董事的公司一年的廣告做做也好發財了。只是我這個樣子,他怎麼會要我呢?”
劉珂鼓勵他:“誰生下來就能當老板的?還是一步一步自己闖過來的。只要你用心,一定會做好的。從明天開始,你不要到那邊去上班了,去書店買些書,在家好好充充電。你沒看電視裡的公益廣告,知識才能改變命運的。我們家的房子,亦珂的鋼琴我可指望著你了。你一定要有信心,你別忘了你可是我們家的頂樑柱呀。”
劉珂連吹帶捧,虞志明的自信就上來了,他說:“你看我的。我一定會好好用心的,我要做出一個樣子來讓他們瞧瞧,我虞志明也不是抬不起的阿鬥。”
劉珂伸出雙臂抱住虞志明的腰,說:“這就對了,這才像我的男人。”
劉珂是在正式當上大堂副理的第二天見到王婷的。當時,劉珂正在台前處理一樁顧客的投訴,說總台的五號服務員在接待顧客時出言不遜。劉珂知道五號就是花花。花花這些天情緒不穩定,估計是有事情。劉珂將顧客的投訴信壓下了,想找個機會跟花花聊聊天。花花是劉珂到賓館以後認識的第一個朋友,現在來了機會,應當有所回報。劉珂很清楚,這封投訴信到了總經理那兒,花花就死定了。
花花已下班,劉珂就給他打傳呼,想約她晚上出來喝茶。花花的傳呼沒回,王婷變戲法一樣地出現在劉珂的面前。王婷打扮得花裡胡哨的,嚇了劉珂一跳。一開始劉珂沒有認出站在面前的這個性感女人就是王婷。直到王婷開口說話,劉珂才反應過來。
劉珂說:“你怎麼穿成這個樣子?現在在哪呢?”
王婷說:“說來話長,一言難盡。我等你下班,我們一起出去走走。我知道你快要下班了。”
劉珂一看表,固然離下班時間只有十幾分鐘了。就說:“你先到邊上的茶座那兒座一會,我馬上就過去。”
劉珂和王婷在臨湖的茶樓落座。王婷從包裡取出一盒香煙,問劉珂抽不抽?劉珂搖搖頭。王婷點燃香煙,說劉珂你現在是有出息了。劉珂說還不是混一碗吃。劉珂問王婷離開廠子以後都到哪去了?
王婷說:“說來也復雜,也簡單。先是搭上了一個港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後來就被我老公發現了,大鬧一場,說起來好笑,這事還出在你們的賓館裡。老頭在你們那兒包了房,我們都以為人不知鬼不覺的,哪曉得他的鼻子比狗的還靈,居然找到賓館來了。再後來我們就離了。再再後來我就讓那老頭給包了,他每月給我五千元的零用,另外在城西給我買了一套房子,不大,倒也舒適。”
劉珂就想起自己還在做大堂保潔工時花花說得那樁事情,莫非當時的女主人公就是王婷。劉珂說王婷你對今後有什麼打算?王婷百無聊賴的樣子,說還有什麼打算,過一天算一天,趁現在還不老,用這身肉賣個好價錢,積攢一些錢養老。我曉得你要說我行屍走肉。你說像我這個樣子人不人,鬼不鬼的,除了給有錢人做妾還能做什麼?我又不是你,肯低頭在大堂拖地,這樣的事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做的。
劉珂說拖地是不見得有多麼好,可這總算是憑自己的力氣弄飯吃。
王婷說今天我不跟你探討人生。我問你虞志明現在混得怎麼樣?這個自以為是的小白臉讓你吃苦了吧?
劉珂說他現在在一家文化傳播公司做事,錢雖然不多,總算是做他喜歡的事。
王婷說這樣也好,人活著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已經很難得了。
從茶樓出來,王婷問劉珂想不想到她在城西的家裡去看看?劉珂說恐怕不方便吧。王婷說沒事的,老頭子每月只來一次,其余的時間都由我打發。你去吧,我們這麼長時間沒見了。劉珂想反正回家也沒事,就點了點頭。王婷到路邊攔下一輛出租,直駛城西。路上,王婷說我本想讓他給我買一輛車的,後來他沒答應,說他的公司受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影響,經營也不好。不過,他答應等情況好轉了就給我買的。劉珂說東南亞金融危機不是已經過去了嗎?王婷說是嗎?那他這次來我得讓他兌現諾言了。
說著,就到了王婷居住的花園,綠草遍地,房子設計頗為新穎。劉珂想什麼時侯我才能住上這樣的房子呢?
王婷的房子在頂層,王婷說我之所以買頂樓,是因為頂樓有一個閣樓,你上去看看,我在上頭舖了木地板,席地可睡的。劉珂爬上樓梯,閣樓布置固然別出心裁,一張席夢思舖在地上,床前還置著一面碩大的玻璃鏡子,劉珂不明白在床前放這麼大一面鏡子有什麼意義。忽然,劉珂就發現了床上的一樣東西,形若男性生殖器的塑料棒,還有一根電線拖在外頭。劉珂的臉就唰地一下緋紅了。她象看見了不應該看見的東西一樣有點做賊心虛,慌慌地下樓,王婷問她:“怎麼樣?還行吧?”
劉珂連連說:“很好。像童話裡講的一樣。”
王婷說其實這兒的房價也不是很貴,如果你們以後要買房,還不如買這兒,這裡的居住環境還是不錯的。我跟你說劉珂,這套房子的產權是我的,所以我也想通了,那老頭來不來都無所謂的,以後他真不肯付我那每月五千的賣身錢我也算是穩賺了。
劉珂不知應該怎麼回答,正躊躇著,王婷放在茶幾上的手機響了。王婷取過一聽,面露難色,說:“你不是說好明天才來的嗎?現在我這兒有朋友在的,不方便的,要不,你晚上再過來好不好?”
劉珂說是他回來了?我也該走了。
王婷說不是那老頭,是另外一個。我也不瞞你劉珂,我的生活是一團糟,老頭子力不從心,我獨守空房,總要尋點事體做做的。他比我年紀還要小,是在讀的大學生。跟他在一起,我才感到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滿足。
劉珂從王婷那兒出來,心裡悶悶的,她想不明白王婷是如何處理好這麼錯綜復雜的關系的,她用自己的肉體換取香港老頭的錢,又用這錢去養一個小男人尋歡作樂。王婷算是活得豁達了。劉珂想不是我不想弄明白,只是這個世界變得太快了,令人眼花繚亂了。
虞志明在沃旗下的文化傳播公司做副總監,象換了一個人似的。穿衣也曉得講究了,一有空就看書,還對劉珂說他要去參加自學考試。虞志明看來很欽佩沃,開口沃,閉口沃。還說做人要做到沃的地步才算是做人。劉珂說照你的邏輯,我們不算是做人了?虞志明說我這不是打個比方嗎。我們是算做人的,沃是做得人上人。
劉珂說志明沃也是一步一步這麼走過來的,也沒有多麼了不起,只要你肯努力,說不定你也會成為第二個沃的。
虞志明說你學會開玩笑了,劉珂,你是不曉得,沃的旗下有多少家產業?他一年產值的零頭給了我們,我們就是千萬富翁了。
劉珂不想再聽虞志明說沃,就說錢多有什麼用?男人錢多了還不是要變壞。虞志明我看沃不是這樣的男人。
劉珂說你又不是沃肚子裡的蛔虫,你怎麼會曉得他心裡在想些什麼?
虞志明說沃說了,要給我配一只手機,讓我跟你商量商量,買什麼式樣的好。我還從來沒有用過手機呢,現在一下子就要自己擁有了,真象是在做夢呢。
劉珂說這種事我不懂的,你自己看著辦好了。說完就要睡覺。
虞志明興致勃勃,要和劉珂親熱。不知為什麼,劉珂一點興趣也沒有,她想起王婷家閣樓上的那面大鏡子和床上的那根塑料棒,就惡心得想吐。虞志明見劉珂沒有回應,以為她累了,也不勉強,關了電視,拿過一本書來看。
花花打了辭職報告。花花跟劉珂說這事時,劉珂一點都不感到奇怪。劉珂想像花花這樣性格的人遲早要離開賓館的。花花說她要去一家夜總會做了。劉珂說我們賓館不也有夜總會的?花花說我不想在這兒做,這兒大家都認識,見了反而不自在。花花說站前台雖然衣冠楚楚,但一天立到晚,人累,錢又少,我做一個月還不夠買一瓶香水的。劉珂是無法理解花花的想法的,因為劉珂從來不用香水,所以她也想象不出不買香水與買香水的區別倒底在哪裡。劉珂說花花那些地方很復雜的,你要自己照顧好自己。花花說劉珂你放心,我心裡有數,我花花是賣笑賣藝不賣身。
劉珂想只怕到時你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劉珂沒把這句話說出口。劉珂說今天我們一起吃頓飯吧,我們在一起這麼長時間,還沒有正兒八經地坐在一起吃過飯呢。
花花說不了,你也忙,等過一段時間再說吧,我這就要走了。
劉珂點點頭,目送著花花的背影在自己的眼前越走越遠,直到看不見了才將目光從遠處收回。
沃給劉珂打電話,聽聲音好像是在很遠的地方打的電話,信號也不是很好。沃說劉珂我是沃。劉珂說我聽出來了,你在哪?在很遠的地方嗎?沃說我在青海,我是在茫茫的戈壁灘上。劉珂的心就有點緊張,劉珂說你跑這麼遠去幹嗎?沃說,我來看戈壁。沃剛說到這兒,手機信號斷了。劉珂貼在耳邊的話筒裡只有沙沙的雜音了。劉珂有點茫然,仿佛有一樣東西一下子掉在地上找不到了。她擱下電話,趕緊做事,卻老是出差錯,而且她的眼睛總是去看電話機,她希望電話會立刻響起,耳邊會出現沃的聲音。
電話鈴真的馬上響了,劉珂迅速拎起話筒,連“你好,這裡是大堂副理”的話都忘了說,就“喂喂”了起來。虞志明在電話那頭說你怎麼了劉珂,你沒事吧劉珂?怎麼跟掉了魂似的?劉珂說:噢,沒事,我剛從一邊跑過來。
虞志明喜孜孜地說劉珂,我這是在用手機給你打電話,你聽聽聲音效果好不好?劉珂說很清楚的。
虞志明說我後來買了個摩托羅拉的,牌子靠得牢一點。劉珂說好的,這個牌子好,你沒事的話我先掛了。虞志明說我沒其他事,就是告訴你一下我的手機號碼,你記一下。劉珂說號碼回家再說吧。說完就掛了電話。
這一天,沃再也沒來電話,他好像一下子人間蒸發了。劉珂失魂落魄了一整天,下了班,也是無精打採的。他沒有回家,去了父母家,亦珂剛從幼兒園接回來,正在看電視裡的兒童節目。見了劉珂只是叫了一聲媽媽,就不再理她了。劉珂就有些失落。父母見了劉珂的臉色,就說這段時間是不是太忙了?臉色這麼不好。劉珂說可能是忙了一點。母親說志明當了副總監了連丈母娘家也不來了。劉珂說媽你是知道他的脾氣的,以前來得也不多,他們公司剛辦起來沒多長時間,事情確實多一些,等稍微空一點,我們再一起過來看你們。母親說其實我也不是怨你們來得少,是看你們有出息了,高興的。人總是要往上走的,以前,我是說過一些不該說的話,但也是為你好。劉珂說媽我都曉得的。劉珂又說今夜我睡這兒,跟你聊聊天。母親說難得你有這份孝心,只是志明的晚飯怎麼辦?劉珂說不要緊的,他一般也是很少回家吃的,我給他打個電話說一聲就行了。這時,劉珂才想起自己沒有記虞志明的手機號碼。她打到虞志明的公司去,虞志明不在公司。劉珂要對方轉告她今晚住在媽媽家裡了。
劉珂給虞志明打電話時,虞志明正在用他的新手機一一給他熟悉的人打電話,告訴對方他的手機號碼,以及他上班的地址。當對方問他在公司裡的職務時,虞志明就很謙虛地說也就是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公司裡當個副總而已。好不容易打得差不多了,剛將手機放進包裡,手機卻響了起來,一聽,是公司裡的人打來的,說劉珂晚上不回家,住在她媽媽那兒了。虞志明說我知道了。心裡就有點鬱鬱的,想著要不要過去看看岳父母,想的結果是否決了自己的提議。虞志明一直對岳母在他和劉珂的婚事上表現出來的嫌貧愛富態度心懷不滿,只是一直不敢說出口來。虞志明現在是要臥薪嘗膽,做出點成就來給人看看了。
沃再給劉珂打電話時,劉珂就有點迫不及待了,她說你在哪裡?沃說我已經回來了,下了班你可以出來一下嗎?劉珂說可以的,你在哪等我?沃說了一個地方,劉珂一聽,就是上次喝茶的那家茶樓,劉珂說你還記得我欠你的一杯茶?沃說,是的,你自己說過欠我這杯茶的。
接完電話,劉珂就一直在等著下班。這天的時間在劉珂看來過得特別慢。下班的時間剛到,她就打了出租車回家,穿上那套中式服裝,然後又打出租到了茶樓。沃已站在茶樓的屋檐下了。他微笑著看著劉珂婀娜多姿地從出租車裡鑽出來,又裊裊婷婷地向自己走過來。劉珂看著沃的臉,沃的臉被高原的陽光曬黑了,是黑裡透著紅的那種黑。劉珂笑了,沃也笑了。
沃說我象不象昆侖山上的淘金者?
劉珂說我看你倒象可可西裡的藏羚羊獵殺者。
沃說可惜我沒有到達可可西裡。
然後兩人又笑了。
沃說我從戈壁灘上採了一些芨芨草和格桑花,不如這樣,我們去看看。劉珂說說好我請你喝茶的。沃說下次請也不遲呀。
沃說著就把車門打開了。劉珂已經無法控制局面了,她順從地彎腰鑽進車子。劉珂問你家在哪兒呀?我去會不會不方便呀?沃說劉珂,你不應該問這些問題的,我們是去看芨芨草和格桑花。劉珂就不響了。車子開出城區,到了一片面積很大的別墅區。車子在其中一幢別墅前停了下來。劉珂下車,別墅群大片地在她的眼前舖開去,到處都是綠色的草坪和馥鬱的桂花樹。夏天的晚霞在天邊火一樣地燃燒著。劉珂連做夢都沒有夢到過在這座城市的一隅還有如此豪華的別墅區。沃打開別墅的門,請劉珂進去。劉珂遲疑了一下,沃說裡邊一個人也沒有。劉珂就進去了。
劉珂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房子,她也從來沒有想過一份人家居然可以住這麼大的房子。除了樓下,還有樓上,裝飾居然可以如此漂亮。沃問劉珂喝什麼?劉珂說喝茶吧。沃就給劉珂泡了一杯茶。劉珂說你瞧,我又喝你的茶了,這樣,我就欠你兩杯茶了。沃笑著說如果這也算一杯,我是佔了便宜了。劉珂說你的花草呢?你不是叫我來看你從戈壁灘上採來的花草的嗎?
沃就從客廳的一角取過兩束花草,說這黃色的碎花就是戈壁灘上最著名的格桑花了,還有這種,也是戈壁灘上才有的芨芨草,它們都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只要一點點雨水就能頑強地生長。
劉珂輕輕地撫摸著芨芨草和格桑花,花瓣和草葉在劉珂的手指的輕觸下發出微微的顫抖。劉珂沒有去過戈壁灘,她也無法想象戈壁是什麼樣子,但她一直非常向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去見一見遼闊無邊的茫茫戈壁。
沃說:“劉珂,我在戈壁上見到這些美麗的格桑花,就想起你,那時我是那樣強烈地感到你就象這些有著頑強生命力的格桑花,我要告訴你我當時的感受,可惜我的話還沒說完,手機信號就斷了。”
劉珂說:“我沒有你想象得那麼好的。如果沒有你的幫助,我還是一個拖地的保潔工。”
沃說:“陪同我們的人告訴我,這些格桑花其實與幹花沒有什麼兩樣,插在花瓶裡可以放很長時間也不會乾枯。”
劉珂說:“其實,它的生命力最旺盛,離開了它的戈壁灘,它也是活不長的。”
沃聽了劉珂的話,就不知道說什麼好。劉珂一笑,說:“我是隨口說說的。”
劉珂問沃洗手間在哪?沃指著客廳的另一頭說你走過去轉一個彎就是。
劉珂按照沃的指點走向洗手間。沃緊張地看著劉珂的背影,直到劉珂轉彎了,才將目光收回來。
劉珂推開洗手間的門,就驚詫萬分了。
寬敞的洗手間變成了玫瑰花的世界。從進門的地上開始,撒滿了數以千朵的紅玫瑰,鏡子前,玫瑰被紮成了大束大束的,縱橫堆放著,浴缸裡已放滿了溫水,水面上漂滿了玫瑰花瓣。劉珂的腦子在一瞬間變成了一片空白。她不知所措地站在門口,然後,關上了門。她象被一雙神奇的手牽引著,她走到浴缸邊,緩緩地脫去中式服裝,接著是乳罩和內褲。她抬起一條修長而圓潤的腿跨進溫熱的池水中,平靜的玫瑰花瓣動盪起來,象一葉一葉的紅色小船在水面上盪漾。劉珂將另一條腿也跨進去了,她蹲了下去,雙手抱胸,水托著花瓣在她的胸前飄著,她進一步將身子浸入水中,伸出雙腿,舒展全身,這樣,她的整個身子就都被玫瑰花瓣裹著了,只有她的臉尚露在水面之上,看上去她象一個披著花衣的花仙子。劉珂無聲地浩嘆一聲,開始用手撩水,水與花瓣一起在她的手臂上滑下來,有的花瓣就粘在上面了,劉珂就用纖纖的手指去拈下來。漸漸地,一陣隱秘的沖動從下而上,在她的體內開始漲潮,她將手插入水中,玫瑰花瓣舖成的水面就劇烈動盪起來。劉珂閉起雙眼,水溫恰到好處地撫摸著她光滑的肌膚。
劉珂披著浴袍從洗手間出來,天色已漸暗,沃坐在沙發上,看著劉珂翩翩而來,她在窗前站住了,她面向窗子,背朝沃,沃的喉嚨發燒發緊。劉珂緩緩地解開浴袍的帶子,雙手向上,再向後一推,浴袍就無聲地滑落到了地上,這時,沃就看到了劉珂粘著玫瑰花瓣的背影。劉珂的身體曲線在西天最後幾絲晚霞的映襯下變作了一尊玉雕。這尊玉雕開始轉動了,劉珂轉過身來,整個裸體就面對著沃了。沃終於看到劉珂的身子了。他的心被劉珂的目光掏空了,不知飛到哪兒去了。劉珂的身上還粘著不少玫瑰花瓣,紅紅的,像一雙雙眼睛注視著沃。沃毫無意識地走過去,劉珂閉上了眼睛。沃走到劉珂的身邊,他聞到了從劉珂身上散發出來的花香與青草香混合在一起的馥鬱香氣。他彎下腰揀起浴袍,抖開,然後披在了劉珂的身上。沃張開雙臂,連人帶袍子一起抱緊了。
劉珂發出一聲酣暢的呻吟。沃說:“劉珂,你說得對,格桑花離開了戈壁,就算它的生命力最旺盛也會死去的。”
沃駕車送劉珂離開了這片別墅區。在進入城區時,劉珂執意要下車。沃沒有堅持。他將車停在路邊,劉珂從車子裡鑽出來,看了沃一眼,就朝前走去了。
沃忽然在後面說:“劉珂,你還欠我一杯茶的。”這時,就有一陣風吹過來,把沃的話吹散了。沃不知道劉珂有沒有聽見他說的話。
■〔寄自浙江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