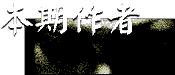一唱三嘆
到了秋天,顧言就四十五歲了。這個年齡對於顧言而言,可以說是一道分水嶺。在機關當了十年科長的顧言倘若在秋天以前不能解決晉升的問題,那麼顧言這一輩子算是活到頭了。組織部門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也有的說這個規定是發過紅頭文件的,不管發沒發過正式的文件,過了四十五歲這道坎的,再要提處級的,微乎其微,也可以說幾乎等於零。至少在顧言所在的機關是如此。
顧言對於自己能再往上挪一挪是早有想法的,十年前,顧言提了個科級,這在論資排輩的機關裡從年齡層次上看也算是往小的靠了,大家都認為顧言已被列入重點後備對象了,而且顧言在業務上的水平在機關也是有口皆碑的,提副處然後再提正處不過是遲早的事情。連顧言自己也是這麼想的,顧言甚至已經在心裡構思過當了處長以後如何管理處室的方略,很有點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感覺。
真是天有不測風雲,顧言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自己這個科長一當就是十年,這在機關是很罕見的,尤其是像顧言這個年齡段的人。每次機關人事調整,顧言就在等著上面來人跟自己談話,但每次都是落了空,使顧言化了不少心思準備的談話內容也統統化為烏有。
在這十年中,顧言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工作是無可挑剔的,不光是勤勤懇懇,也是很動了不少的腦子的,幫著處長做的事情處室裡的同事也都是有目共睹的。顧言當科長時的處長退休時,顧言經過比較周密的思考,認為自己是最有希望的,而且處長在退休前找過顧言,將他推薦顧言的經過都跟顧言說了,因為有這一層因素在,所以顧言也沒去做一些該做的工作,結果是大意失荊州,從外面調來了一位來當處長。這第二任處長明擺著是來踱金的,只當了不到二年就高升了。那一回,顧言為了不再次出現意外,特地跑到主管人事的副局長那裡做了一些工作,副局長對顧言的工作是肯定的。顧言為了把事情做得牢靠一點,還婉轉地提出可否先提個副處,這樣,一級一級上,比較符合局裡的規定。副局長對顧言的暗示不置可否,只要求顧言在人事的問題上不要太敏感,也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局裡會通盤考慮的。當時,顧言是一肚子的委曲,只是不便在局領導面前流露出來。
這一次,顧言又與處長這一職位擦肩而過,就連一個副處也沒有弄上。新提的處長依然是外面調入的,是下屬單位的一個老總,年紀比顧言還要輕。顧言覺得自己徹底沒戲了,有一段時間,顧言頗有點心灰意冷。顧言想前想後,思左思右也搞不懂事情出在哪兒,是哪兒卡住了。最後,顧言得出一個結論是自己官運不好,命中注定自己只能當個科長,就算能力最強,也當不了處長的。這樣一想,顧言的心情才稍稍有些恢復。
顧言的心情是好了一些,顧言的老婆李娜卻又發起了牢騷。李娜在一家自辦發行的報社發行站做事,主要的工作除了管理報紙發行員以外,還兼做一些內部的雜務,雖說沒有經濟上的實權,在站裡卻也是可以呼風喚雨的。比如她要叫一個發行員做一件什麼事情這個發行員是不敢不做的,如果他敢不聽管理員李娜的話,那麼他在發工資時一定會比別人少一些。而顧言就沒有這個魄力,顧言如果要處室的哪位同事幫著做一點事情,就要好言好語。而且還要看對方的臉色,如果恰好碰上對方心情不好,顧言也是要吃閉門羹的,機關是什麼地方?平起平坐的,表面上相互客客氣氣,心底裡誰賣誰的賬?這一切,都被李娜歸結為顧言不是處長的緣故。李娜說如果你是處長,你叫他們做事,誰敢不做?就算他們心裡有意見,當著你的面誰又敢說?這就是有權力與沒有權力的區別。當然,李娜想要顧言當處長還不僅僅是這一方面,其他的事情就多了,這處長就象一個結,一打開,房子可以換大的,工資可以拿高的,車子也可以坐小的了。最要緊的,是人活著的意義或者說價值就不一樣了。李娜堅決地認為,要做人上人,就要當處長,這自然是針對顧言來說的,如果能做局長那更是最好不過的事情,只是這個結總是解不開,解了十年了,好像越系越緊了,一旦變成了死結,那就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處長從面前大搖大擺地走過去而與己無關了。
顧言也認為自己在四十五歲以前當不上處長是一件很沒有面子的事情,簡直可以說自己的人生是很失敗的。科長算什麼?在顧言所在的這座城市,科長這樣的角色比樹上的綠葉還要多,一到冬天,說不準就成了一片枯萎的黃葉從枝頭掉了下來。等到來年春天,再生出無數的綠葉來,周而復始。而處長就不同了,處長就是四季常青的灌木了,到了局長,則是那些受到保護的古樹名木了,在樹身上釘上一塊小牌牌,誰見了都得澆點水,施點肥。
顧言回到家抬不起頭來,李娜也是要有話的,說顧言一點都沒有精神氣,在家裡都是這個樣子,在機關裡還會有生氣?這生氣是很重要的,這是一個人有沒有朝氣的標志。一個人要是沒有了朝氣,怎麼可能去領導其他人?這樣的人當了處長或者說當了局長,這個處或這個局不就要老氣橫秋,暮氣沉沉了?顧言不曉得李娜是從哪學來的這一套套理論,不聽不行,聽了又要頭疼。顧言想以前的李娜不是這個樣子的,李娜和自己談戀愛的時侯,還是一個很怕羞的女子,這十來年,就變成這個樣子了,從李娜身上,是一點也找不出從前的清純了。但顧言不敢將這話說給李娜聽,一說,李娜就又要給他上課了。說李娜不象從前的李娜了,也不是大實話,至少,李娜的外形沒有多少變化,還象結婚前一樣胖胖的。當初顧言跟李娜談戀愛的時侯,顧言的朋友們都是不太認可的,都認為李娜太胖了。顧言也是有過動搖的,但說實在話,李娜的胖是有曲線的胖,衣服搭配得當,還是很能彌補一些的。到了後來,顧言已是有苦難言,朋友們也是理解顧言的苦衷的。說到這個有苦難言,顧言一直認為是自己意志力不強的表現。當時,顧言住的是集體宿舍,是沒機會與李娜進行魚水之歡的。巧就巧在那年的五一節,機關工會組織大家到黃山旅遊,正在熱戀當中的顧言就沒有報名,這樣,集體宿舍就變成了單身宿舍。李娜一來,喜上眉梢,白天兩人出去玩,晚上回來,就感覺兩個人在同一個房間裡是不可能無所作為的。說不上誰主動,反正,經歷了那一夜,擋在兩人中間的那一道堤沒有了,沒有了堤壩的河水自然是要流的,是擋不住的。李娜讓顧言有了一種全新的體驗,而且也讓顧言覺得李娜的胖並不構成對他們今後婚姻生活的任何威脅。李娜恰到好處的胖讓顧言流連忘返,樂此不疲。
當同事們從黃山回來後,就象狗一樣皺起鼻子在房間裡到處嗅,說顧言一定是偷吃了葷腥了,要不然,這房間裡怎麼會有這種氣味的?顧言做賊心虛,不敢多嘴,趕快去買了香煙孝敬大家。大家說,如何,不打自招了吧?這就叫此地無銀三百兩。顧言也不多說,只是笑笑,這笑笑中,流露出來的已是幸福了。
在顧言還沒當科長以前,李娜對顧言的仕途也是不抱希望的,說到底,她跟顧言結婚,也是沒想過顧言是能當科長的。等顧言回家告訴她這個消息時,李娜就有想法了。李娜在目睹了當官的種種好處以後,為顧言的將來作了一個定位,那就是在仕途上發展。李娜對顧言說,以後我會全力支持你的工作,家務事我全包了。你是新人,要在工作上多化點心思,這也是你唯一的強項和優勢。李娜說你只有當上了處長,才有可能繼續向上走。但處長這一關是最難過的,就象埃及的金字塔,越往上就越接近尖頂。你一定要爭取在四十歲以前當上處長,不然,就不會有戲了。顧言剛當上科長,對未來也是躊躇滿志的,對李娜為自己設計的將來也是基本認可的。顧言想我只要努力,是一定可以的。
李娜固然也是說到做到,家裡面的事情一樣也不要顧言做,只要求顧言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還支持顧言去讀研究生進修班,化去了家裡的一大半積蓄,但李娜並不後悔,李娜認為,為了顧言的前途,家庭適當做出一些犧牲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而且也是必須要付出的成本。李娜說世上哪有又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道理?顧言對李娜的支持有點過意不去,顧言說,暫且不說我當不當得上這個處長,就算當上了,我也是不忍心老婆這樣做牛做馬的。李娜批評顧言是農民意識,放長線才能釣大魚,你想要做人上人,不在做人上人之前不付出怎麼可能?想坐享其成,像你我這樣家庭背景的連門都沒有。
顧言聽李娜這麼說,也不響了。顧言確實是從農村到城市來的,他先是考取了大學,畢業後分到了機關,這在當時並不稀奇,要是換在現在,不曉得會有多少雙羨慕的眼睛看著顧言。李娜也是普通的市井人家出身,身上也沒有與生俱來的富貴人家氣質,但好歹是從小生活在城裡的人,在一些生活的習慣上要比顧言透出一些文明。顧言不少的不良生活習慣也確實是在李娜的教育下才得到改變的。比如說顧言坐在飯桌前吃飯時,不自覺地就將一只腳擱到椅子上去了;再比如顧言穿西裝不習慣系領帶;說話時東張西望。凡此種種,如果不是李娜的監督和強化培訓,顧言是很難改變的。自從顧言當了科長以後,李娜對顧言生活習性上的要求就更嚴了。顧言以前上下班拎的都是一只舊得不能再舊的小皮包,李娜堅決把顧言的舊包扔進了垃圾箱,從此後,顧言上下班拎的包就不斷地變換了,基本上是與潮流相吻合。直到最近,手機盛行,李娜也是咬緊了牙關一定要給顧言買一個的。顧言不想打腫臉充胖子,李娜反對顧言的觀點,說這是必須的通訊工具,要是你跟處長一起出去,處長恰好沒帶手機而又需要打電話的時侯,你這手機就起作用了。顧言後來確實碰上過類似的事情,只是向顧言借手機的不是處長而是處室裡的同事。看著同事若無其事地與對方通話,顧言的心就一跳一跳的。要知道,平時顧言是從不開機的呀,買這只手機純粹是為了應處長以上的人物的急的呀,現在倒好,應了同事的急了。
第三任處長上台,顧言就覺得自己已是一個多余的人了。李娜也有點恨鐵不成鋼,這麼多年來的心血眼看就要付之東流,想想實在是不甘心,可又無計可施。老是對著顧言發牢騷,看顧言垂頭喪氣的樣子,李娜也有些於心不忍。經過一番心情的調整,李娜決定進行最後的一搏。李娜跟顧言說你也不要灰心,你不是還沒到四十五嗎?還有機會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顧言哭笑不得,但又不忍心掃李娜的心,也不關心李娜究竟又會拿出來一個什麼樣的方案。李娜經過份析,認為顧言屢次失利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工作能力不強,而是沒有搞好關系。李娜說看來我們以前認為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會得到相應的回報的觀點是錯誤的,業務能力固然重要,但在某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比方說現在就是關系比能力更重要。所以,李娜要顧言把今後的工作重點轉移到與領導搞好關系上來。顧言再次覺得了李娜的想法是不可行的,在這一點上,顧言是弱項,顧言不會喝酒,也不會抽煙,更不會搓麻將,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是顧言不會跳舞。這樣一個四不幹部,要想在仕途上繼續發展看來是很緲茫的一件事了。顧言看到了自己的弱點,對李娜的方案就不怎麼熱心。但表面上還是同意李娜的觀點的。
不喝酒、不抽煙、不打麻將、不跳舞,曾經作為顧言的四大優點,現在因為形勢的變化而變成了顧言的四大缺點。既然是缺點,就得改。李娜允許顧言可以適量地喝點酒,適量地學著抽點煙,也可以在適當時侯學一學如何與領導搓麻將的技巧,當然,在工作需要的情況下,也不妨進舞廳,學學跳舞。顧言的包裡確實備著一包香煙,而且還是中華牌的,但顧言從來不抽,就是跟領導在一起時,有了遞煙的機會也會忘了主動遞一棵煙給領導,等到別人在互相遞煙了才會想起自己包裡也是有煙的,但這時往往已經遲了,因為如果在這時顧言再遞煙給領導就顯得很不合事宜了。遞煙是要在很自然的手勢中完成整個動作的,這個動作如果沒有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訓練是絕對做不到這樣自然的,它是在有意無意中完成的,手勢的嫻熟看不出有一絲做作的痕跡,完全是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顧言在心裡嘆一口氣,想,我這一輩子也學不到這個份上。再說喝酒,顧言也是有機會與領導一起喝喝酒的,以前,顧言就只顧自己喝一點飲料,也從來不去向領導敬酒。顧言看著別人端著酒杯一桌一桌地輪流敬領導就很不以為然。現在,顧言也要改變戰術了,也要喝幹紅了,或者說喝白酒了。這要看主桌的領導喝的是什麼酒。顧言第一次去給領導敬酒時,領導就很驚奇,說是顧言來敬,我是一定要喝了這一杯的,顧言學著別人敬酒時說的話,說領導隨意,我幹了。說完一仰脖子一飲而盡,領導說你顧言都幹了,哪有我不幹之理,說完也幹了。顧言覺得領導就是爽氣,接著又到另外的桌上去敬,一圈下來,顧言就有些頭暈了,接著又有些眼花了。顧言趁人不注意,就提前退了席,到洗手間想把喝下去的給吐了,哪曉得喝進去容易,要吐出來就難了。顧言在洗手間“呃呃”了半天,只吐出一點清水來,頭卻像裂開似的難受。出來,就連走路也不穩了,騎自行車當然更不可能了,好在顧言的心裡還是清醒的,都說喝醉酒的人是人醉心不醉,顧言今天總算是有切身體會了。顧言打的回到家裡,李娜一看就嚇了一大跳,趕緊扶顧言上床,顧言剛在床上躺下,就嘩嘩地吐了一地。吐出來後,顧言才感到輕鬆多了。李娜的眼裡噙了淚水,默默地打掃被顧言吐臟了的地板,又為顧言洗臉。顧言說,李娜,我算是過了一關了,我發現其實喝酒沒有什麼難的,我連研究生都讀下來了,還怕一瓶酒不成?
經過這一次,顧言發現了自己的酒量,在要緊關頭是可以應付一陣的,尤其是在領導遭到圍攻時,自己就能出馬了。
至於搓麻將,顧言算不得是一個聰明人,他跟著同事學過一陣子,無奈顧言一聽到搓麻將時發出的聲音,頭脹痛得比喝醉酒還要難受。顧言也是陪領導去玩過麻將的,因為自己實在上不了台面,就在邊上看,看他們搓得興致勃勃,也只好硬著頭皮看下去。顧言不是不知道跟在領導後面要學會包容一切,但面對現實,顧言就有點應付不過來了。這時,顧言就十分佩服那些久經麻場的人了,他們在說說笑笑中裝作很肉痛地將錢輸給領導,其實心裡是在笑的。因為他們的任務就是陪領導搓麻將,就是將錢輸給領導,輸得越多,任務就完成得越出色。
到夜總會顧言也只能是袖手旁觀的,看著別人摟著窈窕的小姐在舞池裡旋來旋去,顧言只能坐在一邊做一個觀眾欣賞領導們的豐採。倘若有一位小姐來請顧言跳舞,顧言就會全身不自在,拒絕了小姐不光不給小姐面子,自己臉上也是沒有面子的,都什麼年頭了,居然還會有不會跳舞的男人。顧言知道自己在小姐的眼睛裡形像是十分糟糕的,但顧言想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顧言所在的部門每年有大量的接待任務,原先像進舞廳這類接待顧言是不插手的,更不要說象搓麻將這種讓顧言苦不堪言的應酬了。這些天顧言跟著跑了一些地方,才曉得當這個處室的頭真是不好當。
顧言的應酬多了,回家就沒有準了,李娜在這一點上是非常大度的,而且李娜對顧言到夜總會也沒有多少心虛的感覺,李娜相信顧言是不會落水的。但李娜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一個人常在海邊走,你不想下海,海浪卻是不長眼睛的,一不留神,浪花就把走在灘上人的鞋子給打濕了,這算是灘上走路人的錯呢,還是浪花的錯?
夜總會裡有一個叫薛蓮的女子,是在吧台上做的,見顧言每次都是帶一幫人進來,就獨自一人坐在一邊喝茶,等他們跳完了,就結帳陪著他們走出夜總會。薛蓮就有點好奇,象顧言這種角色的人薛蓮也不是沒見過,但大多是陪著客人一起活動的。顧言來得次數一多,就與薛蓮熟悉了,見了,就點點頭算是打了招呼了,薛蓮就泡一杯茶叫小姐送給顧言,顧言朝薛蓮笑笑,以示感激,薛蓮也回笑一下。有一天,顧言來得遲了,原先坐的位置就被人坐著了,顧言正在左右張望,薛蓮就舉手向他示意,顧言走過去,薛蓮說今晚人來得多,你就坐吧台旁吧。顧言不太習慣坐高高的吧椅,但別處已沒有空了,只好坐下了。薛蓮忙裡偷閑,跟顧言聊天,顧言就知道了薛蓮原來是個下崗工人,原先是一家頗具規模的棉紡織廠的質量檢驗員,工廠效益不好,一大半人下崗了,我找了不少地方,就到這兒來了。顧言說你怎麼到這種地方來做?薛蓮說我也是沒辦法,愛人單位也是半死不活的,眼看就要不行了,我愛人也是說下崗就下崗的人,在這裡做說出去是不大好聽,但收入也還過得去,況且我做得是這個,也不是什麼丟人現眼的事,你說呢?薛蓮這樣問顧言的時侯,就笑了,眼睛也瞇了起來。顧言言不由衷地說,是的是的,都一樣的。顧言想薛蓮比起那些舞池裡的女子是要好得多了,但錢一定是掙得不多的,凡事都是辯証的,要想得到的多就必須要付出的多。顧言就覺得自己真是幸運的人,李娜的工作說不上有多好,但至少旱澇保收,一家人生活著是沒有多大的後顧之憂的。
薛蓮為顧言續水時問他怎麼不下去跳舞?顧言說他不會跳。薛蓮說這年頭像你這樣的男人真是少見。顧言問,這樣是好還是不好?薛蓮回答說那要看什麼情況了,如果是做老公當然是這樣的人好了,要是做你現在這樣的工作,就不算是一個很稱職的人了,你要想得到上司的厚愛並繼續得到栽培有所發展就很困難了。顧言聽了薛蓮的話,想我真是一無是處了,看樣子真是走到頭了,你瞧,連一個夜總會做吧台的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這樣想著,顧言就從心底感到了一陣一陣的悲觀。薛蓮看了顧言一眼,一笑,說,我不過開開玩笑罷了,你的上司真要是有眼光的,你這樣的人就應當重用。顧言對薛蓮自相矛盾的說法不予理睬。薛蓮覺得自己話說多了,就忙著給顧言加水。
每次顧言有應酬,李娜就會先睡了,這一次,當顧言回家時,已是午夜了,李娜還沒有睡,顧言就覺得有些奇怪,問李娜這麼晚了怎麼還不睡。李娜沒說話,眼眶卻紅了,顧言就曉得家裡一定出事了,就放下包,走過去抱住李娜。李娜說小小出事了。小小是顧言和李娜的女兒,今年讀初三了。顧言聽了嚇了一跳。要李娜快說發生了什麼事情了。李娜說小小在學校談戀愛了。顧言說這怎麼可能?小小才十六歲呀。李娜說都是我們太大意了,自己的事顧得太多,對小小放鬆了。顧言一直認為對女兒不要管得太嚴,任其自然最好。顧言說你怎麼知道的?是老師說的?李娜說我下午到小小學校去了,老師向我反映了小小戀愛的事情,男的是同一所學校的,讀高二。顧言問李娜曉不曉得事情到哪一步了?李娜說老師也不是特別清楚,只要求家長配合,做做工作。顧言一時變得六神無主,在房間裡走動起來。李娜說我剛才跟小小談過了,小小沒有否認,你說我們該怎麼辦?顧言說這孩子怎麼一點不像你我呢,你我都是到了晚婚年齡才開始談得戀愛,這孩子。李娜說你也不要說這些無用的話,現在是要想辦法阻止小小繼續這段不正常的感情。
顧言說李娜,你說我們是不是對小小關心得太少了?我們太看重我的所謂仕途,反倒把女兒給耽擱了。李娜說也不能這麼說話,我們對小小也是盡了責任的,她的成績也一直在班裡名列前茅。說到小小的成績,顧言趕緊問小小現在的成績怎麼樣?李娜說我問了老師,成績沒有什麼明顯的改變。
顧言說還好。李娜說還好,還好個屁!再這樣下去,小小的成績遲早會下去的。這真是作孽啊,我這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小小小小這個樣子,你又是這個樣子。顧言說你也不要灰心,小小不是那種不可理喻的孩子,我明天找她談談。顧言覺得很累,就洗了上床要睡覺了。李娜忽然想起一件事,對顧言說晚上還接到你爸的電話,說你媽的身體不太好,叫你有空回去看看。顧言嘴上說好的,雙眼已經閉上了,不一會,就睡著了。
次日是星期六,顧言醒來後對李娜說,今天我們帶著小小一起出去走走,我們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出去走走了。李娜擦了擦蒙朧的睡眼,用手去摸顧言。顧言這才想起夫妻兩人也是很長時間沒有過性生活了。但顧言一想到小小,就沒了興致,對李娜說,晚上吧。李娜翻過身去,不理顧言,顧言知道李娜生氣了,又怕一早就弄出聲響,被小小聽見了不好。就撫摸了李娜一會,重復說還是晚上吧。說著就起了床。顧言想只要人還在床上,就難免受不了李娜幾乎裸著的身子,李娜看上去有點胖的身子在床上有很大的誘惑。
吃了早餐,顧言一家三口就打了出租去一個叫宋城的主題公園。小小說過好幾次要到宋城來,顧言一直沒有答應,顧言一直對類似的仿古公園抱有偏見,認為這都是現代人的一廂情願,搭起這麼一座公園也好叫城,豈不要讓古人笑掉大牙。但事實是顧言不去,依然是有很多人去的,而且今天,顧言也到這兒來了。
走遍了大半個宋城,小小的興致卻一直不高。顧言想趁李娜不在時與小小說說話。在宋街,顧言為小小買了一只陶制的塤,小小才顯得高興了一點,雙手捧著塤放在嘴前吹,卻怎麼也吹不出有旋律的音響來,顧言說這是最古老的樂器了,如果吹得好,聲音是很蒼涼的。小小放棄了吹奏的努力,挽起顧言的手臂,走路一跳一跳的,充滿了彈性與活力。小小雖說只有十六歲,卻已發育得很好了,個兒已超過了母親,身材卻比李娜要好,走在顧言身邊,婀娜多姿,象一棵正茁壯成長的小白楊樹。顧言是很為有這樣一個出色的女兒而驕傲的。顧言不時地轉過頭去看小小,小小被爸爸看得不好意思起來。顧言感嘆道:“小小,你真是長大了,一眨眼的功夫,我們的小小就長成了一個美麗的大姑娘了。”小小紅了臉,說:“爸,瞧你十五十六的都說些啥呀。”顧言笑著繼續說:“小小,爸爸有你這樣好的女兒,還要其他虛泡泡的東西有什麼用呢?”李娜在一邊說:“就是,看我們的女兒長得真是沒話好說,我走遍了宋城,也沒見到比我們小小更漂亮的。”顧言又接著說:“小小是爸爸媽媽最得意的作品了,足以傳世了。”
一家三口這樣開心地說著,小小的臉色就晴了。在城牆上,小小打炮還打中了一只狗熊,興奮得又笑又跳。在員外的女兒拋繡球時,那只紅色的繡球還不偏不倚地打中了顧言的頭。大家起哄要顧言上樓台與員外小姐相會成親,顧言在小小的竭力鼓動下就上去做了一回員外的女婿。只有李娜沒有任何收獲,顧言和小小就向她表示了慰問,李娜說你們有了收獲不就是我也有了?顧言聽後很是發了些感慨,說李娜是天下少有的好妻子好母親。說得李娜心花怒放。小小突然對李娜說:“媽媽,當初爸爸是不是用這樣的甜言蜜語把你騙到手的?”顧言李娜聽了就有點突然,面面相覷了一會,不知該說些什麼。在十六歲的初三學生面前,顧言和李娜第一次覺得自己的智慧是如此的有限,豈止是有限,簡直是貧乏。
在遊玩宋城的過程中,顧言終於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與小小談談關於小小早戀的事。吃過了晚飯,一家三口回了家,就在客廳裡坐定,正吃著李娜從冰箱裡取出來的西瓜時,小小開口了。小小說:“爸爸媽媽,今天我玩得很快樂。我也曉得你們陪我出去玩的目的。但我不在乎。你們要相信我,我會處理好自己的事情的。從明天開始,我不會再有新的麻煩帶給你們了。”
顧言和李娜相視了一眼,顧言說:“小小,你能這樣想,爸爸媽媽真是很高興,我們的女兒真是長大了。我們相信你的小小,你一定會妥善處理好這件事情的。”
淚水從小小的眼裡成串地滾出來,李娜忙去拿了毛巾替小小擦淚。小小哽嚥著說:“爸爸媽媽,我愛你們。”
小小這麼一說,顧言和李娜就忍不住落淚了。李娜抱住小小,說小小你真是媽的好女兒,都怪媽對你關心不夠。顧言如釋重負,說都別哭了,以後,每隔一個星期我們就去一個地方,由小小負責提供郊遊計劃,一家三口共同實施。小小聽了立刻破涕為笑,氣氛融洽得讓顧言好一陣感動。當天晚上,顧言和李娜也是興味盎然,雖然玩了一天有點累,上了床卻都沒有想睡的意思,小小這麼聽話懂事,讓夫妻倆虛驚一場,應該好好表示一下的。結果是李娜連著要了顧言兩次,搞得顧言第二天還有些腰酸,李娜譏諷顧言老了,不中用了,顧言也開玩笑說,那得請人幫助扶貧了。李娜說扶貧也是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的,得從自身找原因,對症下藥,李娜找的藥是托人從西藏搞了根牛的玩藝切成一截一截的浸了白酒要顧言每天喝上幾口。顧言一看切成片的牛玩藝就想吐,無奈李娜在一旁監督著,只好閉著眼睛喝下去,權當是吃藥。
女兒的問題解決了,顧言自己這一頭卻不太平了。且說這一天顧言到夜總會,發現薛蓮的眼睛紅紅的,一看就知道是哭過了。顧言問怎麼回事?薛蓮說沒事。直到快結束時,顧言又問了一句,薛蓮才告訴顧言,是她愛人下崗了,這些天心情一直不好,總是喝酒,喝醉了就打她。顧言聽後有點不太相信,覺得現在的男人是不該打老婆的,有本事就到外面掙錢去,打老婆算什麼本事。顧言也不知道如何安慰薛蓮,只是說他剛下崗有個心理上的適應過程,你要多給他一些關心和鼓勵。薛蓮點點頭,輕聲對顧言說謝謝。
又過了幾天,顧言接待了一批客人,就住在夜總會所在的酒店,因為人來得比較多,加上來的客人與顧言所在的機關關系非同尋常,處長就決定多包一個房間讓顧言晚上睡在酒店,客人有事也叫得應。接風酒喝了照例是安排活動,桑拿的桑拿,遊泳的遊泳,打保齡的打保齡,跳舞的跳舞。顧言負責跳舞的一拔客人。他照例是泡一杯茶在吧台邊坐著,薛蓮的眼睛還紅著,顧言說還這樣?薛蓮點點,顧言說這就不像話了,下崗又不是他一個,總是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薛蓮說都怪我命生的不好。顧言說也不能這麼說,也不是哪個人生來就一定是好命的。
顧言負責的這一批客人沒有跳多長時間就回房休息了。顧言又到其他的幾個場地看了看,也都差不多散了,就放心地回到自己的房間,洗了澡,給家裡打了電話,告訴李娜今夜不回家睡了,然後就取過一張報紙來看,卻怎麼也看不下去,鉛字間老是映出薛蓮紅腫的眼睛。顧言拿起電話給吧台打了個電話,正是薛蓮接的。薛蓮奇怪地說怎麼會是你?顧言說我今晚睡在你們酒店了,你待會下了班,要是時間還不太遲的話你就到我房間來吧。顧言遲疑地補充道,你可以來洗個澡的。薛蓮也遲緩地回答道,今晚客人少,我很快就可以下班了,你告訴我房號吧。顧言就把房號告訴了薛蓮。
顧言剛穿好衣服,門鈴就被按響了。顧言打開門一看,是薛蓮。顧言說這麼快的?薛蓮說其實你再遲幾分鐘打電話我就走了。事後顧言想這都是命啊,如果我的電話再遲打幾分鐘,薛蓮就走了,再如果我那天不住在酒店,也不會發生事情了。
薛蓮在沙發上坐了。這是顧言第一次在明亮的燈光下看到薛蓮,她比在吧台時看上去要年輕。顧言在心裡猜測薛蓮的年齡最多不會超過三十歲。薛蓮被顧言看得不好意思起來,臉就紅了。顧言問薛蓮要不要吃水果,每個房間裡都有水果的。薛蓮點點頭,又搖搖頭。顧言說你這是要吃還是不要吃?薛蓮的臉又紅了。顧言拿起一只蘋果削了遞到薛蓮的手上,薛蓮在接蘋果時手就與顧言的手碰上了。顧言覺得薛蓮的手很軟,是那種柔若無骨的軟。薛蓮咬著蘋果,問這兒的房間很貴的吧?顧言笑著說你不是這酒店裡的人嗎?你怎麼會不知道這房間的價格的?薛蓮的臉又一紅,說我們是最底層的打工的,不會去關心這些事情的。薛蓮吃完了蘋果,顧言說,你要不要洗個熱水澡?薛蓮問方便嗎?顧言說沒有什麼不方便的。薛蓮就走向了衛生間。
當薛蓮洗好澡從衛生間出來時,顧言又一次發現薛蓮的美麗了。薛蓮的頭發披散著,臉紅紅的,眼睛烏黑地看著她前方的某一個目標。顧言發現薛蓮竟然穿著裕袍。這是顧言沒有想到的。事情正在朝著顧言原先沒有料到的方向滑去,顧言似乎沒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了。當薛蓮脫下裕袍露出線條優美的身體時,顧言一時沒有反應過來。薛蓮用眼睛示意著顧言,顧言無所適從,只感到一個雪白的女人裸體在眼前晃動著。事情完畢後,顧言撫摸著薛蓮身上的傷痕和多處的烏青,心疼得說不出話來。薛蓮的表現很令顧言吃驚,她瘋狂的程度令李娜也是望塵莫及的。這會,薛琴依偎在顧言的懷裡,嘴裡還在喃喃地說:“這樣的男人,這樣的男人。”顧言不知道薛蓮所指的是哪個男人,是自己?還是薛蓮的愛人?
當薛蓮離開房間後,顧言才如夢初醒一般地沖進衛生間,擰開水龍頭,嘩嘩地沖洗起來。顧言在心裡說我墮落了,我竟然跟李娜以外的女人做了這種事了。顧言想我還有什麼資格再去教育小小不能這樣,不能那樣?
次日,當顧言再次到夜總會時,看到的薛蓮與前一天判若兩人,簡直是容光煥發。顧言沒有坐到吧台邊去,而是盡量離開吧台遠一點。薛蓮似乎知道顧言會這樣做,也不計較,只是在過來倒水時輕聲對顧言說我下了班上去。顧言看著薛蓮張口結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薛蓮對著顧言笑笑,裊裊娜娜地離去了。顧言想我是真的無可救藥了,我居然沒有拒絕她。顧言神思恍惚地安頓好客人走進自己的房間,連澡也沒洗,就倒在了床上。時近午夜,顧言忽然從床上跳起來,迅速跑進衛生間洗了澡。薛蓮進來了。兩人幾乎沒有任何舖墊地就進入了角色。薛蓮給了顧言在李娜那兒沒有體驗過的過程,顧言閉著眼睛,在心裡說我徹底完蛋了,我再也當不了處長了,眼看就是秋天,這都是注定的,這個薛蓮,這個瘋狂的遲暮之夏。
在薛蓮將要離去時,顧言從包裡抽出一疊錢遞給薛蓮。薛蓮的眼神一下子黯然失色了。薛蓮用異樣的目光盯著顧言,說:“你把我看作她們一樣的人了。”顧言無地自容,自圓其說:“你愛人下崗了,你的工資也不高,我沒有別的意思。”薛蓮說:“我是工資不高,但我拿的錢一分一厘都是乾淨的。”顧言拿著錢的手不知往何處放。薛蓮又說:“你真要把我當作那樣的女人,你這點錢是不夠的,我的開價是很高的,因為我這是除我丈夫以外的第一次。”
說完,薛蓮的眼淚就流了出來。顧言走過去抱住薛蓮,說:“薛蓮,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我真是想幫幫你的。”
薛蓮從顧言的懷中掙脫身子,說:“我要你幫的不是錢。”說完就開門走了。顧言毫無知覺一樣地在門後立了好久。心想我又做了一樁錯事,我這大半生,總是不斷地做著錯事。顧言知道,薛蓮這一走,他們就算完了。顧言覺得自己像做了個夢一樣,還來不及回憶夢境,夢就醒了。
送走了客人,顧言就該回家睡覺了。面對李娜,顧言的心裡就有無比的歉疚,就想從各方面作些彌補。他特意調休了一天,這在顧言長期的機關生涯中是十分罕見的,他去菜市場買了菜,還打掃了家中的地板,擦洗了廚具。這很讓李娜納悶,說顧言你是不是做了對不起你老婆的事情了?顧言嬉皮笑臉地說我敢嗎?就是你借我一個豹子膽我也不敢呀。李娜說倒也是,憑你這個樣子,也不見得會有女人送上門。顧言聽了,方大出一口氣,想,這人活著真是不能做虧心事的,要不,遲早是要穿崩的。
晚上,顧言也是十分地賣力。李娜以為是分開了一些日子的緣故,就努力地配合著顧言。李娜說你今天發了瘋一樣的,會不會是喝了牛的那個東西浸泡的酒起作用了?顧言說我也不曉得,或許是吧。李娜說我們報社最近又有一批記者去西部採風,我再托他們給我帶一根來。顧言有苦說不出,又不敢拒絕李娜的好意,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也未必一定是喝了那酒才這樣的,說不定我心事沒了,心情舒暢了,又回到從前了呢。李娜說要真是這樣,那個短命的處長我們也不要當了,你看折騰了這麼多年,處長倒沒有當上,搞得我們夫妻倒是生份了,想通了,家是頭件事,家和萬事興,家裡的事沒有弄好,就算官做得再大又有什麼意思?顧言同意李娜的觀點。夫妻倆互相寬著心,心境似乎一下子開朗了許多,想想以前的日子真是活得太累了。顧言放下了心上的包袱,人也變得精神了。再去夜總會時面對薛蓮也磊落了不少,有時,也和薛蓮說說笑話。薛蓮對顧言也是不理不睬,像對待普通的客人一樣。顧言看到薛蓮的這個態度,就放心了很多。心想像薛蓮這樣的女子真是難得,真像她的名字一樣出污泥而不染呢。要是人的一生當中有薛蓮這樣的紅顏知己倒是一樁既浪漫又溫馨美滿的事了。顧言想只是我沒有這樣的福氣,好好的一段情緣被自己弄巧成拙。顧言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一點風聲,是在一次局領導宴請外省來客的酒席上,局長秘書透露給顧言的,秘書說機關最近可能要進行一些人事方面的調整。顧言問我們處室會不會動?秘書說這個還未定。顧言思前想後,得出一個結論,沒定就是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不動,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要動。動與不動都是因人而定的,假若處長出事了呢?處長一出事就得動了。顧言的心一動,一個惡毒的念頭跳了出來。顧言是早就掌握了處長的把柄的,每次請客人上夜總會,處長也是先要來轉一轉的,輪流與幾個熟悉的女子跳上幾曲,然後就神秘地消失了,只有顧言知道處長上哪去了。那幾個漂亮一點的女子每天總會缺席一個的。顧言負責結帳,自然是曉得處長包的是哪間房的。回到家裡,顧言把這事跟李娜說了。李娜說顧言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你要當處長,就只有現在的處長下去。顧言說我這樣做是不是太缺德了?李娜說也不能這麼說,是你們處長先做出了不仁的事,你不義是在後的。顧言被李娜這麼一鼓動,就下了決心。顧言想,我必須在秋天到來的時侯做好這件事,一定要天衣無縫才是。
秋天到來的時侯,機關裡就真的出事了。顧言所在這個處室的處長因涉嫌嫖娼被公安局弄進去了。顧言剛一聽到這個消息,先是下意識地嚇了一跳,坐在辦公室好長時間都沒有動彈,顧言在心裡再次重復了一遍事情的經過,直到確信自己做的事找不出半點破綻才心定下來。然後顧言就開始暗暗高興了。處長這次要是查實了,肯定是要免職了。處室不能一日無頭,自己這回是十有八九要柳暗花明了。這樣一想,顧言就出去靈市面了,各方面的說法不一,但大致的意思與情節是差不多的。顧言想,這一回看來是要來真的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處長嫖娼,免職處份是商量都不要商量的。從顧言了解來的情況大致如下,比顧言還要年輕的處長在酒店裡召暗妓被公安捉奸在床。大家都說活該處長晦氣,這種事情要多少有多少,偏偏他就被抓了。那天,恰好是全市大掃盪,各大酒店沒有通風報信的,統統一網打盡。本來,也是不會出事的,酒店裡的人通知有關房間時處長剛好出去了,回來就帶了一個女人,而且誰也沒注意這個女人是怎樣跟在處長後面進去的,那女人穿得一點也不像做那種事情的,看上去倒像是處長的夫人。正漸入佳境,門就被打開了。這個樣子,處長也是沒有話好說了,說女人是他老婆,連那女人叫姓甚名誰也沒弄靈清。在這個機關裡傳得活靈活現的故事裡面,沒有一個人會想到處長的出事是因為一個關鍵的電話為公安提供了可靠的線索,一抓一個準。
處長一直沒有上班,處室就沒領頭的了。顧言想我不能守株待兔,我應當主動出擊才是上策。顧言一方面多做一些原本應該是處長處理的事,另一方面想方設法接近管人事的副局長,顧言一直對當初副局長跟自己打的不痛不痒的官腔耿耿於懷,但事到如今,顧言是分得清孰輕孰重的。李娜在聽了顧言的情況介紹後也讚同顧言走主動這一步棋。李娜還對顧言說,眼看就到秋天了,我看今年的秋天對你對我們全家都是一個好兆頭。李娜還舉例說明說她們發行站後園的一棵楓樹本來已經死了的,不知何故今年竟活了過來,紅葉滿枝,好看得很呢。顧言自然也是興奮不已,十年的等待說不定就在今年的秋天有了結果了。但興奮歸興奮,顧言對處長這件事還是有些心有余悸,李娜安慰顧言:“無毒不丈夫,水已經潑出去了,你也不必後悔,更不要去想要不要收回的問題。誰都知道他是自投羅網,只要你不說,我不說,誰會曉得其中的奧秘?再說你這是為共產黨做了一件好事,清除了一個腐敗分子,讓你當處長也是應該的,就算是對你的獎勵也應當讓你做處長了,顧言你想想,我們都等了十年了,等得我頭上都生了白發了。再說一個人的一生有幾個十年?”
事情正如顧言李娜所料,只過了半個多月,處長就被免職了,同時宣布即日起由顧言擔任代理處長。顧言並不在乎這代理二字,這是遲早要去掉的,平平處室同事的心罷了。當天下午,顧言就抽空給李娜打了個電話,把這個好消息通知了她,李娜在電話裡開心得就差尖叫了,說一定要好好慶祝一下,下了班她就去買菜。顧言說晚上有應酬,慶祝的事改天吧。李娜通情達理地說,你現在是處長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顧言說你不是一直在盼著這一天嗎?李娜說沒錯,我是一直在盼著這一天,但這一天真得來了,我又有點說不出來的失落了,覺得你離開我們娘兒倆越來越遠了。顧言說你這就是頭發長見識短了,凡事總有得有失,再說我們這事明擺著是得大於失,你何必傷感呢?李娜說我是高興過了頭了。顧言說晚上回來再跟你細說,我現在要掛了。
下了班,顧言沒有應酬,他在機關食堂吃了飯就一直待在辦公室裡,直到天黑,才去了薛蓮上班的酒店。走進夜總會時,裡面還是冷冷清清的,薛蓮見了顧言,有些吃驚。她沒見顧言帶著客人,心裡已明白了幾分,也不說話,給顧言泡了一杯茶,顧言在薛蓮彎腰為自己斟茶時說:“薛蓮,我終於又喝了你斟的茶了。”薛蓮也沒看顧言,就走開去了。顧言一直獨自坐在那兒喝茶,即使後來進來的人多了,也沒人注意顧言。那些小姐都是認得顧言的,以為他又陪客人,而根據以往的規矩,顧言是從不跳舞的。顧言一直等到薛蓮下班,才提早幾分鐘走出夜總會,他在酒店外面的樹蔭下等著薛蓮。薛蓮走出酒店,推著自行車,她仿佛早知道顧言會在外面等著,看著顧言從樹下走出來。兩人走在馬路邊的樹蔭下,天色已晚,街頭已是行人稀少。顧言說:“薛蓮,我為自己的過失再次向你道歉。”
薛蓮淡淡地說:“都是過去的事了,你也不要放在心上了。也是我當時太沖動了。”
顧言說:“薛蓮,你能不能再給我一個機會?”
薛蓮說:“我想過的,結論是我們不可能再從新開始了。你是一個難得的好男人,是我太貪心了,我不應該去要一樣原本不屬於我的東西的。”
顧言說:“你為什麼不試著以另一種方式去要呢?”
薛蓮說:“我做不到的。我想要的東西就是全部,而你不可能給我你的全部的。這一點你比我更清楚。”
顧言覺得自己積聚了一個晚上的自信正在土崩瓦解。
薛蓮說:“天已經很晚了,我得先走了。”說完,薛蓮就騎上車子飛快地離去了。看著薛蓮消失在夜色中的身影,顧言才想起忘了告訴薛蓮自己已經當了代理處長的事了。
顧言充滿了挫折感地回到家,李娜和小小竟都沒有睡,在等著他回來。小小一躍而起,撲進顧言的懷裡,顧言猝不及防,差點摔倒。顧言自嘲地說:“你看,小小,爸爸是真的老了,連自己的女兒都要抱不動了。”
李娜說是小小一定要等你回來,說好事不應當隔夜,你看,小小還給你折了四
十五只紙鶴呢?你想想,今天是什麼日子?
顧言一看,房間裡掛得到處都是彩色的紙鶴。小小調皮地說:“爸爸你閉上眼睛。”顧言閉上眼睛,小小就將電燈熄了,顧言聽到了小小劃火柴的聲音,顧言突然想起今天正是自己四十五歲的生日。等顧言睜開眼睛,一只大大的蛋糕上插著蠟燭,正在燃燒,小小把李娜推到顧言面前,李娜從身後拿出一束紅色的玫瑰花,羞澀地說:“都是小小的主意。”顧言接過玫瑰,放在鼻子底下聞,就聞到了一縷縷馥鬱的香氣。顧言很為在此以前的行動感到羞愧。他用右手摟住李娜,又用左手抱住小小,用力吹滅了搖曳著的燭光。在顧言吹滅蠟燭的一剎那,顧言想起好久沒有回老家看看父母親了,上次父親來電話說母親身體不好,也不知道現在好點沒有?顧言想我已經做好了該做的事情,我得回去一趟了。小小打開電燈,顧言還在發楞,李娜推了推顧言,顧言才回過神來,說:“小小,給爸爸拿刀,我們來切蛋糕。”顧言就在小小的幫助下切開了蛋糕。顧言的四十五歲生日就這樣過去了。
■〔寄自浙江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