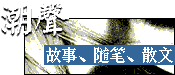情 書
“XX,你知道嗎?我已經注意你很長一段時間了。第一次見到你,你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是一封情書,確切地說,是一封代筆的情書。這是我在大學時期的業余愛好,最後甚至變成了一種職業。
你可能已經不記得那天了,那是一個春天的下午,準確地說,應該是傍晚,當時花兒盛開,你從禮堂門口向我走來,我感到你周圍的空氣帶著一種濕潤的感覺,仿佛和別人完全不同。
你的頭發是濕的,黑色的,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黑色。是那種讓人想要用手指觸摸的溫暖的黑色,披散在肩頭……
你或許已經忘記了我是誰。可是第一次見到你,我就感到了你的存在,奇怪吧?好多人天天和我相處,我甚至連他們的名字都想不起來,可是,當你第一次從我身邊擦肩而過的時候,我竟然感到了心痛。難道這就是他們所說的緣分嗎?
……”
當時,我大概是20歲左右,就讀於一所二流理工大學的計算機系。我們的學校說起來也算有些年頭的,但是和清華、天大那些真正歷史悠久的名校沒法比。它成立於1958年,我暗自認為,這晦氣的年份正好代表了我們學校的某種特色,即所謂的四三不靠。說來也是一所一類大學,但是因為座落於市區,無論規模還是師資力量都受局限,結果經營得還沒有那些熱門的二類學校紅火。周圍漸漸建起不少高檔寫字樓,把校園包圍在裡面,它日見憔悴,仿佛即將被都市蠶食。
就是在這樣一個局促的校園裡,我度過了一生中最為乏味的4年。我討厭自己的專業,因為是人就可以看出來,我和計算機毫無共同點。而且,我偏科偏的厲害,簡直沒有幾門專業課能夠順利過關。相反,凡是和文科有關的科目我都考的非常好,比如科技英語、革命史、邏輯等等。我能夠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就順利地通過英語6級考試,但是只要一涉及微積分、電路和編程,我就變成了徹底的低能。當時我也曾經苦思冥想來著,就是我為什麼會學計算機呢?
這個問題時至今日也沒有確切的答案。
漸漸的,我開始和周圍的環境疏離。大家把我當成了一個怪人,雖然比較離譜,但是因為我性格溫和,又是一部電影活字典,所以在宿舍裡還比較受歡迎。她們多少也容忍了我在早上抄作業的習慣。而且最後大家都默認了我的某些怪癖,比如聽交響樂,在床頭掛飛機模型……最後,如果我是在看課本被誰看到了,反而會令她們大吃一驚:“哎呀,出什麼事了嗎?”
到了這時候,我知道,自己總算是混出頭了。
我寫情書的專長是被一個同宿舍的女生發掘出來的,她當時對學校裡的一個高年級男生產生了瘋狂的“愛情”。我說瘋狂,是因為她愛上的那個家伙在我眼裡一錢不值,此人是學校詩社的社長,除去對老師溜須拍馬之外,他寫得一手汪國真似的濫情詩,最要命的是還經常搞什麼現場朗誦,以顯示自己的魅力。我一生中最為害怕兩件事情,一件是吃蔥,我簡直對蔥的氣味過敏到了一聞就想嘔吐的地步;另外一件事就是別人在我面前用那樣的腔調讀詩。每到這種時候,我總是站起來抱頭鼠竄。
說句實話,這不是因為我對此人有什麼偏見,而是詩這東西對於我來說太過重要,我總是覺得,詩被他人用功利的方式表達出來,無異於我自己當眾被人施暴。
不過這是題外話了。話說我的同學央求我替她寫一封信表白,也就是一般意義上的情書。我當時一揮而就,而她拿去寄給了那位社長,居然就成了。
就這麼簡單。
漸漸地,我開始小有名氣,我是說在寫情書這方面。來找我幫忙的人越來越多。一開始我還堅持把工作做足,比如和對方聊聊,看是不是要把他或者她的心情和經歷寫進去。後來,我幹脆就寫一些抒情段落,然後把該空出來的地方空出來,注明“以下的經歷你自己填寫”,就把這種模塊化的東西直接交給我的“當事人”。
對了,是模塊化,這是我當時唯一一個使用的和專業有關的名詞。
奇怪的是,人們真的喜歡我的這種服務,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要我幫他們代筆。這些人中,男生和女生的比例基本是一半對一半。如果在這之前,我以為女生是被追求的話,那麼現在我改變了看法。我們學校的女孩子中,有不少人是在主動地向男生表白,其原因,大概是其中一個女生所說的:“這年頭可愛的男生越來越少”。
有趣的是,男生們也在向我抱怨同樣的問題。
我寫的情書,幾乎很少出現重合的現象,也就是說,幾乎沒有一個男生給一個女生寫信,而同時這個女孩子也在給他寫的情況發生。從來就沒有什麼一拍即合的。一般來說,他們在要我代筆一兩封之後就會自動停止,銷聲匿跡,我蠻可以通過許多跡象判斷他們是否成功。實際上,男生相當沒有耐心,總是一擊不中就全身而退,女孩子又比較矜持,往往是一封信之後就不再表白。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是,和我有過此類交往的男生往往和我成為朋友,而女生卻會在事後盡量避開我。其結果就是,我在女生樓中越來越孤立,不過不是那種不友好的孤立,而是她們只有在感情出了問題的時候才來找我。
那封情書是我大三第二學期的作品。
這封信是我應一個個子不高的男生的要求寫的,他沒有告訴我是寫給誰的。事實上,時至今日,我連此人的名字也記不清了。只記得當時他沉默寡言,對我說要寫得詩意一些,有些“印象派”的感覺。我不由得對此人多看了兩眼,因為在理科大學聽到“印象派”這個字眼,猶如在剛剛裝修完畢的房屋裡,聽到從天花板上滲下水來,發出“啪嗒”一聲那樣古怪。
於是,我稍微花了點功夫寫成了本文開頭的這封信。既然對方好象頗為識貨,我的感覺就有點像交作文,還是經心一點比較好。這也是一種職業榮譽感嘛。
幾天後,他轉給了我一封信。信裝在一種我在市面上沒有見過的淡蘭色小信封裡,寫在同色的信紙上,用的是黑色的鋼筆,字跡整齊。
“這是什麼?”
“她回信了。”
我狐疑地問:“你給我幹什麼?”
“你既然寫了第一封,就好人做到底吧。”
……
就這樣,糊裡糊塗地,我開始了和一個陌生人的通信。或者確切地說,是和一個陌生女孩的情書往來。
“你真的願意花時間,哪怕一點時間來了解我嗎?現代生活的節奏是如此之快,我一直害怕自己在尚未被人了解之前就已經老去。信來得很有規律,幾乎是每周一封,總是放在我的信箱裡,淡藍色的小信封裝著厚實的信紙,外面套一個牛皮紙信封,上面寫我的名字。我只需要把回信和這封信放在一起,扔到232信箱,上面寫上“某某收”就行了。那是那個男生的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
你寫信的方式,是那樣的熟悉,仿佛我的確曾經感覺到你從我身邊走過……雖然你說的那一天我已經沒有了印象。
你願意和我通信嗎?先了解一下彼此?我說的是了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對方了解的……”
“我甚至不了解我自己……但是,我總是覺得有一種渴望,隱隱地在折磨我,我感到非常的寂寞,而且,我覺得自己正在失去什麼,是什麼呢?我也不知道。”
“能失去什麼呢?假如你是一只貓,然後你被迫說一種大多數動物都懂的語言,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只貓,還有某種奇怪的認記讓你困擾:‘別的貓都是怎樣生活的呢?’是不是能遇到別的貓呢?遇到它之後,是不是能夠認出來呢?別的貓是不是也不幸福呢?”
“我今天晚上聽了北方昆曲劇院的四折戲,分別是西廂記「佳期」、長生殿「小宴」、桃花扇「尋香」和牡丹亭的「驚夢」。啊,怎麼向你描述我的心情呢?這是多麼美妙的一種東西,尤其這幾折,都是男歡女愛,歡娛無限的感覺,中國戲曲在表演中的那種和諧,那種形式美,簡直是……旖旎,只能用這個詞來形容我的感覺。
然而,蘊藏在我們內心的那種古老的憂愁,又在其中一覽無余,那種繁華過後即是悲秋的哀愁,那種萬事乃過眼煙雲的悲哀,深深打動了我。今晚,我和幾百年前的愛情故事相遇……在這種時刻,我真的為自己的母語是中文,為自己有幸能聽到而愛上這些感到高興。”
“我在藍天白雲的早上感到憂傷,這麼一個美好的早上,或許我該遇到什麼人,愛上他,和他一起。然而早上醒來,我幾乎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最後才發現是在宿舍,馬上要去上課。要考試了,我覺得非常絕望,功課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一回事……沒有人了解我。”
“在這樣的學校裡學習,感覺像被陽光釘在了沙灘上,各種能動性統統地被乏味淹沒,寸步不能移。人只能眼看時間流逝,讓考試自己爬過來吞噬你。我老是想起恐怖電影裡的經典鏡頭,巨大的陰影向人襲來,人被恐懼攫住,在地上徒勞地一點一點移動……小的時候,每當看到這裡,我總是特別著急,甚至自己的腳在下面不停地亂搗,我老是想,他們為什麼就不能大步逃跑呢?
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不是不想跑,是根本動不了。”
“兩個人坐在樓梯上,不知怎麼的,就像談戀愛似的,男生女生分坐樓梯兩邊,之間隔著不痛不痒的距離,說話時眼神偶爾對望一下,粘住一回再閃開,漸漸地就恍惚了……其間無數的人上上下下,總要側身讓他們從中間穿過……”
反正當時我注意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個在和他,或者不如說是在和我通信的女生。
如此一來二去的,我居然開始盼望這些信,其急切程度,自己都感到吃驚。
因為我發覺,自己的的確確是在和一個什麼人通信。
那人不再是一個虛幻的目標,而是在某地存在著,而且能夠回應我。這是一種有來有往的感覺,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其實,我們又能寫些什麼呢?很多時候,我都感到,那些信與其說是寫給對方的,不如說是寫給自己的。
我卻喜歡上了這種不知所雲的氣氛。
可是,一想到接到我的信的人是個女孩子,而她又在把我,一個同性當成異性來傾吐,我就有一種錯位的感覺。
整件事情簡直荒誕至極,猶如兩面鏡子對放,讓從中窺看的人頭暈目眩,永遠找不到開始或結束的地方。
她到底是誰呢?
我一次也沒有見過此人和什麼女孩子在一起走,所以我無從判斷,那個女孩子的長相、身高、乃至是長發還是短發,也沒有人提供給我此人女友的情報。
似乎我自己也很矛盾,既想知道,又怕麻煩。
後來,我也沒有再追究這一切了。
因為在通了十封信左右的時候,一切突然嘎然而止。
再也沒有信了。
我每天都要看一下信箱,沒有信,什麼都沒有。
那個男生在此之前似乎總是在校園中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可是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那種惘然若失的感覺困擾了我很久。
直到有一次和數理系的人聊天,我才知道,他已經退學。
“退學?為什麼?”
“考試不及格吧?好像他已經好幾門補考不過了。”
“那他女朋友呢?”
對方困惑地說:“不太清楚,他老是一個人獨來獨往的。這人有毛病,他們宿舍裡的人都不太理他。”
……
漸漸地,我也把這件事情擱下了。
畢竟,沒有什麼是不能淡忘的。
再說就在這件事情之後,我開始了如火如荼的復習,那年的期末要考硬件裡的單片機原理,我記得,我就是從那時侯開始,有了神經衰弱的跡象。
我當時連走路做夢,都是在背書。
不過,也就是因為這件事情,我才發現自己當時是多麼的寂寞。
我漸漸把注意力轉移到身邊的世界上。
這樣一來,我看到的東西讓我自己都感到驚訝。
有一次,在校園裡吃飯的時候,我看到自己同宿舍的女生和社長在一起,不過她可一點也不像平時那副溫順的樣子。兩個人當時大概是為什麼事情吵起來了,翻了臉,我的同學抬手就給了對方一個耳光,聲音清脆之極。
社長一臉逆來順受的表情,仿佛已經習慣了。
我目瞪口呆。
也不知道社長曉不曉得,他被拉入這個溫柔鄉的陷阱就是我設的,真不知是該可憐他,還是佩服他。
現在都已經什麼年代了?
我才發現,自己簡直生活得如同一個完全被隔絕在人類社會之外的人。
這些信件只有使得我更加孤獨,從那時起,我開始拒絕再寫這類的東西,因為我感到,自己似乎被這種工作磨損得非常厲害。
也就是從那時侯開始,我決定開始所謂的“接觸社會”。
我試著用自己這點寫作和外語能力給一個報社做一些英文稿件的翻譯,既而開始撰稿。畢業以後,我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那裡的編輯。
3年後,我升職了,儼然成為了社會中的精英分子之一,這是當時在大學裡所有的同學始料不及的。當我發現自己混得還不錯的時候,多少也有點滑稽和錯位的感覺。
除去那些往來信的片段,我不再記得任何東西,那是當時我窮極無聊的時候,把它們抄錄在一個本子上的。
如果沒有這些片段,我甚至不敢肯定,自己也收到過和寫過這樣的信。
■〔寄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