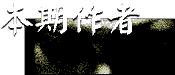吴晨骏,1966年5月 出生,1989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动力 系。后在一家电力研究所工作,1995年辞 去公职。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和小说写作至 今。在《人民文学》、《钟山》、《今天》、《 大家》、《作家》、《山花》、《江南》等刊物 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三十余万字。
·吴晨骏·
一 本 书
在第一页上教堂起火了
牧师到处找水
翻开第二页
鸟儿正在舔
红润的嘴唇
第三页和第四页
被先前读的人撕掉
第五页上有一滴
蜡烛的残骸
第六页告诉我
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
一个人卜卜卜敲了三下门
第七页是一些杂乱的谈话
从隔壁房间透过墙传来
第八页上有一个折痕
那人在此页停顿过
没有说明什么原因
也许他被人杀伤
第九页鱼儿再次游进河中
■
女人的著作
我梦里走在你身边,触摸不到你
你的细手,靠近我又离去的你
我触摸不到你的一丝头发,你神圣的
目光
你,一个高尚而洁净,在空气中散去的
身影
在空气中凝聚的女人,我们从草堆出
发
从草堆后面来到草堆前面,行走在
落满草梗的路上,我们从桥的这头,飞
身到桥的那边
经过工厂,冒烟的旧房子
总共三排,我们经过阴沉沉的天空
田野,还有死去的鸟,一串死去的鼠
我梦见你和你的芳香的躯体
我若不在梦中,无法明白你和你躯体
的特征
哦,音乐,你和我在一起,又不触及,
哦,你,一部
女人的著作所引起的无尽的伤感
■
熟悉的时刻
今天,我看到了什么?
房间里缭绕的烟雾
还是一台旧电视播映的
尼日利亚影片
今天,在约翰·列农的陪伴下
我看到了什么?
今天,我趴在桌前,看到了什么?
他们灵魂相见的地方
没有女人和法国香水
没有阳光,也没有草丛
烟缸盛满一个,又换一个
他们在房子的上空引吭高歌
今天,在这一刻,我看到了什么?
一只绿色的水瓶
和一根热水器
一只面包,和一桌面的面包屑
我看到停滞的时间,夜晚
以及之后的无数夜晚
一滴水,或一只电子闹钟
一本薄薄的书,一筒卫生纸
一个人长着又黑又密的胡子
今天,当熟悉的时刻靠近我
天上也没有飞机的轰鸣
虫子们都已歇息
我该干什么?我看到了什么?
当光线不再照亮面庞
就像我,只有一个在风中思考的头颅
它说明什么?开始还是结束?
哦,一个简单的读音,它充满了学问
今天,不仅今天,我看到了什么?
我在想什么?我端起茶杯
又为什么放下?
■
希 望 如 此
怀抱孔雀
怀抱一个极乐世界
在我身边
所有重量一并消失
怀抱绝望
怀抱光秃秃的秤杆
一只驴子骑在一个人上面
怀抱这一切
统治这栋楼
从切开的窗户看到
四个女孩
昨天我和朋友
经过她们时正驾驶着
两辆跑车
冲上高地
怀抱它们的尾巴
怀抱它们留下的大脚印
到处可见圆形花坛
任何影子都不会落在
它们上面
衔着一只鸭蛋
展开翅膀
渡过大河
它正被一座石桥跨越
■
鲁迅在上海
后来仔细想想,鲁迅当年在上海
给柔石支持,与瞿秋白过从甚密
是很奇妙,我读过柔石的文字
也欣赏瞿秋白的为人
至于鲁迅,大家都知道他的伟大
文学家鲁迅,早年写过不少小说
他去过日本,回国在教育部干过
似乎又曾与孙伏园合办《语丝》
最近一篇文章里介绍了他翻译过
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
从东北飘零到上海的萧红和萧军
也都得到过鲁迅的垂爱
鲁迅谈起文学经历,提到他的小说
大都在北京写成,似乎
到上海后,他只做些杂文
鲁迅故居里,我曾看到一份
他病逝后郁达夫拍的唁电
我喜欢郁达夫,也熟悉他的笔迹
像孩童的一般,歪歪扭扭,当年
鲁迅曾作诗,劝他不要离开上海
迁居杭州。郁达夫,徐志摩,萧红
与我都有很深的渊缘
有一趟我去浙江海宁,在一处
山坡上偶遇徐志摩的坟墓
想到他那么年轻就死了,很伤心
鲁迅与徐志摩,大概没有什么交往
大概早先亦曾有过,一两次见面。
据说鲁迅死时,萧军曾抚棺
痛哭,萧军又叫田军,萧红又叫悄吟
这些,都是我慢慢知道的
《域外小说选》是由鲁迅和
周作人共同翻译
史料记载周作人当汉奸颇为详尽
但谈及他们兄弟的关系则只一带而过
另外,现在还流行一种说法
周作人是个散文大家
鲁迅作品中很少
对周作人的评价
在初冬寒颤颤的空气里
阳光也不能让人温暖,我爱鲁迅甚过
爱我自己
■
血
如果我被它烧伤
如果一只鸡站在我头部
如果它是青色就像一棵树
走过的人就会死亡而且长大
如果它像高兴的麦子呈现黄色
它此时的面容就像手掌
它有力地转动从不停止
每当夜色降临时它就离开我
每当我路过时他们就叫我叔叔
我的肌肉就会闪光
每当我去乡村剃头
我总会冒烟和断裂
我不是漆黑之中的液体
(在一张桌子内部)
从来没有人会享用我
我将到河边挖出我扔掉的骨头
■
实在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我改变午睡的习惯
去河边读鲁迅的书
这一时期造成了我以后的失眠
对于失眠我几乎绝望
每当河边长满青草
蜻蜓在河面飞动时
我总感到虚弱和困倦
一棵大柳树向河面倾斜
中午的阳光把我拖向远处
即使黑夜我总处在
柔弱的纸船上
随手掐断岸边的一根小花
当我精力集中到某一点
花就在我手上变成一团水迹
■
高 二
新食堂在我上高二时造好
考完试我和一大帮同学去吃晚饭
夏天的傍晚空气中充满饥饿的气息
班主任问一个男同学怎么留刘海
我觉得那个家伙很讨厌
高考前我把一大捆书寄给
一个在汽车上认识的人
我已经很久不摸树皮
进入剥落的感觉之中
在深夜撬开窗户
从地板上体会到松软
半夜后天气很凉
我只能回味已不存在的寂静
同时我也看着月亮
我使出全部的力气把一样东西
扔到河面上
也没有人从隐秘处看我
我朝着河面发愣
在强光下比如正午12点以后的一小时
我也看过史蒂文森或者谁的
《绑架》,原版和译文我都看过
是从旧书店买的
书中有一些人的对话
我以为这就是文学
■
身 体 前 倾
他恶心地想,草已经长高了
他握住手指
使劲向外拔,看着遍地的草
狗跑过窗棂趴在草上
他忍住快要迸出的肺血
草都已经茂盛了,映出光芒
它们不是牧草,它们是一些老妇
它们从出生到熄灭
已经变成了打火机,他玩弄着它
扔到空中,“叭”,窜起火苗
草中已经充满了间隙
儿子穿着漂亮的衣服,他不是儿子
他忍住儿子带来的疼痛,想着妻子
妻子也已经长得丰满,就像这些灰狗
在草上舔地皮,儿子也已长大
他从男人转化为树,再也不能转化为
草
■
我和洗脚的女人
大片的草摇滚着
翻着波浪,女人
向脚盆里倒了些
热水,我又看见
大片的草中,站起
一只骆驼,一条毛巾
掉进脚盆,女人
舒服地洗着脚,大片的
草,从我眼前消失
只剩下一颗夕阳,一团
湿气,蒙上了女人
和我的眼镜
我摘下眼镜,流出了
泪水,一阵辛酸
我和女人走在草原上
我忽然涌起的
那阵辛酸
大片的草覆盖了我、女人
站着的我和
洗脚的女人
像音乐的刀子
割着我胸前的皮肤
女人身上,落满
飞机驶过时振落的
蛛网
■
·吴晨骏·
旅 途
小店黑老板从柜台后伸出好奇的目
光,在买烟的马吉身上扫来扫去。这人穿
一件不太干净的圆领老头衫,头发蓬乱,
像走了一天的山路。他可能是县里下来的
干部,也可能是过路的。“住在老杨家吗?--
我家也可以住的,比他家要便宜吓。几时
走?”黑老板自言自语,继而又训斥在柜台
旁探头探脑的小孩,“死进去,你个小虾子。”
马吉出现在小店以来只说了一句话,关于
香烟的牌子,甚至连这句话也没说清楚,
嘴里哼了一声。他接过香烟,迫不急待地
点上一根,走出小店。黑老板摇摇头,“你
个小虾子,还不死进去。”小孩的脏脸上露
出僵硬的笑容。
马吉走下小店门前的土坡时,黑老
板对小孩的叫喊声也从背后追上了他。他
继续沿一条两边长着竹子和榆树的小路,
匆匆行走。牛粪和狗粪的气味迎面扑来。
越过名叫富贵庄的村子,在灰暗的天幕上,
布满绵延不绝的山影。农舍中的灯火,增
添了暮色的浓重。经过篱笆围着的菜地和
一只粪坑,在大狗的吠声中,马吉推开一
间草屋的门。草屋和猪圈相邻,在正屋的
侧面。不知这家人是否姓杨--黑老板说的
那个老杨。这一夜,马吉在凹凸不平的床
板上睡得很难受。刚躺下时他遭到无数只
蚊子的袭击,他带来的蚊香一点也不管用。
而睡着后,他又接连做了两个噩梦,在这
两个梦之间,他去了一趟户外,站在朦胧
的月光中往菜地里撒尿。
前一个梦中,他用手枪瞄准了一个
裹着棉袄的孩子,“砰”的一响,孩子在枪
声中倒退了几步,仍朝他走来。他又开了
一枪,还是不能打死那孩子。他撒完尿重
新入睡后做的梦,则是在公园的门口。他
和朋友们在公园的铁门前拦住一辆出租车。
临上车前,他记起有个朋友还坐在街边的
长椅上。天阴沉沉的,似乎在积蓄着雨水。
从出租车边看去,长椅上的朋友背影发白。
那朋友要被人害死呢,梦中的马吉扶住半
开的车门想。果然,他看到长椅上多了一
个发白的背影,一个杀手,和那朋友并排
坐着。杀手轻轻地推倒了那朋友--现在是
一具尸体,因为杀手的匕首已悄无声息地
捅进那朋友的软肋。杀手拖着尸体,塞进
长椅下的空档。那倒是掩藏尸体的妙法,
马吉想。
早晨,被噩梦和蚊子折磨了一夜的
他,走出草屋,站在猪圈旁,清了清嗓子,
伸了个懒腰。昨晚灰色的山影在晨光中披
挂着绿色的草木。小店黑老板背着手,从
村头走来。他老远就向马吉喊,“你早啊。”
待走近了之后,他低声说,“住我家去,行
吗?我家的条件很好吓。”见马吉没反应,
黑老板怏怏地离去了。这人来富贵庄干什
么?他的神色不太对头,肯定不会是县里
下来的干部。来玩的?他怎么会独个出来
玩?这时,正屋的门“吱呀”朝里打开,这
家的女主人捧着一只木盆冲出门槛,喘着
气,昂着头,一口气把木盆端到猪圈旁边。
满满一盆饲料被掀在猪圈的食槽里。她抬
起憋得通红的脸,斜看着马吉,“呵,”她
干笑道。“呵,”马吉也对她干笑。“喽尔,
喽尔,喽尔,”女主人召唤猪圈地上的猪,
并用木棍在食槽里搅拌。
在房东家吃了一碗稀饭,马吉咀嚼
着嘴里的萝卜渣,经过菜地边一小截倒塌
的篱笆,来到村子中的小路上。他没有目
标地东张西望,偶尔他站在一棵榆树下,
研究着千疮百孔的树皮,而另一时刻,他
愣愣地注视村子边缘一片刚插完秧苗的稻
田。是否换个人家住呢?草屋里的蚊子确
实太凶了。马吉盯着村头坡子上的小店,
两个笨拙的石灰字“小店”刷在小店的山
墙上。但小店的客房也不见得有多舒服啊,
黑老板的殷勤只是为了赚钱而已。随着上
午时间的流逝,地面气温不断升高,马吉
皮肤上沁出了一层细汗。他在村口的榆树
荫里停下脚步,目送一直通向山那边的小
路。路边,成垄的豌豆接受着阳光的照射。
“嗨幺,嗨幺,”农妇挑着水桶,从
村子里走来,越走越近。到马吉站的树荫
下时,她把蒙在头上的毛巾扯下,原来是
女房东。女房东也看见了他,朝他笑,脸像
榆树皮似地裂开了。她在他脚边搁下担子,
用毛巾擦去脖子里的汗水。“我们这地方
落后吓,”她自嘲地说。“风景蛮好,”马吉
说。她把毛巾搭在头发上,“外地人都这
么说的。我们从小就住这儿,看惯了。”“
是啊,你们从小……,”马吉说。“我还得去
田里,”女房东挑起担子,“哪天叫我家死
鬼带你到村子旁边转转。”“不用,我能……,”
马吉说。女房东放开脚步,走进明亮的豌
豆田里。扁担在她肩上摆动,她臀部鼓胀,
过着农民的生活,除了农忙时节,平时没
有大不了的事情,倒也不错啊。空气中飘
过阵阵庄稼的茎叶蒸发出来的气味,喜鹊
在榆树上面乱叫。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