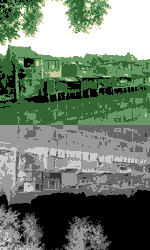
·楚 尘·
路 过 黄 村
……就这样我们到处晃荡, 一个冒牌者和一个仅仅的一半:既没有达 到存在,也没有成为演员。
--引自里尔克《马尔特札 记》
一
黄村是一个地名。虽然我们可以在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地图上找出若
干个与此同名的地方来,但我心里其实很
清楚,我去过的这个叫黄村的地方大概只
有一个,而且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跟我
的一位叫李德成的朋友能够扯上关系。李
德成是我在大学期间唯一的一位不是在本
校认识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南京的一个叫奥杰的酒吧里拿着一
把吉它自弹自唱,他的声音有点浑厚,但
不够圆润,大概是唱得不多的缘故,他的
演唱远不如他弹奏的指法那么娴熟。当时,
李德成的身边还站着几个黑人,他们手中
都拿着一把吉它,李德成后来告诉我,他
正准备与他们组建一个乐队,这是组建前
的一次友情演出。几个黑人朋友来自沙特
阿拉伯和阿联酋,他们在南京大学留学,
学习古代文学,李德成当时与他们一起讨
论给乐队取名的时候,他们一致想到了“
唐朝”,可惜,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组建乐队的事后来不了了之。几年之
后,中国的北京也出现了一支叫“唐朝”的
乐队,我知道的时候,心里颇有些不是滋
味,我想,要是当时李德成他们如愿的话,
恐怕几年之后的这个叫“唐朝”的乐队只
能另改名称了。我之所以对此事感到有些
遗憾,是因为组建乐队的事如果能够实现
的话,我大概也是“唐朝”乐队的一员了。
不过,这倒没有影响我们以后的交往,我
后来经常背着在大学里靠省吃俭用攒钱买
下来的吉它,去与他们交流,演奏我们自
己作词谱曲的歌。黑人朋友后来临走的时
候,我们还一起在北园的紧挨教学楼的那
个草坪上搞了一次小型的告别演出,我就
是在那一天认识李尤的。那是六月的一个
晚上,原计划本来是在我们几个人当中搞
一次自娱自乐的演唱,由于吸引了更多的
北园的朋友们,这次告别的聚会倒成了一
次不大不小的演唱会,我记得后来草坪上
的同学越聚越多,那个场面到现在仍让我
激动不已,我们唱了很多歌,到最后似乎
整个儿成了一个大合唱,那些围拢过来的
校友们情不自禁地与我们一起唱起来。后
来有很多校友碰到我的时候,仍对那一晚
记忆犹新,都向我声称那是他们大学期间
在北园度过的一个最美好的夜晚。
过了一个月,黑人朋友萨姆松等人和
李德成先后离校,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怀念那次告别的
聚会。虽然黑人朋友与我分手的时候一再
嘱咐我以后有机会去他们的国家聚聚,但
到现在我仍感希望渺茫,也不知要等到什
么时候才能碰面。见不到黑人朋友倒在常
理之中,可是毕业以后,我与李德成见面
的机会也一直是一个零,我时常跟李尤感
叹自己身不由已,按理说,如果真正想见
朋友的话,还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问题
是我总是抽不出时间来,总是把希望寄托
在下一次。我记得我和李德成最后一次见
面的时候是在那年七月底,当时我和李尤
已谈了一个月的恋爱。我们分手之前在儒
林酒家吃了一顿饭,在座的有我与李尤,
还有李德成与他的女朋友张小雅,张小雅
是商院的,念大二。李德成把他的那把吉
它送给了我,他说留给我做个纪念,而且
他认为把它带回黄村也不方便,行李已经
够多的了。李德成和张小雅与我们后来在
汉口路分了手,我记得他当时跟我与李尤
挥手时说了一句:“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
去黄村找我。”我到现在仍记得李德成向
我们挥手告别的姿势和表情。
遗憾的是,虽然黄村这个地名对我来
说耳熟目详,李德成在校时不知跟我说过
它多少次,但是至今我也搞不清黄村到底
在一个什么地方。我想,我总有一天会弄
清楚的。
二
这是一九八七年夏天的事情。时间
又过了八年。八年的时间足够使人忘掉很
多从前的事情。大学毕业后我感觉自己再
也没有轻松过,为了努力地活下去并且尽
量活得快活一些,我先是被一些单位选择,
然后自己又不停地选择其它单位,我一直
想找一个能够使我游刃有余地大干一番的
地方。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我南来北往地
去过许多城市,在那些城市我留下过一些
痕迹,但我总是未能如愿以偿。至今我仍
在马不停蹄地寻找着,我顽固得还没有丧
失掉希望。
在大学毕业后最初两年的时光里,我
多少还有一些闲情逸致去拨弄拨弄自己的
吉它,李德成的那把吉它我也一直放在身
边,当时在单位,像我这样拥有两把吉它
的年轻大学生绝对是一个有头有面的人物,
我在单位同龄人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很高,
那帮朋友居然很少有懂音乐的;由于他们
对音乐的无知,我顺理成章地令他们感到
敬佩,当时的团委还打过我的主意,单位
的头儿认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可能更利于
做好年轻人的工作,他找我谈话想让我去
干团委书记。当时,我对那个单位有些失
望,一直在暗暗地等待机会逃走,所以我
回绝了那个头儿的好意。两年之后,我再
也没有机会去弹奏我的吉它,我终于跳了
糟。由于经常搬家,那两把吉它就慢慢地
被弄丢了,我至今也搞不清楚它们是在什
么时候被我遗弃的。
这八年的时间除了更换工作,就是与
李尤折腾爱情,李尤大学毕业后并没有与
我分在同一个城市,有一段时间,为了我
们的爱情,我与她来来去去花了不少冤枉
钱。我们离了又合,合了又分,到最后彼此
累得直想放弃这令人劳筋伤骨的爱情。也
不知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反正后来李尤也
来到了南京,我们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我们现在已经同居两年多了,像一对
小夫妻那样在南京生活,只是至今还没有
领结婚证。在下雨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
么总是在下雨的时候),我和李尤都不想
出门,两个人只好呆呆地在房间对坐着,
总是忍不住在雨声中感叹时光有如白驹过
隙。我们俩似乎已渐渐地远离了从前的生
活。我隐隐地感到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事
实,时光催人老啊,我已经看到了李尤眼
角上的鱼尾纹,八年前,她是多么年轻,青
春,美丽;想起她以后还会老下去的模样,
我总是在心里感到无奈和伤感。
吉它…大学时光…李德成……。我几乎再
也难以想象它们曾经属于过我,曾经与我
有过关系。八年的时间,我几乎已经忘记
了李德成,还有那个与他有所关联的叫黄
村的地方。如果不是由于一次偶然,他和
那个叫黄村的地方大概再也不会从我的记
忆深处浮现出来了。
三
有时候,我不能不感叹生活的确是
如此荒诞,充满了偶然与必然的扯不清的
关联,我万万没有料到,我在八年以后的
一天,居然稀里糊涂地路过一次黄村,并
且在那个叫黄村的地方寻找我在大学时的
好友李德成。
好了,我不想再拐什么弯了,还是让我
们去黄村看看吧。我要让你们知道,那些
在黄村发生的与我或者与李德成有关的事
情,为什么是那么令我莫名其妙,那些令
我焦头烂额的事情到现在仍让我心有余悸
。
因为我没有想要去黄村,所以我觉得
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我是如何偶然路过黄村
的:
那也许是一个与昨天和未来没有什么
两样的一天。那天傍晚下班后,我没有像
以前那样买好菜后等李尤回来做饭。我回
家后把公文包放在桌上,点燃了一支烟,
我坐了下来,突然感到自己再也不想动了。
我陷入到沉思之中,把头和身子埋在沙发
里一口一口闷闷地抽烟。我模模糊糊感到
自己忽然对此刻面对的生活有一种厌倦之
情,房间里的气息熟悉得让我憋闷,我在
心里不禁对自己与李尤这几年来的生活感
到怀疑--这难道就是我们当初追求的生
活吗?我越想越提不起精神,我感到我与
李尤之间的生活已经出现了一道罅隙,但
毛病到底显现在哪里?我尚不能明细地察
觉。我也相信不久的将来这种状态会慢慢
地有所改善或者渐趋更好(但只有鬼知道
什么时候!);问题是现实是一回事,未来
又是一回事,麻烦的事情在此时很容易在
我身上出现--我这个人向来对一切没有
足够的耐性。所以,在那一刻,当一种绝望
的情绪笼罩我的时候,我一刹那间感到自
己有点心灰意冷,我没有让自己去菜场,
虽然我的肚子已经饿了,我感到自己根本
不想动弹。我在那里吞云吐雾,破天荒的。
当我听到李尤把她的钥匙插向锁孔的时候,
我发现黄昏已经过去,夜晚早已降临,我
手中烟头的微光把房间里的黑暗照得更黑。
李尤把门推进来的时候,大概从走廊上透
出的微光中看出了一个笨拙的身影,她吓
得一声惊叫,慌忙中拉开电灯(她把开关
线拽断了),她从来没有看到我在这样的
时刻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她没有料到我
会这样。她哭了。她看上去显得很累,单位
离家很远,每天早出晚归地赶路是很辛苦
的。
我一向受不了女人的哭声,我只要一
听到她们的哭声,心里就会紧张得发慌。
我开始心烦意乱,我感到房间里突然生长
着一种与我对抗的东西,我根本无法招架。
李尤还在轻轻地抽泣着,仿佛受到无穷的
委屈,她把自己摆在房间的正中央,她的
包还挂在肩上,身体在抽泣中微微地摇晃
着。我再也不能与她这样对峙下去了,我
难受极了。我突然在房间里吼了声:“我再
也不希望这样生活了,我已经烦透了!”我
的声音使李尤吓了一跳,皮包从她的肩上
捷速地滑了下来。她大概没有料到我会这
样。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我感到自己快
要疯了。我开始在房间里砸东西,那些平
时靠我们省吃俭用买下来的东西一件一件
地被我抛向了地面,顿时,房间里充满了
各种怪音,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刺耳。李
尤被我的行为惊呆了,她开始放声号啕大
哭,她很快地过来抱住我的胳膊,拚命想
挡住我的双手,她没有说一句话,她只是
想使我停止动作。我砸了一阵,慢慢地没
有了力气,就停了下来。这时候,我突然听
不到李尤的哭声了,我抬起头看她,但见
她眼角上的泪水还在不停地往下淌。不知
为什么,我感到自己的鼻子也微微地有些
酸涩,我在那一瞬间感到有些伤心。我把
视线伸向了窗外,外面已是万家灯火,一
些人家已经关门睡觉了,而我和李尤尚无
一滴水一粒米下肚。然而,我们都不想吃
任何东西。
也不知过了多久,李尤已经在收拾这
个被我破坏得乱七八糟的房间,那些玻璃
的碎片和被我搞坏的一些物件,在李尤的
清理中,发出了一些令人不舒服的声响,
我不禁皱紧了眉头。我们一起精疲力竭地
坐在房间里,呆呆地望着房间那些少了东
西的地方或者互望着对方。我看见李尤右
手的大拇指头还在流血,那可能是刚才划
破的,可她还浑然不觉。我不禁心头一阵
紧缩,一丝淡淡的感伤再次油然而生。
我说:“李尤,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这
样的。”
李尤听了我的话,竟然忍不住又流下
泪来,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她说:“你以为
我不感到累吗?只是我说不出口。我不知
道我们怎么了。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没有
像当初希望的那样?”
我无言以对。过了一会才说出一句:“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李尤有些警觉地问我:“那么,我们怎
样才能下去呢?”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已经是深夜了。我们仍没有吃什么东
西,我们不感到饥饿,饥饿感仿佛早已被
我们糟糕的心情抽空了。我和李尤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尴尬地坐在自己的房子
里,莫名的无聊和空洞。
“你真的想这么做吗?”李尤又开始流
泪了。
“我没有办法。”我说。
“我们走到今天很不容易。难道你不想
珍惜吗?我们还可以好好调整的。”李尤
恳切地望着我。我不能看李尤的眼睛,看
了我的心就软了下来。我怎么跟她说呢。
我低下头,一声不吭地想把自己凌乱的思
绪好好理清。李尤从厨房里拿了一点吃的
东西,我这才觉得肚子空空的。
“李尤,我们出去一趟吧。”
“到哪里?”
“外面。”
“什么时候?”
“现在!”
……
四
就这样在那天吵架的当天夜里,大
概快凌晨三点了吧,我和李尤匆匆地收拾
了行装,然后赶往火车站。当时,我们都有
一种尽快逃离南京的冲动。我们随便地爬
上了一列火车,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也不知道自己搭乘的这列火车驶往何处。
车厢里的灯光有些暗淡,人们已经安然入
睡,谁还会在意这两个狼狈不堪的年轻人
呢,上半夜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全世
界大概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了。幸好是夏
天,卧铺车厢还有座,乘务员给我们办完
手续后,我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列
车哐当哐当地运行着,车窗外一片漆黑,
一屁股坐下来,我才感到自己已经很累,
李尤也是哈欠连天。我们躺下来,很快进
入了梦乡。
这一觉睡得真是太沉了,等我醒来的
时候已是第二天黄昏,我睁开眼睛,好像
还没有睡够,李尤仍在梦里。窗外的风景
太令我陌生了,到现在我仍然不知这列火
车要把我们带向何处,我迷迷糊糊地倚在
那里,我想我们总得要选择一个地方下车,
等李尤醒来后再商量吧。我决定再躺一会
儿,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在蒙胧中忽
然听到列车播音员的声音响在耳边:“旅
客们请注意了,前方到站--黄村,请需要
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我吃了一惊,
从上铺上跳了下来,摇了摇头,以为我听
错了,但播音员很快又把刚才的声音重复
了一遍。黄村?黄村!我的记忆顿时好像翻
滚起来,这难道是李德成说的那个黄村?
这么说,我们可以下车去看看他了?我有
些犹疑,但还是赶紧把李尤弄醒,我对她
说,快起来吧,快到黄村了,我们下车去看
看李德成吧。黄村?李尤听了我的话,非常
惊讶,她大概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黄
村?什么黄村?”她纳闷地问我。我说怎么
黄村你都不知道啦,它是李德成的家乡啊,
我们正好可以去看看他了。李尤一下子回
过神来,她甚至露出一点兴奋的表情来,
不过,她很快地又问了我一句:“你能肯定
这个黄村就是李德成说的那个黄村吗?”
我一下子愣住了,是啊,我怎么能够肯定
呢?我想了想,对李尤说,不管怎么样,我
们还是先下车吧,反正我们总要下车的。
李尤同意了。
黄村很快就到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