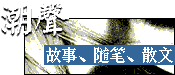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粟四维·
三伯父的照片
伯父就算不是父母吧,也是近亲了。小 时候常听同学提起他们的伯父,他的家如 何如何,他给了他们多少礼物等等、等等。 然而伯父这个词对我 而言却是个抽象概念。和许多所谓的外省
人一样,父亲只身随部队来台湾,海峡成
了天堑以后,就再也飞不回老家了。连父
亲都不知道伯父的下场,在台湾出生成长
的我就更不会关心了。
而言却是个抽象概念。和许多所谓的外省
人一样,父亲只身随部队来台湾,海峡成
了天堑以后,就再也飞不回老家了。连父
亲都不知道伯父的下场,在台湾出生成长
的我就更不会关心了。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就从没有安于 现状过。他从不买菜,但每回我想吃些什 么,他总会主动带我到市场去。说真的,我 实在不想和他在公共场合一起出现。他一 到市场,一定先看看梨子苹果之类。看到 小贩说那是富士苹果,他马上吼了回去:“ 这是什么富士苹果,假的!根本是台湾自 己出的烂苹果。”再隔几天,看到了市场上 的梨,小贩好心切了一片让他尝,他手一 挥,又用他那四川腔说,“什么四季梨三 分利的,比大陆莱阳梨差远了!”他喜欢抽 烟,在大陆货还是禁忌的时代,不知从那 里弄到一个大陆制造的烟盒,手一压把手, 烟就出来了。他还满自欢喜的告诉我,“大 陆做的,不一样吧?”然而我发誓根本没去 碰那东西,那烟盒就再也压不出烟来了。 父亲也就做个顺水人情,把它送给我当玩 具了。有一天他从巷子口走回家,看见我 在楼梯口,坐在流动摊子上吃起蚵仔面线。 我本想告诉他这面线有多么好吃,让他也 有机会分享,但他没等我开口,替我付了 钱,把我拉了回家,用他浓眉下如同黑暗 中从门缝透出光束般的眼睛盯着我说,“ 以后不准在街上买台湾人做的东西。”我 一直都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同样是摊子上 的东西,臭豆腐他却是趋之若骛。即使是 三十五、六度的大热天里,他只要一听到 楼下卖臭豆腐那老头的吆喝声,即便是在 马桶上蹲了半个多小时看报纸,他也会冲 出来,使劲地把那不怎么灵光的玻璃门拉 开,向楼下大吼一声,“臭豆腐,”然后就 随便抽几张新台币往楼下跑。数分钟后, 就看着他拎着一袋臭豆腐,边走边说,“儿 子,来吃。”他吃东西本来就不在乎什么仪 态、仪表的,吃起臭豆腐来就更没这回事 了,只见他张开大嘴,与其说吃,不如说是 猛烈地吸吮着带着辣椒汁和酸白菜的豆腐, 接着就撕牙咧嘴地,像是拼命咬碎,又像 是舍不得往肚里吞地似地,咀嚼着又烫又 辣的美味佳肴。
谈到台湾的媒体宣传,他更是嗤之以 鼻:电视上的政治评论,他说是愚民政策; 综艺歌唱节目,他说是靡靡之音;广告则 代表了社会腐化现象,新闻则是国民党的 传声筒。总之,台湾在他的眼里,根本是罪 恶之国,沉沦之岛。更要命的是他口没遮 拦的态度,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警 备总部在五、六十年代是人人谈虎色变的, 而我父亲三进三出,最后一回被人诬陷为 匪谍,幸亏承办军官是母亲的老乡,为人 宽厚,而他的四川土话也显示出他的身份 是老粗而不是奸细,才逃脱了被枪毙的命 运。这些是都发生在我有记忆之前的事, 但后来听父亲和其他家人谈起,总还是让 我觉得自己的一生真是侥幸地被一位好心 人赎救了。不过,最令我难过的是有一回, 姐姐不知道为什么偷偷地告诉我,
“爸爸是匪谍。”
我当然害怕这顶帽子扣到父亲的头 上,但更令我伤痛的是,为何父亲成了一 个坏人?父亲纵然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我, 但我相信他绝对是善良的。几天后,姐姐 才又改口说,
“父亲只是想家吧。”
我松了口气。
※ ※ ※
然而,一直要等到二十多年以后,我也 在美国住了八年,我才能真正体会到父亲 过去种种鲁莽、不合常理的行为,只能用“ 想家”二字解释吧。就在我入伍服役前没 多久,父亲从海外打了通电话回来,他不 知从那来得到的消息,说台湾快完蛋了。 这话我从来没当真过,因为只要一有机会 他都会这么说。但这次不一样的是,他要 母亲把房子卖掉,然后马上移民美国。如 果母亲不做,就是害了全家,把他用一辈 子的积蓄买下的房子,随台湾的完蛋而付 之流水。在他的逻辑之下,为避免母亲毁 掉他的一生于一旦,他的方法就是撂下一 句话,“你如果不卖房子我就不寄钱回家。”“ 家”,这个字在父亲心中是模棱两可的。家 的感觉可以强烈得让父亲即使在六十年后 的梦里,仍上演着他和年岁相仿的侄子, 爬到树上采桃子的故事;但却也模糊得让 他不以为养家是个死而后已的责任。然而, 我当时没能体会到的是,父亲定义的家和 我想要的家其实并不一样。他不知道的是, 他心中的家已经在四十年代的动乱下,随 着他到台湾而如残雪般地消融了;而我要 的家则因他那不可及的家如梦魇般地斫伤 得永远残缺一角……
※ ※ ※
那已经是半世纪以前的事了。还和侄 子爬树啃桃子的父亲并没有体会到祖父的 去世代表着什么意义。
“祖父是个乡绅,专门替人排难解纷的。”
这话父亲也向我说了不下十几回,每 回的表情总是那么自豪。然而除了这话以 外,就再也没听父亲说过有关祖父的事了。 大概在祖父出殡以后,父亲仍然没有停止 在桃树林里的游戏,更别说接下来国民政 府从天的那一头搬到隔江那栋白色的洋楼 房里,除了稀奇以外又是怎么回事。后来 家乡来了许多连话都不会听的外地人,有 些还穿着从没见过的军装。不过这些久而 久之也就没啥稀奇,反正不关己事,还不 如从小熟悉的几个游戏,愈玩愈有味道。 也许父亲的一生也就是场游戏吧,只不过 不同阶段玩的不一样。游戏对在玩的人而 言是种生命,一如尔后父亲每回和老板打 麻将,总是战战兢兢地,嬴也不是,输更要 命。但对旁观者而言,游戏永远只是浪费 时间罢了。记得有天早上母亲突然问我,
“昨天晚上你爸爸还在和老板打牌的 时候,你是不是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我没说话,也来不及想是不是该为自 己不礼貌的行为惭悔。如果是,那么父亲 只顾玩,不顾家人又算什么,我心里想。
“你爸爸陪着老板打麻将,听到你的关 门声,一边打着,一边出冷汗。”母亲接着 说。
也许三伯父能在身旁劝他就好了,一 个半世纪以前,他看着父亲尽在一些无意 义的事上消磨,他总有办法以他的资历和 学识指引父亲一点人生的出路。做为儿子 的我只有承担游戏的代价。
“你三伯父是中央大学毕业的。”那时 的中央大学还在南京,没迁到重庆。算算 时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而今已九十多 岁了,年岁上可以做我的祖父。
“你祖父和大伯父早死,家里没得吃的, 你三伯父就教我去考海军官校。我当时连 初中都还没毕业,连报考资格都没有,三 伯父就从村子请了一个叫‘李杰’的人,高 中毕业,帮我……”
“报名?”我岔着问。
“哪里?”父亲又用那四川口音睥睨地 说,“不但报名,而且考试。所以你爸爸的 这个名字其实是那个人的;我是假的‘李 杰’。”父亲眉飞色舞地大谈他当初作弊找 枪手的经历。
“那年海军官校每省只录取两名,而我, 就是其中一名。”父亲对考试的结果很是 骄傲。作弊的结果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但 如果结果改变了一生的命运,或即使仅仅 是一时的优越感,那总还是会因此自豪的。 待在学校一辈子的我在这点上总算能体会 父亲的心思。
“我进入官校没多久,学校就迁到了台 湾。”父亲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 妈个X。蒋介石连一封信都不准我们寄回 去。”
“我在官校四年就只学会喊领袖万岁。 还有就是一把手枪,告诉我们随时准备为 领袖去死。
“你妈有没有告诉你我被警备总部抓 去的事?”
“没有。”
“嘿…嘿…这你就不知道了。”父亲得意 地准备开始讲述他的英勇事迹。“那年你 姐姐刚生下来没多久,我还是个小少尉, 薪水连菜钱都不够,还得付电费。不过我 想到了个办法,我连了根线,就把电偷来 了。”
“你没被查到吗?”
“当然被人检举了,”父亲睁着眼说,“ 连海军总部都来查,说我破坏公共安全。
“呵呵…”父亲捂着他的笑嘴,“你妈妈 当时吓得脸都白了,抱着你姐姐都说不出 话来。”
“那你当时怎么办?”我问。
“我把来的人骂了一顿,说他们是国民 党的走狗。本来想打他们,后来被你吴叔 叔阻止。吴叔叔塞了点钱给他们,他们才 走了。
“没多久,我被派到船上,就在哨站门 口,两个年轻军人向我走上来,问我是不 是李杰,我说我是,他们就说我们的长官 请你过去一下。我什么也没想到,就拎着 包包跟他们进了一个屋里,屋里坐着一个 少将,陆军的,他又重复问我是不是李杰, 我也照实回答。他从头到尾看了我一遍, 皱皱眉头,到桌上拿了一叠资料给我,我 看到上面印了‘机密’两个字,写着:
查李员生性玩劣狡猾,屡次散布污蔑 领袖之言论。今与匪勾结,欲将挟持XX舰 驶往匪区,令速将逮捕,交付审判,以儆效 尤。
“那怎么办?”我紧张地问道。
“那张少将又看了看我一眼,”父亲气 定神闲地继续他的故事,“对我说,‘我看 你这个人老实得很,怎么会做这种事?’我 就跟他说,‘什么挟持不鞋子的,我根本不 知道这件事啊!’张少将接着告诉我,‘现 在有人要陷害你,你呢,就当做什么都不 知道,走出门口后,什么都不要提。’要是 当时没有张少将一句话,我早就被枪毙了。”
父亲说完眯着眼睛,摇着那根翘着的 右腿,嘴巴似笑不笑地闭着,像是在想什 么,可是又更像是什么都不想。我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过了半晌,他接着说,“要不 是你三伯父,我早就在四川和我侄子、和 你么爸在一起,也不会在这个鬼岛上被人 耍了。”父亲的眼眶红了,可是我没敢上前 问他怎么回事,因为上回我问他的时候, 他只说了声,“小浑蛋,滚开。”
第二天早上,我在垃圾箱找一本不该 丢掉的笔记本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一张撕 碎了的老照片。我好奇地把它拼了起来, 原来是张学士照,黑白的,照片的色泽非 常熟悉,就如同母亲高中时留着赫本头的 那张一样。不,应该说更黄一些。我翻过背 面,有着苍遒的钢笔字迹,以简体字写着:
“四叔留念,侄道荣敬上。”
※ ※ ※
父亲在台湾的几十年一直尝试着和在 大陆的亲人联络。头先的二、三十年自然 是徒劳无功,一直等到邓小平开放之后, 他才辗转从在美国的舅舅那儿和大陆联系 上了。先是他弟弟,我们管他叫么爸。听说 他向父亲要了很多钱,起初因为海外关系 被关在牛棚,吃了不少苦,后来又因为海 外关系当上了当地的人民政协副主席。接 着,父亲和他年岁差不多的侄子联络上了, 从他侄子那儿,才知道我三伯父在文革期 间因为胃疾而死了。三伯父生前的最后一 个决定就是把女儿嫁给了一个随军入川的 共产党员,也因此,父亲的侄女才免于文 革的迫害。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再配 合三伯父鼓励和帮助父亲就读海军官校的 故事,我不得不佩服三伯父的眼光。
在我看来,父亲的生命除了麻将之外, 就是等着不知道多久才可以等到的家书, 他就是等着家里的人来信告诉他,回家的 时候到了。记得那是八十年代末,父亲临 时在台湾住了三十多年之后,不知道从那 儿听说台湾快完,就坚持要把我住了一辈 子的公寓房卖掉。我当时已经是个大学生 了,“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但 是我对这个家却连个发言权也谈不上。父 亲常常鼓励我多找些同学到家里玩玩,但 等到他觉得时候到了,他该回老家、该把 我们的家卖掉的时候,这些就都不提了。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这个家也满足了我不 少虚荣心。有段时间父母和姐姐都不在家,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住着,有个同学到家里 来,还开玩笑地警告我,别住这么大的房 子,当心被鬼抓走。我当然没被他的话吓 到,反而因此高兴了好几天。这倒也是,要 不是别人的评论和后来租房子的经验,我 还真不知道在台北市能住上四十多坪的公 寓,还称得上是幸运的事。不过这些后来 都成了过往云烟了。我们把房子卖了,就 随便在对面的国民住宅里租了间房,差不 多只有原来的一半大,因此该卖的就都卖 了,不能卖的也都给人了。反正父亲的意 思是再过四年就移民美国,这四年就将就 点住着。父亲年岁比我大上三、四十,但似 乎比我还不明白,人生能有多少个四年。 新屋的房东不准有宠物,所以我只有把Happy 送走。这个家只有我可以把Happy驯得服 服帖贴地。小时候有一次母亲要替我盖被, 它马上惊醒,对着母亲张牙舞爪。对此,母 亲是厌恶、嫉妒、赞美、又觉得好笑。不过 这回Happy却连我也不听了,就在他的新 主人来接它的时候,他突然从我的怀里跳 走,奋不顾身地往街口冲。我没法,第一次 不是快乐淘气地追着它跑,在躲过几辆车 之后,总算把它制服、送上计程车了。Happy 手伏在关紧了的车窗,焦虑失望地盯着我。 上天没有赋予动物流泪的能力,我那时才 知道,这是他对人类的恩赐。而父亲只在 巷子口看着我尴尬地、身不由己地把Happy 捉上了计程车,事后才说,
“我老早就告诉你把它扔掉,你看你在 街上捉它多危险!”
送完了Happy,接着就要把家腾空。 我再也没什么力气负责这项任务,父亲又 刚好不在,所以一切大大小小的事都得由 母亲处理。平常羸弱的母亲这时却显得坚 强了。也许对他而言,搬个家根本是件小 事吧。整个过程他不多说话,只有在接近 尾声的时候像是发表一份大胆的评论,“ 总比在大陆逃难的时候强多了吧。”等到 把家搬完了,母亲松了口气,彷佛也是完 成了一桩大事,但我却彷佛意识到另外一 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油然开始。趁着新屋主 还没搬进来的前一天晚上,我偷偷地潜入 了这个又属于我的家、又不像我的家的地 方。大概是住在同一间公寓里一辈子,对 空间的感觉已经麻木了,我顿然体验到这 间公寓是不着边际地大,大到我不知道应 该在什么角落立足。墙上的壁灯本来就不 亮,此刻照着空荡荡的屋子就更显得晦暗 无力了。印象中,屋子里总是有些东西的, 所以此刻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空的力量,轻 飘飘地,但却难以承受,我实在受不了地 自己一个人嚎啕大哭了起来,尖叫着,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没有 家?”
“现在饭厅的空间太小了,到时候把饭 厅和厨房打通,整个空间就显得大多了。” 我突然听到一番讨论声接在一阵跳跃轻快 的脚步声之后,我知道是他们来了,赶紧 吞咽了最后一把泪水,腼腆地从他们的身 边擦过。虽然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有机会进入这个本来属于我的空间,但还 是惭愧地不敢往里头多望一眼,就匆匆地 把门带上了。我知道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男子是不应该这么样失态,所以从那次起, 我就再也哭不出来了。
房子卖了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怪异的 力量让我没事就注意“吉屋出售”的招牌, 虽然我不是买主,也怕别人知道我现在是 没有家的人。做了这种无意义的事大约两 个月左右的时间,台北的房价涨了十倍, 我才死了这条心。
搬完了家,开始了新的生活,台湾的社 会也开始了新的气象。一直认定自己是知 识分子、还在念大学的我,不时地阅读报 纸,一会儿蒋经国说,“不接触、不谈判、 不妥协,”后来又换着说,“时代在变,环 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一会儿又传说蒋经 国病危,最后,终于开放到大陆探亲了。我 思索着这一连串政治局势的变化,又习惯 性地预估开放探亲对台湾可能造成的影响, 也同时想着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做些什 么。正在我看着报纸想着问题的时候,突 然一阵惊怖的敲门声,
“快点!快点!”父亲焦急地喊叫着,像 是忙着要去做什么事,可是又像是找不到 件实实在在的事做。
“怎么了?”我也紧张地问。
“国民党准我们回大陆了!”
“那好啊,你就可以去大陆瞧瞧了。”
父亲看了我一眼,似乎没听清楚我说 些什么,继续说,“我要去你妈的抽屉把存 摺找出来。我干了一辈子,总不会连二十 万都没有吧。”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只要父亲手 上有钱,他总会尽快地把它花掉,即使打 麻将输掉都行。
“干什么?!我要带回大陆!”
“你去大陆观光需要二十万台币吗?” 我有点奈不住性了。
“你浑蛋!”父亲让我吃了一惊,“这些 钱是我赚的,我为什么不能花?”
“你能不能用点大脑做这件事?你难道 不知道我们家缺钱吗?”我顶了回去。其实 我早就想要这么做了,因为我慢慢发现父 亲和我的关系,亲情越来越淡,剩下来的 就是“力”了。过去年纪小,力气也小,也 不想当个不孝子,所以只有在他面前唯唯 诺诺,但现在家也没了,什么也没了,要打 架也绝对不输他,所以胆子就大了起来。
“你想要阻止我,我就杀了你。”父亲 的话,和讲话时凶狠的表情在别人看来一 定会吓坏了。
“你敢!”母亲突然冲出来岔到我们中 间。父亲用他那曾经是军人的手臂往母亲 的肩膀一扯,母亲没防着这一层,摔倒在 地,卡在饭桌下零乱的桌脚之间了。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有母亲替你撑 腰,你就不必怕我了!”父亲瞠着眼,嘴角 颤抖地说。
“我跟你拼了!”母亲从桌角间挣扎了 出来,用手肘撑了下身体,就在地上往父 亲的脚扑去。父亲就像座山一般,一动也 不动,很快地把母亲甩开以后,就顺手拿 起摆在桌上的不锈钢茶壶,往我的头上砸 下。我什么念头也没有,像是干一件司空 见惯的事一般地用手臂挡住他,接着就把 他抱紧,让他一动也不能动。等到父亲冷 静了些,我才松开手说,
“你要回大陆你就回去,我也不稀罕你 跟我在一起,更不稀罕你的钱!”
父亲在地上还爬不起来,看着天花板, 眼眶逐渐地红了,
“你知道人生最惨的是什么吗?”父亲 问我,我撇过头看着窗外的天空,他接着 说,“妻离子散。”
※ ※ ※
“各位旅客,欢迎您乘坐中国西南航空 第么么七四号航班,从香港直飞重庆,机 上有五名乘务员为您服务。。。”我没想到 回大陆是这么容易的事。陈怀生为此牺牲 了生命,有人为此牺牲了青春。入境柜台 上几个穿着绿色制服,像是军人又不是军 人的官员看着我的蓝色护照,明显地和他 们习惯见到的港澳台胞证长得不太一样。 他们用我十分熟悉但永远也没听懂的四川 话、交头接耳地不知在商量些什么。大概 即使改革开放已经行之有年,但这些曾经 为社会主义祖国把关、严防某些人回大陆 的卫士们,似乎搞不懂我为什么要从太平 洋的另一端,飞到中国大陆的西南内地。
“美国人。”这是我唯一听得懂的三个 字,是其中的头教导属下,我藏在肤色底 下真实的身份。不久,承办的官员没有表 情地望着我,恨不得多看我一眼,四、五秒 钟的时间,让我局促不安。“砰!”那官员 在护照上盖了入境许可,我到了中国。
我不太敢往接机的地方看,只顾着转 动行李的轮轴整齐划一地轮唱着,迎接一 袋又一袋、永无止境、从他乡递来的包裹。 等到行李领到了,我往入境的大门走去, 心情开始紧张了。我边走边找父亲的踪迹, 但等候的人群里没有一个我熟悉的面孔。 等到我接近了人群,才看到一个牌子,大 大地写着我的名字,我赶紧趋向前去。
“您好,我是李治平,您是…?”举牌的 是个瘦削的中年男子。
“治平,我是你大堂兄啊。”他激动地 握着我的手,一一将来接机的人介绍了一 遍。
“四叔近来身体不好,要不是医生特别 警告他不能离开家乱跑,他一定会亲自来 接你。他还告诉我们你的身高、体重…嗯, 相信你一定比以前瘦了些。”堂兄稍稍地 看了我一眼,继续说下去,“他还特别交代 我们你的头发梳成什么样子,在左边分叉, 然后喷上厚厚的发胶,让人感觉头发油扑 扑地、给人很有精神的样子。我们都笑他, 那有人八年头发都不变的,呵呵。”
“父亲在这儿一切都还好吗?”我不由 自主地问道。
堂兄向我解释了一下父亲回大陆以后 的状况,“四叔基本上都还好,只是猛吃 辣椒,劝都劝不听,他说台湾的辣椒不够 辣,吃得不过瘾。
“你不晓得,有一回可能是辣椒吃多了, 他突然喊着胸口疼,我们赶紧带他进医院, 还不到医院的时候就晕了过去,把我们给 急死了。我们告诉医生,你爸爸是台胞,在 这儿没有家,医生才紧急处理。还好,过 了大概四十多分钟醒了过来,你堂姐看到 他醒了,高兴得都哭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他醒来第一句话是什么?” 堂哥问,我摇了摇头,他接着说,“他就问 我们,‘我刚才是不是死了?’我们就笑他, 要是死了,现在还会说话吗?
“不过你父亲很坚持,他说他一定是死 过了。他说他迷迷糊糊地看到了你和你姐 姐,好像就在面前,他想去握住你们的手, 可是怎么都摸不着。没多久,他还来不及 和你们说话,你们就不见了,也不知道你 们在哪里。”
我们一路上聊着,四十多分钟的路,彷 佛十分钟就走完了。到家了,父亲已经和 其他亲戚站在门口迎接。他看到是我们到 了,主动走上前来。那会儿重庆的天气阴 沉沉地,但是父亲还是戴着一副褐色的太 阳眼镜。大大的眼镜遮住父亲的脸,让我 几乎想不起来父亲八年前的模样。从前父 亲的牌友都称赞他的头发,即使上了岁数, 还是那么乌黑。但现在的头发却在鬓角显 出丝丝的白花了。不过头发整整齐齐,一 看就知道是刚剪过的样子。所以虽然泛白, 他的头发仍然是父亲脸上唯一让我可以找 到他昔日风采的剩馀物。父亲的右手握着 根拐杖,不自由主地颤抖着。一位大约四 十多岁的女子站在他的左边,扶着手,不 时地注意父亲的步伐。也许因为父亲知道 有人扶着他吧,纵然他的步伐显得颠扑, 他一点也不低头,直通通地朝着我走来。 他看到我只是微微地笑,从头到尾把我打 量了一遍。而我透过镜片看着父亲的眼睛, 一种在我生命记忆中从没有经验过的慈祥 感动了我。我流下了八年来从来不肯轻易 释放的眼泪,生疏地喊了一声,“爸爸!”
晚餐桌上摆着生鱼片、铁板鳕鱼、酥炸 生豪、、、一些我以为在四川内地不可能 吃到的佳肴全在桌上了。
“三个月以前你爸爸听说你要来就吩 咐我把菜准备好,还亲自开菜单,全是你 在台湾爱吃的菜。我就说嘛,鱼要当天买 的才新鲜,他就天天唠叨。”其中一位亲戚 撅着嘴,而父亲则在一旁像小孩子般地轻 轻地笑着。
“还有五粮液,三个月以前就买好了。 你父亲还和我们辩,说菜不能先买,酒总 可以先准备好吧。”另一位亲戚好心地关 怀着,“你们在美国吃不吃得到五粮液?我 们想喝一口,但谁敢把酒瓶打开?”大夥儿 听到这儿都笑了。
“明天还有节目,”父亲开口了,“我们 一块儿到朝天门!”
“朝天门”,这个彷佛听过、但却一点 也不熟悉的地方,不知有什么特殊。我们 的车子沿着江边在山路蜿延,顿然间,江 面豁然开朗,“呜…呜…”惟恐不惊动天地 的汽笛声让我明白,朝天门是个热热闹闹 的码头。
“抗战胜利之后,你三伯父就送我到这 里,唷,就是你现在站的位置,”父亲心平 气和地说着。我感觉到站稳了脚跟,仔仔 细细地向远方望去,嘉陵江从左手边向着 长江、也是夕阳的方向,没有声音、深长细 匀地流着。眼前就是长江,顺着下去,不就 是到了东海,然后就可以接上台湾、美国 了吗?
父亲语调一转,接着说,“哎呀,你不 知道,人山人海!”父亲的四川腔调把这四 个字说得铿锵有力,似乎要奋力把声音盖 过万头钻动的人群。
“为什么?”我好奇地问。
“大家都赶着要回家呀!”父亲大概没 有意识到他那“回家”二字说得清楚地让 我觉得陌生,所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 继续说,“那时抗战刚刚胜利,码头每天都 挤满了人,有些人还边挤边喊着,‘不让老 子回去,我就跟你拼了’。我那时候要跟着 官校师生到南京开学,你三伯父催着我, 我也紧张得很,既怕脱离了部队,又怕拎 在身上的那口大皮箱被人扒走。其实那口 皮箱除了几件简短的内衣裤之外,就只有 前一天夜里我的侄儿送给我的笔记本。我 那时连张船票都没有,三伯父就同大副说 了些话,让我上了船,但是只能在甲板,不 能让船上的军官发现,所以整个行程我都 是躲躲藏藏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安身。” 父亲又开始发挥他说故事的本领,“你三 伯父和船上的人谈好了以后,我们就站在 你现在站的位置,三伯父握着我的手,告 诉我一有什么事一定要写信回来。唉,我 第一封寄回家的信,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 事了。”
“当时我的侄儿也在码头上,他站在你 三伯父的身后,像是在躲我的样子,一会 儿问你三伯父是不是该买些清凉油让我带 着,一会儿又吆喝小贩买些解渴的,一会 儿又着急地望着停在江边的船。”
父亲稍微停顿了一下,“那时要是跟不 上往南京开的船,情况就不一样了
……”
父亲痴痴地望着江的另外一边,不动、 也不作声。堂兄搀着我的手,对我说,“治 平,你不晓得四叔知道你来有多高兴。昨 天你醉倒以后,他和我们还继续吃饭聊天。 他平常吃完饭都侃个没完没了,但昨天却 不多说话,只有在嘴角保持着微笑,我们 趁机开他的玩笑,他就像个刚讨媳妇的新 郎官一样害羞,想还嘴,但却又不知道要 怎么说。”
“这是要盖啥子?”父亲指着在码头右 方、一片大约有社区垒球场那么大、施工 中的大楼问堂兄。
“听说是个大型购物中心。”
“这些在我离开的时候都没有的。”父 亲评论着。
堂兄看到父亲又停止了说话,就转过 头来,“当初要没有你三伯父逼着你父亲 读海军官校,他就没办法到台湾、也就没 有你了。”堂兄无意识地重复父亲过去经 常讲的话。
“你三伯父也是从这儿坐船到南京念 中央大学的。那时候的大学生不得了。” 堂兄虽然看来谦虚沉稳,但说这话的当口 还是掩盖不住骄傲的神色。
“你三伯父回到重庆,在当地还是个新 闻。他人长得高高瘦瘦的,非常英俊,好多 女孩子追他呢。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 卫兵造他的反,他受不了一连串的打击, 得胃病去世了。
“我们弟兄三个人,因为成份的关系, 都没机会好好念书,所以看到你拿到博士、 在美国当大学教授,实在觉得非常安慰。” 堂兄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我也常常告 诉我女儿,要好好念书,学习他的祖父还 有小叔你,为我们李家争光。”
“呜…呜……”一阵汽笛声吸引了堂兄的 注意力。他往停在江心的客船望去,也和 父亲一样沉默了。过了半晌,他像是发现 了什么似地从提包里拿出了一张照片,我 习惯性地把照片翻到了背面,上头有着十 分熟悉的字迹,写着,
“治平留念:三伯父遗照,堂兄道荣敬 上。”
我再仔细一看,这不就是父亲撕毁的 那张吗?不对,眼前这张照片的眼睛似乎 有着更多岁月刻划出的深沉。我提高照片, 对着嘉陵江和长江合围成的那座小山上望 去,离山不远处就是那艘客船,晃悠悠地、 一点也不在意客船上急着要回家的游子, 反正是早是晚,总会到达目的地的。
“当初要保存这张照片并不容易,那些 红卫兵要是看到我们家里有张学士照,那 我们肯定会被斗争的,”堂兄慎重地说,“ 不过我还是不听我爱人的劝告,私底下留 了两张,一张在几年前寄给了你父亲,另 外就是这一张了。”
※ ※ ※
这张照片随着我回到了美国,半夜里, 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告诉自己这不过是时 差的缘故。不管怎样,我点起了桌灯,桌上 三伯父的照片还没收起来。我望着他细致 的眼神,丰厚的嘴唇似乎想要开口告诉我 什么,可能是另一段故事吧。我还没等着 他说,也还来不及向他倾吐我心中从来没 有向他人说过,但一直想要同他说的话, 突然一阵香味让我分了心,像是从好远好 远的地方传来,又彷佛是一种很久很久没 闻过、但却曾经那么熟悉的味道。
“哎呀,不是卖蚵仔面线的欧巴桑推车 过来了吗?”一个兴奋而又幼嫩的声音对 着楼下喊着。
“不,那是你父亲爱吃的臭豆腐吧。” 三伯父无言地对我说。。。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恍恍惚惚之 间,看到天花板上吊着的风扇,就像刚起 锚的船身后的桨一般,有力但却缓慢地转 动着。我侧过头来看着熟睡的妻子,摇着 他说,“咱们去吃臭豆腐吧。”
“拜托,你做给我吃,这是美国,不是 台湾。”翻个身,她又继续睡了。
“噢,是啊,”我这才真正清醒,“当初 在台湾没有认认真真地吃,把臭豆腐的味 道牢牢地记在心上,现在想吃都吃不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