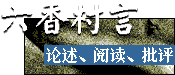·楚 尘·
越过界限,消 除阴影与隔阂
A、对背叛者的背叛回眸脑海里与现在很近的文化记忆, 才仅仅几年时间,当时迫切需要吐故纳新 的中国文化在西风东渐的浪潮中扮演了一 个多么不合时宜的角色:它在一种两难的 场合把自己逼到一个尴尬的境地--头脑 过分发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没能挺住自己 更没有经受住考验,他们在昏昏然中被西 方的各种话语搅得神魂颠倒如坠雾里,在 现代与传统之间,在借鉴与吸收之间,在 取长补短的扬弃征程中,他们没能在震耳 欲聋的喧嚣中清醒自己,而是把自己的双 脚踩在别人的脚印上亦步亦趋,那种蹒跚 学步的姿态下走出了一个又一个冀图在学 术上一步登天的“学人”……一段时间, 这种别扭的学风感冒般地传染一时。
米兰·昆德拉是那时被煮沸的话题之 一。
最初被米兰·昆德拉吸引完全是从《 小说的艺术》中获得了某种契合内心气息 的东西,尤其是他在论述七十一个词时所 持的美学态度,而且他还从德语 Kitsch中衍 生并创造了“媚俗”这个侵蚀人类心灵的 普遍弱点的形容词,它似乎道破了文化工 业时代的病态本质。然而,骨子里的昆德 拉是最为媚俗的,当我再来阅读他的《生 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为了 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不朽 》等作品时,我完全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 觉:一个口口声声反对、抗议媚俗的人恰 恰是做出媚俗举动的人,这种言行互相背 离的阴影使我以惋惜的而不是信服、欣赏 的心情阅读着他的作品;其实,昆德拉的 小说无非是用性、政治、纯洁与粗鄙的爱 情、国家社会主义等串制起来的一件时髦 的文化外衣。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 白了他的小说何以满足和占有了大众对文 化的好奇心,以及其后来何以能够捷速地 穿过文化阶层流入到市井深巷的缘由。
但是,遗憾的是,昆德拉先生并没有 从自己相互矛盾的东西中看到自己的缺陷 ,而是喋喋不休地连篇累赎地写文章抱怨 人们误解甚至曲解了他本来的意图,他还 抱怨人们对他的作品错译得离谱,这种类 似掩耳盗铃的举动无异于把别人看出的破 绽又从里到外兜底翻了出来。或许,《被 背叛的遗嘱》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他的个人 延宕的思维与想象力、理解力、判断力严 重脱节时产生的“怪胎”。
尽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噱头:许多艺 术、艺术大师在他的笔下交叉进出;有出 乎意料的甚至连他本人都感到惊奇的思想 火花;以及种种看起来似乎充满积极的肯 定与否定的美学精神。然而他对卡夫卡、 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瓦格纳等艺术大 师的指手画脚是毫无道理的,他甚至批判 阿多诺对斯特拉文斯基的曲解。阿多诺让 昆德拉气愤的居然是,阿多诺用短路的方 法找到了自己的一种态度,而不是寻找一 种认识的意图。这太可笑了,昆德拉在此 大错特错。在二十世纪中叶,很少有什么 具体的、极具典型的契合阿多诺个人内心 气息的音乐实例,可供他用来缓解自己对 音乐衰落的悲观看法,阿多诺尽管有他当 时的局限,但他毕竟通过对斯特拉文斯基 、勋伯格、瓦格纳等音乐大师的音乐实例 的分析,精辟而冷静地俯察到:“今天不 论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音乐,都是以可能存 在的最清楚的线条勾画出了切断当今社会 的矛盾和裂缝”,尔后,他还马上补充道 ,“同时,音乐借助这个社会产生的最深 的裂缝和这个社会相分离”。昆德拉能理 解吗?他在音乐上的禀赋和感受能力比起 阿多诺不知要逊色多少倍,昆德拉只是做 过一个通俗的爵士乐手,而阿多诺不仅是 一个天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一个 严肃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他曾诚挚地感谢 他从20世纪20年代的勋伯格的现代音 乐学派中吸取的革命性的无调性技巧,应 该说他对音乐实例的分析是颇有见地和权 威的。昆德拉的这种与事实不协调的指责 使我们不能不从他的美学趣味中见出问题 。
卡夫卡生前的平庸的好友麦克斯·布 洛德是否背叛了他的遗嘱尚待考证,这个 遗留的历史问题其实不关读者的事。它无 非暴露了当时的可能事实:卡夫卡对自己 与自己所处时代的疑虑,他或许怀疑自己 的感觉的能力--自己是否真实地表现了 那个时代。这种犹疑的心境使他当时不能 果断地下定消毁自己作品的决心,以致把 这个权利交给了布洛德。虽然这个结果是 否可靠尚难有人证实,但卡夫卡动摇了自 己对世界的看法是有迹可循了。昆德拉一 直对此纠缠不休,他一方面感叹如果没有 布洛德,人们在今天甚至不会知道卡夫卡 的名字,另一方面又大力讽刺曾经搞过写 作的布洛德的小说平常得让人难过,以及 布洛德对现代艺术一窍不通,他甚至抱怨 布洛德在自己的作品《爱情的欢喜王国》 中歪曲了卡夫卡的形象。这算什么呢?难 道我们所面对的读者均是一群笨蛋吗?显 然不是。计较布洛德个人的品性根本毫无 必要,退一万步说,假如没有布洛德,我 们或许不会这么早就知道在世界文学位置 上的卡夫卡,或者知道得更晚更少。这一 点,真值得向布洛德致敬。问题是这不算 真正的问题,它太接近于虚无了,昆德拉 先生有什么理由在此饶舌?
因而,我们不能不说昆德拉为这些问 题斤斤计较是无聊的。并且,他在道德上 、智力上或美感趣味上与卡夫卡是难以类 比的,卡夫卡永远是横陈在他面前的大山 ,他须仰视,才能看清卡夫卡的轮廓。我 们从他对卡夫卡的理解、对阿多诺的横加 责难中可以看出他的变味的审美方向。
小说应当提出问题,而不是化解问题 (化解是哲学和美学的事情)。这大概正 是卡夫卡与昆德拉之间的最本质的区别。 我曾经认真研读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 ,我发觉他有时对小说的意识和感觉的清 理是非常准确和到位的,但是,更多的时 候,我觉察到他陷入到了一个自我设定的 陷阱中不能自拨,他满足于沉浸和陶醉在 自己的自圆自说中。到最后,我忽然发现 ,昆德拉已经被自己在叙述中不停地产生 的矛盾包围了,他根本就没有突围的能力 。但是,昆德拉先生喜欢为自己辩护,这 正是我不喜欢他的一个方面。在《小说的 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饶 舌的地方够多的了。
我们来看,昆德拉先生明明知道:
“小说有某种功能,那就是让人发现事 物的模糊性。小说应该毁掉确定性。这正 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误解的根源。
“小说家的才智在于确定性的缺乏, 他们萦绕于脑际的念头,就是把一切肯定 变换成疑问。小说应该描绘世界的本来面 目,即谜和悖论。
“小说的智慧则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 。人的愚蠢就在于有问必答。”
我们发觉,昆德拉先生也有不糊涂的 时候,可是,我们又发觉,昆德拉先生做 的与说的有多么大的距离,他的言行不一 的举止是多么令人失望。在昆德拉的小说 文本中,他有的是具有形式意义的写作技 巧,有的是一些矫情的添油加醋,他华而 不实;他所追求的模糊性,他渐渐乐道的 那些小说的智慧跑到哪儿去了呢?他力图 彰显的一切是那么地接功近利,他的作品 还有什么是可以隐蔽的?一味地指责和声 讨昆德拉先生好像不是本文的目的,还是 去看看卡夫卡的伟大的做派吧。卡夫卡从 来不怕深渊,他甚至认为只有丧失自我才 是通向深渊的唯一途径,因此,他用他的 身心,他的整个灵魂,面对这个布满陷阱 与污浊的世界--他在孤独中感受到了一 种可怕的畸形现象,一种对时代的准则格 格不入的感觉。
卡夫卡用对世界充满焦虑的幻象代替 了客观事实,这与昆德拉隐蔽在事实背后 的举动是格格不入的。卡夫卡之后,事物 再也不会是主人公的模糊灵魂的模糊反应 ,也不是他的欲望的影子与痛苦的映象, 而是在它经过模棱两可的曲折的旅程之后 回归自己的属性。我们反对某些强加于别 人以求得暗示自己内心能力的人。昆德拉 理解别人之后又掺进了自己的想法的做法 ,是明显有些滑稽的。面对他炮制的这个 杂烩,怎么吃它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胃口, 难道有人为了适应它而强迫自己的胃口? 意味深长的是,昆德拉是否偏离问题好多 人还看不透。其实不论我们是否赞成还是 拒绝了他,甚至也不论我们是否接受了卡 夫卡对世界焦虑的看法,我们的判断力应 当不必取决于别人以何种方式进行说教, 而是我们的心中应该自有自己的主见-- 从那些庸俗的常识、约定成俗的文本中脱 离开来。
B、缺席与到场:寻找悬挂在时间中的碎 片
时间不是没有重量,时间的不可回复 性只能使我们倒逆着回溯跌落在记忆中的 碎片。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那么时 间就永远不会停止给其顽强的重击,那些 被伤害的残片总是东一块西一块遗落在人 类有限的记忆里,所以时间之链虽然连续 不断,但历史从来就未曾连贯过。碎,并 不等于损失殆尽,我们常常能够从中俯拾 一些充满棱角和锋芒毕露的东西,但历史 的真实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深有疑虑的 ,罗伯-格里耶当然也毫不例外,大概还 由于害怕记忆失真的心理在作崇,他偏偏 打着“传奇故事”的幌子,或许只是想以 此为屏障,借以掩蔽自己对历史记忆的谬 误之处。然而,奇怪的是,罗伯-格里耶 并非为了重现历史的片断,他个人可能也 无意这么做,虽然《重现的镜子》是作者 “因短暂的瞥见而留下的个人回忆”,但 这本书并非是其自身历史的总结。即便涉 及到与作者本人休戚相关的故事,他也从 不作过多的卷入和叙述,罗伯-格里耶自 有其高明的处理办法--他总是使它们戛 然而止或擦肩而过,说白了,他只是在利 用这些故事作为自己叙述故事时的跳板, 正是凭着这种巧妙的迂回的办法,罗伯- 格里耶才能够游刃有余地将自己身边的那 些“无足轻重的琐事、空隙和极其巨大的 事件交织在一起,并把自身存在的不确定 性与整个现代文学的不确定性统一起来” ,形成了自己卓尔不群的叙事风格。
罗伯-格里耶一直竭力反对以往的那 种一贯的、世俗的陈辞滥调,他不喜欢而 且深恶痛绝于那些在传统的阴影里躲躲闪 闪的东西,他更反对那种对于秩序的盲从 ,并且慷慨激昂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 真的非得在秩序和混乱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的话,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混乱。罗伯- 格里耶的立场与其说是固执的,不如说是 最坚定的,他懂得在最为合适的时候把自 己的感觉巧妙地安置和渗透在--那些已 被他击碎的废墟之上。所以,以传奇故事 题材及其矛盾的探索性实验来贯穿《重现 的镜子》的至始至终,在罗伯-格里耶看 来是非常必要,因为他感到它最适宜表现 那种处于永恒的不相称状态中的秩序与自 由之间的殊死搏斗,最适宜表现理性的分 类与毁灭或者说是混乱之间的不可调和的 冲突。在法国,那些持正统观念的左派人 士曾经在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对罗 伯-格里耶进行无聊的横加指责,说他的 作品缺乏“参与意识”,“容易使年轻的 一代斗志涣散”。在一个有着优秀文学传 统的国度,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人为的 障碍,是令人吃惊也是令人遗憾的,好在 这一切早已随风飘逝,罗伯-格里耶的意 义已不以那些左派人士的意志为转移,他 已凸现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
也许,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更普遍的 问题向罗伯-格里耶提了出来:为什么需 要那么多的圈套和陷阱使他的每一部作品 都那么难读呢?进而,人们甚至还会从各 个方面追问:为什么不把事情说得更简单 些、不把自己置于公众可以理解的范围、 不作必要的努力以便更能被理解呢,等等 。这样的问题不仅仅针对于罗伯-格里耶 ,它们还可能扩散到博尔赫斯、科塔萨尔 等小说大师那里。面对这些十分荒谬的问 题,罗伯-格里耶只能无奈地声明自己的 写作是对他本人的一种反抗,同样也是对 公众的反抗,他要不停地致力于一种在光 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无拘无束的叙述,并且 将它搏斗的种种逆境精确地表现出来。从 《重现的镜子》这个文本的几个含混的发 展线索我们可以察觉,罗伯-格里耶的意 图在故事的核心形成可能之后,已渐渐地 彰显出来:他不仅仅要向文学史挑战,而 且更要向那些已成事实的固有观念挑战。
在罗伯-格里耶的心目中,文学史早 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然而,这种变 化仍然在距他非常遥远的地方观望着他, 令其可想而不可及。罗伯-格里耶显然对 这一未能实现的现实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重现的镜子》假借“传奇故事”式的文 本性尝试或许正是被逼无奈的他对传统文 学史进行的一次逃逸与放逐之后的重新排 列和安排。当然,《重现的镜子》的根本 意义还不仅仅在于这一点。
一个作家的长处或许正是其短处所在 ,当我们说罗伯-格里耶最擅长于一种飘 忽的、游离的、令人费解的、变化莫测的 甚至时而脱节时而又重迭的表现能力时, 其实也似乎在说他最不擅长于背离这些能 力的能力,在《重现的镜子》中,罗伯- 格里耶依然没能逃脱自己在《幽灵城市》 《金姑娘》、《橡皮》、《嫉妒》等文本 中的叙述阴影,我们仍然从中感到那些从 前的气息在里面不停地晃荡。
亨利·德·科兰特是个什么人物呢? 罗伯-格里耶个人与他并没有什么交往, 甚至可能从来没有跟他面对面地在一起过 。但罗伯-格里耶为什么总是不遗余力地 一再提起他?这似乎并不难解释,罗伯- 格里耶只是想重现一个逝去的部分历史的 片断,一个个体心灵所捕捉和感受到的一 个曾经的时代气息,罗伯-格里耶经历过 法国革命的两次失败,他总是“明显感到 所有非正统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经过保持沉 默的一段短痛之后将会很快转向右翼的。 ”当他年老的时候,再面对这段记忆时, 这些历史的呈现已经面目俱非,罗伯-格 里耶从心里不得不对历史提出质疑,他嘲 笑自己不是历史学家,否则就该“重建一 种第三真相”了。因此,罗伯-格里耶从 未曾中断对科兰特的叙述是有原因的,他 只是想保持“重现”的意义。
罗伯-格里耶的写作是一种孤独的、 固执的、超越故事和时间的研究,他在这 本书中集传记、虚构、文学理论为一体, 巧妙地将自己的家庭生活、童年经历、夫 妻情感、创作及论战情况凝聚在一起,具 有强烈的关于美学、哲学、历史、文化学 和文艺理论的理性思辩,同时,他还不失 时机地记下了许多关于萨特、加谬、罗兰 ·巴特等一些艺术大师的珍贵文献及评价 文字,这些或许正是此书关键之价值所在 。我觉得他对萨特的论述是非常独特而精 辟的,它甚至超越了一大批评论萨特作品 的批评家的头顶,他是这样论述让-保罗 ·萨特的:
“就其计划来看,萨特的作品是一个 失败。但是这个失败如今倒使我们感兴趣 ,使我们很有感触。他想成为全人类空前 绝后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最终或许成为 新思想结构的先锋:不确定性、活动性、 失控性。今后,人们会清楚地看到《存在 与虚无》这本书的结束语‘无意义的激情 ’距离让-保罗的‘就算我什么也没有说 ’这句似乎相差很远的话并不太远。”他 说得如此中肯又一语中的。
罗伯-格里耶说他是用一本小书的篇 幅从侧面审视别人与自己是极有道理的, 因为“现实具有非连续性,它是由一些没 有缘由的并列事件构成的,其中的每个事 件都是独立的,它们的突如其来的方式偶 然地、无缘无故地不断显现出来,因而更 加难以捉摸。”所以“只有靠着第三者的 叙述,人们才能够了解一些难以组合的片 断。”
实际上,罗伯-格里耶在这里只不过 是试着说一说他当时是怎样看待自己周围 的那些事的,或者是他现在用“比较主观 的方式,去想象当时是怎样看那些事的。 ”一个被想象所包围的恍惚意识,由于对 从前剧终和曲末了的事情的解脱,使作者 与现在的存在重新产生了联系,在现实的 态度与想象的态度中穿行;这种像梦境一 样的审美观照,无异让人从现实回到梦境 中苏醒!
正如罗伯-格里耶在结尾描述外祖母 从昏愦的脑袋里似乎自言自语的话:“傻 瓜,哪里会,茶,永远是不会喝完的。” 是的,水就是现实,而记忆永远是泡在水 里的茶叶,与我们隔着一层透明的障碍, 时间稍稍一长,我们便只能从浓喝到淡, 越喝越淡……
在阅读罗伯-格里耶的作品过程中, 我时常想起他曾经说过那些话:
“在我们周围,世界的意义只是部分 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总是有 争议的。艺术作品又怎么可能预先提出某 种意义,而不管是什么意义呢?……现实 在它的发展过程过去之后,也许会具有某 种意义,也就是说,在艺术作品完成之后 。……我们再也不相信僵化凝固、现成的 意义。这是赋予人的陈旧的神化的秩序, 以及其后十九世纪理性主义的秩序。但是 关于人,我们提供的是这样的希望:只有 人创造的形式可能赋予世界以意义。”
这或许正是罗伯-格里耶站在他作品 的背后,为我们递上的一把钥匙,他并不 打算永远关闭自己的大门,他把开启的权 利留给了我们。
C、一个被创造了的个体心灵的历史
“摇蓝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 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两片黑暗的永恒 之间一道短暂的光的缝隙。尽管两者是相 似的双胞胎,人,就像一条规则,看出生 以前的深渊,比他前往的那个更镇静一些 。然而,我知道,有一个年青的时间恐怖 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 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于恐 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 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认 识到他根本没有存在于那里,也没有人为 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 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 是某种神秘的告别。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 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 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 也是空的,好像,在事情相反的过程里, 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
几年前,我在朋友那里无意中翻到《 说吧,记忆》这本并不起眼的小册子,当 我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时,我一下子就被 它的文字和叙述震住了,我带着幸福而颤 栗的心情在一种极度愉悦的享受中急切地 读完了它,我到现在都不能平息自己对这 本书的激动之情。它在我的阅读经历里, 是一部唯一可以与《词语》相媲美的自传 体的作品。与《词语》不同的是,《说吧 ,记忆》的作者并没有像萨特那样--把 想象中的事件、把虚幻的东西变成了现实 ,然后抵达和逼近了存在的深渊,以贯彻 自己一生的哲学使命;纳博科夫是凭着对 词语的非凡的控制能力,在现实与虚幻之 间神奇地游荡和跳跃,他营构的是一个被 自己重新创造和整合了的世界。
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说吧,记忆 》是一部举足轻重的作品,它远远地超越 了《洛莉塔》的分量。美国另一名著名作 家厄普代克在读到《说吧,记忆》的时候 ,便隐然显出宛如进入天堂的感觉。他亲 自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撰文盛赞这部 颇不寻常的小说中“那些美丽的用语,曲 折的思想,深沉的思绪,使其它的一切看 来那么平淡和灰暗无光。”在文学史上, 一个作家评介并盛赞另一个与他齐名作家 的作品是比较少见的,这显出了《说吧, 记忆》是一部非同凡响的书。那么,《说 吧,记忆》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说吧,记忆》虽然是一部回忆录, 但其与文学史上的任何一部回忆录都有质 的区别,它没有单纯地凭借往昔的记忆来 增强回忆的氛围,也没有依附在自己独特 的色彩斑驳的道路中,更没有将自己个人 的身世无限膨胀成自言自语的话语。纳博 科夫的创造就在于他的写作是一种智性的 、充满光辉的灵性普照,他对于自己生命 的间隙(1903-1940年)的经历 :“生命中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早期教育 ,频繁的国外旅行,对蝴蝶的酷爱和捕猎 ,写诗,结交女友,十月革命,在国外的 生涯”等等,并没有作多少纯客观的描述 ,而是依靠自己丰富的知识、洞察的见识 及自己充满创造的想象对现实进行改造, 使一个本来平静、顺应时间流程的客观世 界散发出强烈而迷人的韵味。另外,纳博 科夫独特的文本形式及卓然一家的语言风 格,更使本书的构思和布局充满奇诡,跳 宕,曲折,加上他的充满隐喻和迷宫的结 构,使读者的思绪不断地向存在的核心跌 落,向最美的也是最难以言说的生命的偶 然性和必然性挺进。
纳博科夫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并创造 自己的知识系统,他甚至并不去详考因果 ,遵循逻辑,而是相信海德格尔所说的: 世界在时间性中到场。正是凭借对暗淡了 又重新发出光泽的时间的审视,纳博科夫 得以在时间感的显露中从自省意识的开端 一直追溯到生命意识的觉醒,他在时间上 跨越37个年头,在地理上从圣彼得堡延 伸到圣纳泽尔,形成了纳博科夫个人回忆 的一个有系统的集合。同时,也正是对记 忆有着说不清的障碍,那些生命中空的点 ,模糊的地带,微暗的范围,居然被幻化 成美丽的焦点,闪烁并指引着纳博科夫的 视觉与触觉走上一条真正的伊甸园之路。 纳博科夫感叹“宇宙是多么的小(一只袋 鼠的口袋就能装得下它),倘与人的意识 ,与仅仅一段个人的回忆和它词语的表现 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与弱小”。
此外,作者对鳞翅学、国际象棋和诗 歌的年轻激情和计谋,对于田野里和审视 光亮里的多种追求,使他受过训练的目光 有种超自然的敏锐;加上他将自己的俄国 记忆用英语重述--俄语复归--英语再 现的史无前例的三重性创造,使作者在记 忆的反面更能从容用想象考察“出生以前 的深渊”和“我们的存在中两片黑暗的永 恒之间一道短暂的光的缝隙”。这些都是 作者个人的忧伤眼睛中的隐痛。作者知道 自己永远不会完成自己的思考,但他并不 放弃希望有一天再写一本《说下去,记忆 》的书,以覆盖自己在1940-196 0年在美国度过的年月:“某些挥发物的 升华与某些金属的熔化”仍然在作者的“ 线圈与坩锅里”进行着的记忆。
纳博科夫的审美对象至少已经还原在 时间中,因而它是非现实性的,作者的想 象不仅超越了时空,超越了现实,也超越 了存在。我们没有真正倾听到纳博科夫显 现了的从前,而是在想象中倾听到了纳博 科夫的想象与创造,所以,无论是读者还 是作者,他们面对的其实都是一种诱发出 的梦境--不但对我们所注意或厌烦的东 西视而不见,而且,这些东西也使我们避 开了所有尘世间的束缚。这种虚像可能纯 粹中性化了或彻底破坏了记忆中曾经的对 象,但却不能消磨其本质。从容观照记忆 在人们的想象中的行为,似乎暗示了观照 对象的存在。虽然实际上从一个世界到另 一世界的过渡是不存在的,美只是适用于 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它意味着对世界 的本质结构的否定。但也恰是这种双重的 变化使一种记忆活动转化为一种表现行为 ,转化成纳博科夫对自己在欧洲往昔的创 造性回忆,转化成纳博科夫对自己“生命 两端非个人的黑暗中最微弱的个人的闪光 ”的精彩辨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