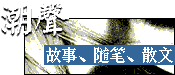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吴晨骏·
城市和乡村
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放弃了贫穷和落 后,也放弃了原始的活力。我30岁以后 ,尤感活力对我的重要。在漫无边际的苍 白的日子中,我的体力在缓缓下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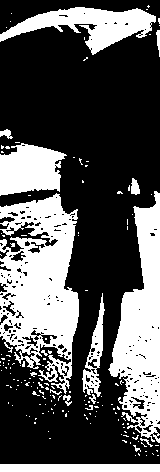 当
我偶尔伸出头,从自家的门口,看向灰蒙
蒙的天空,我的视线和天空一样疲软。
当
我偶尔伸出头,从自家的门口,看向灰蒙
蒙的天空,我的视线和天空一样疲软。年初,我搬到现在的地方,在收拾房 间时,隔壁老头拖住我的衣袖悄悄问,房 租多少钱?后来又问过好几次,但我都没 有告诉他。我不懂他为什么老是追问我房 租的事。与他贴身站着,我厌恶他嘴角的 涎液。隔壁这一家,除了老头,还有三个 人:老太、女儿和外孙。时间久了,我对 他们不像刚来时那样处处躲避了,我甚至 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呢。我在门口看天空时 ,老头也正在门外浇他干瘪的盆花,嘴唇 无声地嗫嚅。
实际当我的视线与天空接触时,我接 触的并非天空。我接触到的是被我的经历 过滤了的天空的概念。我早就与我幼年时 的蓝天远离。我跟随着另一个我,抛弃了 乡村来到城市,而另一个我也并不比我更 多地了解城市,不比我聪明,也不比我更 适应城市的汽车尾气和街道上毫无感情色 彩的行人。他的任务就是带领我向城市进 军,把我丢却、抛进、扔在一个虚幻的城 市里,迫使我接受城市的教育,接受努力 做人的训诫,不管徒劳与否。
我走在夜晚的街道上,以为这就是城 市最好的时刻了。我无钱乘坐的士,只得 步行回家。街灯淡黄的光照着商店橱窗, 也照着我的躯体。风在穿梭,弹奏着我紧 张了一天的神经。我是一个具有某种职业 的人,这是我的身份。即使此时街道上只 有我,我的身份也不会遗失。我和我的身 份一起在街旁享受着城市的夜晚。在城市 ,只有流浪汉没有身份,流浪汉受人歧视 是因为他没有身份。而没有身份之人,名 义上便不属于城市了。
我无法从城市归回乡村。我怀念乡村 ——我活力的源头,却宁愿在城市中衰老 和枯竭,我不断消耗着乡村对我幼年的滋 养,却不能重新去体会乡村的益处。乡村 生了我,而城市改造了我。
在这个租来的房子里,我住了近一年 了,我越来越感到隔壁那家缺少了一个人 ,即那老夫妻的女婿、那女儿的丈夫、那 小孩的父亲。有一次我似乎听我老婆说, 那个女婿、丈夫和父亲是个当兵的。但当 时我没深究,现在我忘了我老婆是否说过 这样的话了。确实的一点是,常到隔壁那 家来的男人,是小孩的舅舅。一般到了星 期天,小孩的舅舅就提着一捆菜钻进隔壁 的门洞。
我们住老式楼房的2楼,东西向,紧 挨汉西门大街。街道两边开着一间间小饭 馆。大清早炸油条、中午和晚上炒菜的油 烟,飘向我家门口。单是油烟倒也罢了, 有时飘过来污浊的臭味,我的眉头不由得 皱上老半天。小孩的舅舅在楼梯口出现, 迅速穿过走廊上的浓油,逼近我。这是他 的休息日,也是隔壁一家欢乐的时刻。那 小孩从黑暗的门洞里跳出,扑向他舅舅。
一天朋友小顾来访,我趿拉着拖鞋, 和他去不远的汉西门广场喝啤酒。我们坐 在一截半塌的城墙下,背对阳光,向散布 广场的女人们身上扫视,无聊地谈论着她 们谁看上去像鸡。一个骑童车的小孩晃过 我们眼前,车后跟着两个妇女。我一愣, 这不是我家隔壁的女人吗。她个头矮小, 脸微微发红。和她并排的那个妇女也很面 熟。他们三个迎着下午的阳光,从我们眼 前晃过。
隔壁淌口水的老头总是给我孩子糖吃 。遇到这种情形,我便对我老婆说:“快 把糖还给人家!”我老婆一把抢走孩子手 中的糖袋--“还给人家”--“我家有 糖”--“你们留着吃”--“谢谢”- -“不用,我家有糖”。早晨,我推开家 门,门前的走廊上摆满了破破烂烂的床架 。老头正给床架涂上暗红色的油漆,他脸 上洋溢幸福的波澜。“嘿,你早!”老头 对我说。
一只东张西望的鸟,在城市中不断迁 徙、筑巢,过一阵子把旧巢扔掉,筑一个 新巢。我就是这只鸟。我的家当在一次次 迁徙中损坏,或失去了原有的面貌。我老 婆在迁徙途中养成了“抹”的习惯,她每 天下班回家,就从厕所的门后取下一块抹 布,在家具表面抹来抹去,在冰箱、洗衣 机和电视机的外壳上抹来抹去。她通常的 形像是:右手抓着抹布,站在房间中央, 警惕的眼神注视着房间里的每样东西。而 这勤劳的人对于做饭却无兴趣。
我做梦,梦见过各种场景和各种人, 梦见杀戮和性交。杀……性交:我将精液 射在一个女人肉体上,醒来发现我的短裤 潮了。我的梦境纯情而伤感。梦中的那些 人头脑简单,只按自身逻辑行事,都穿着 蓝衣服,是皮影人。
近来,我很少做梦了,过度的疲倦和 家庭的喧嚣,挤压了梦境的疆域。当我麻 木地仰视天空时,梦境也向银灰色的天空 中飞去。从乡村到城市,我不自觉地放弃 了贫穷和落后,接受了富足。可几年之后 我又自觉地放弃了富足,自觉地接受了贫 穷。在城市中做一个穷人,最大的不便来 自心理。那些高楼,那些报纸,那些行人 ,都暗示着贫穷是一种罪过。当我贫穷的 时候,我无法忘记我曾经富足的过去。
钱……死神拥有的最锐利的匕首。自 尊、人格、闲暇、平静和坦荡,这些都是 钱的别名。“会有钱的,”这是友人所能 给我的最好的祝词。这是钱的世界,这是 钱左右的世界。我之所以思想,是因为我 要用思想换钱。我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 我藐视钱,而非因为我不思想。
在城市边缘的树林中,我捕捉到一只 蝴蝶。蝴蝶在树枝上一动不动,像死了一 般。我想把它送人,但它死了。我用手指 弹烟灰似地把它弹落在树下的草丛里。落 地之前,它苏醒了,拍打了两下翅膀,仿 佛落花,在空气的浮力中翻了翻花瓣。
我们一行十人沿早已存在的小路,从 山脚往上爬。我们踩着石块,攀援着树枝 ,吃力地爬山。途中我们没有遇见一只野 兽。这就是自然景物了吗?原本豺狼虎豹 出没的山丘和丛林,现在都属于了人。我 们除了看见自己,再看不到野兽。在野兽 与人的对峙中,最终人掠夺了野兽的权利 。到处是人造的自然,人伪造的自然。难 道我们不应对地球上耸立起的摩天大楼心 存疑虑?
那条既已存在的、积满了黄叶的小路 ,在植物园附近。初秋树林弥漫着午后的 光线,显得苍老和忧郁。进入树林不久, 小顾突兀地招呼蹲在矮树丛中的一对陌生 男女。--那男的是我过去的同事。小顾 解释道。来自山石上的细尘,裹在风中, 摩擦我们过于娇嫩的皮肤。我们故意喧哗 ,装出童心未泯、肆无忌惮的样子,在整 个爬山途中不断亵渎着被逐出山林的野兽 们的魂灵。
不停地拍照,不停地变换姿势和角度 ,仿佛我们登山只为了拍照,仿佛我们热 爱这些斑驳的树皮、丑陋的山石和粗糙的 地貌。“越过山岗,前面就是紫霞湖了。 ”谁嘟囔了一句。我想象着紫霞湖的湖水 ,碧绿、清澈,照见天空和大山。我们蹲 在水边,湖水也会照见我们的脸。现在, 去紫霞湖成了登山的目的之一。我从小路 边拣起一根断木,挥舞着,或在地面捣几 下。
我紧随前面的同伴,上到山腰,树木 越来越密集。小路这时不再向上,而是渐 渐下行。透过枝叶的缝隙,我看到远处山 下闪烁的白点,那是紫霞湖的反光。有一 阵白点消失了,因为我们改变了行走的方 向。当我们重新拐到这一方向时,白点就 又出现在枝叶之间。下山的过程中,我一 直在搜寻那些白点,直到我们到达山脚的 瓦房边。“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问瓦 房前洗衣服的老头。“植物园。”老头说 。我们在山上兜了一圈,结果翻进了植物 园里面。我们越过植物园的大门,进入了 植物园。
我曾经在南湖小区租房子,进入市区 的途中,要经过朝天宫。朝天宫,明朝在 南京建都时,作为朝廷举行盛典前练习朝 廷礼仪的场所,也是官僚子弟袭封和文武 官员学习朝见天子的地方。现在这里有两 个民间市场:旧书市场和古玩市场。古玩 市场在朝天宫的院子里,旧书市场则在院 子外面靠河的角落。我的藏书大都是从这 个旧书市场买的。这里的旧书,相对新书 价格很便宜,最高卖到4、5元钱,一般 在2至3元。旧书摊的摊主基本是些无业 人员,有中年、青年和老年人。我为一本 书和他们还价时,他们总是说:“没看到 吗?这是名著!”
我的藏书全是破破烂烂的书,但都是 名著,有海明威、福克纳,有《古斯泰· 贝林的故事》和《春琴传》,有车尔尼雪 夫斯基和契诃夫,有米斯特拉尔的诗集和 塞拉的《蜂房》,有《地理学词典》和《 小儿病的诊断和治疗》,有辛格、三岛由 纪夫和斯坦培克,有司格特和帕特里克· 怀特,有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
寄信从邮局出来,我蹬着自行车滑到 不远的朝天宫。我沿河边搜索书摊。在一 堆乱糟糟的书前,我停下脚步,目光落在 一本书上。库柏的《航海家》。我想买下 它。正在我犹豫间,摊主老头看看天色, 然后开始把一本本书放进麻袋。“我要回 家了,”他对旁边的小伙子说。我的决定 还未明确,他已经把手伸向库柏,缓缓将 库柏放进麻袋。第二天、第三天、从此以 后,我在朝天宫再没遇到那个摊主老头, 他生病或是死了,或是别的原因,我一概 不知。
多少年前,我孓然一身,在大学校园 里穿行。我走出校园门口,进入傍晚饥饿 的城市,进入夜间吃饱喝足的城市。我从 一户户人家亮着灯的窗前走过。窗户里的 人在吃饭、看书、打毛衣,低着头从一个 房间隐没,又现身另一房间的窗里。他们 对房屋外面树荫中的我浑然不觉。在灯光 中,他们干着、想着、谈论着他们家里的 事情,他们完全忽略了黑暗树荫中站着的 我。
我被拒绝在近在咫尺的亲密气氛之外 。那气氛是黄色的,来自灯光。我匆匆行 走在校园附近的林荫道上。我路过林荫道 边一栋二层楼房。我从楼房拐角的窗户看 进去。一个戴眼镜的老太伏在红漆的方桌 上写字。窗户里的灯光是黄色的,墙壁是 白色的。我停下脚步,探头俯在窗纱上盯 着老太。我全神贯注盯着老太,老太在全 神贯注地写字。我想这老太对我来说是一 个“别人”,而我对于这老太则不存在。 我不是老太,也不是黑夜,我是虚无。我 是在虚无中弥散的虚无。
哦,我的家。什么时候我才会有我的 家。那时我发誓我也要有个家。我在自己 的家中忽略家之外的一切--忽略喧闹的 城市,忽略肉欲沸腾的人群,同时无意之 中也忽略了窥视着我家窗户的孤独者。
我的家,现在位于汉西门大街的路边 ,东西向。东面被高楼挡住,唯有下午才 有阳光从西边的阳台照进来。 10月份我接 收阳光的时间是下午3点半。这时我一般 坐在电脑前。阳光爬进了门槛……爬到我 脚边……爬上我的后背。阳光用微微的热 量抚摸我,将刺眼的雪白的光线铺在我的 键盘上。而3点半之前,屋子里阴阴的, 灰色的情绪蒙着黑头巾,在屋子里跳舞。 阳光一进来,就彻底赶走了它们。阳光统 治了我的房屋,使我得到清洁,使我的皮 肤更加伏贴,使身体里的血液变得新鲜。 这是最美好的时刻,从下午3点半开始, 延续到5点。然后夜晚来临,我打开台灯 ……
假如一天全都这样阳光明媚,假如我 有一处新房子,假如我的房子四面用玻璃 做成,我就可以像一棵饱满的、翠绿的青 菜,充份得到光照,吸进二氧化碳,吐出 氧气,在凳子上长胖,长高。我就可以健 康,不受细菌的干扰。
上午我在厨房刷牙时,听到窗外隔壁 老头说:“不要好事变坏事,适得其反呀 。”我轻轻推开窗户,朝外看,隔壁老头 在清扫门前的走廊。他说的“好事”是什 么呢?我把牙刷在嘴里捣了捣,心里嘀咕 ,莫非他说自己在做好事?扫走廊也该算 个好事了,可是这怎么会变成坏事呢?让 人费解。他扫地的声音“沙沙”的,很响 。他移动笤帚时,走廊里扬起阵阵灰尘, 把他包裹。
一张俏丽的脸,转眼又显得很平庸。 俏丽的脸来自电视机屏幕,而平庸的脸则 和我的脸相像。我以最简单的方式(类似 动物的方式)去爱慕那张俏丽和动人的脸 。我这样做的后果是徒增失落和伤感。那 张俏丽的脸本是另一具人体的抽象的符号 ,我却要真实地去靠近它。我却要让那符 号在我内心生根,在我的肉体中长芽。我 却要让那符号吞噬我,在夏天的夜晚。
我站在一座桥上。桥在湖泊的中央。 远处是高楼的灯火,湖水和黑夜连成一片 。我穿一件很长的衬衫,衬衫的下摆拖到 膝盖,像个印度人。我依在桥栏上,面对 一张模糊不清的脸。那脸偶尔看我,多数 时候看着茫茫黑夜。它与黑夜,由同样的 物质组成。它们彼此交流,无限亲密。
水泥桥栏粗糙的颗粒深陷我的掌心。 我对那俏丽的脸说:“哦,湖水。”脸也 说:“湖水。”我黝黑的目光穿透黑夜中 的光年,直达那张脸。脸说:“我们回去 吧。”我的身子慢慢疏远了桥栏,但仍停 留在桥上。“那我们就回去吧,”我刚说 完,身子就猛然越过桥栏,朝湖水中栽去 ,一开始像海豚,然后像一截圆木,静静 躺在湖底。水流的萧声缠绕着我--一艘 长满水草的沉船。
我的下沉,打搅了一群小鱼的安睡。 鱼儿们喧闹着,从湖底的淤泥中飞起,仓 惶逃蹿,无能地刺进黑暗的水域。慌乱中 的碰擦,增加了无谓的恐惧。我正面朝上 ,看那些高楼折射水中的灯光,像天上繁 星。久远恬静的景象在我心中泛滥,我手 执蒲扇,躺在散发着麦芒气味的打谷场上 ,辨认北斗七星的形状。我对星星的迷惑 不解,使我心地纯洁。而那俏丽的脸,却 使我感到自己很脏。湖底的我,断绝了对 脸的向往的我,是质朴无瑕的我。湖水刮 过我的皮肤。乡村静躺在城市的湖底。我 是乡村的化身。
(1998.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