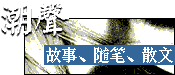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叙 灵·
致命的诱惑
歌德在他的长诗《浮士德》中,自始至终用 一种智者的语气阐述一个问题: 一个人为抵挡住诱惑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说到诱 惑,并非如传统意义上的定义-- 所有的诱惑皆是邪恶的。我想正如人一样,诱惑 也有好坏之分。在一切的诱惑中, 文学艺术的诱惑堪称最强大、最美好,同时又是 最致命的。多年以来,我的生活 一直因它泛起阵阵波澜,我的痛苦和欢乐皆由它 酿造。一个月以前,我从有天堂和地狱之称的深圳 ,来到福州谋生。刚到福州那阵 子,因孤单寂寞的驱使,也认识了一些同事。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经接触发现 这些同事大多都是一些极现实、世故的人,很难 从他们身上察看到与灵魂闪光有 关的东西。日头一长,随工作环境滋生出的一些 人与事,渐渐地,把我一颗初涉 陌生地那种新鲜清明的心,搅和成一坛混浊的水 。我感到窒息的呼吸和无聊的沉 闷。一天傍晚,我和一位来自西安的同事,沿一 条开满黄色野花的小径漫步,在 不时碰出思想火花的闲谈中,不觉我俩已来到闽 江岸边。站立在堆积如山被夕阳 染红的河沙上,背靠一望无际的荒草地,聆听晚 风的轻盈和远逝。我俩由大江宽 广的流逝和野地的荒凉谈到人生以及与人生密切 相关的文学。虽然我这位可爱的 同事对文学并不是很精通,但与他的一番行云流 水般的闲谈,我还是从中品尝到 了一种久违的幸福。由此,我觉得这个黄昏是无 限地温暖和丰满。时间流动如风, 从我们时而高亢时而平静的谈话声中滑过。天完 全暗了下来,当我和同事从河边 返回到宿舍门口时,我摸了摸裤袋上的钥匙串, 顿时吓了一跳,天啊!在荡涤心 灵的交谈中,我不知把房间钥匙丢到哪里去了。 此时此刻,除毫无怨言接受不能 入室的事实外,不得不在内心反复感叹文学之神 对我的再次诱惑和戏弄。
一九九○年,我在一家乡村供销社做营业员 。在乡村工作,逢赶集之日有些 事做外,其它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眺看乡村农田、 谛听近处吊井吱嘎声的无聊之中 度过。那时,迫切希望做一件能宽慰精神的事。 有时实在闲得慌,便一个人偷偷 地跑到稻田旁看农夫耕地插秧;或者独自爬到荒 坡上,呆望远处的大山和原野上 的村庄。尝试各种解闷的方法后,最终发现唯有 读书能给人以充实。乡村交通闭 塞(一天只通一趟班车),文化落后,要找几本 有趣的书较困难。费尽力气借来 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陶潜文集,如获至宝,彻 夜挑灯贪看。以后每日反复阅读, 直至闭上眼,也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便又想着 找些另外的书来看。乡村不仅借 书难,就是拿着钱也买不到一本书,于是每逢休 假干脆不回县城看父母,一个人 悄悄跑到离乡村几百里外的吉首市,甚至前往省 城长沙去买书,每次花去平时省 吃俭用攒下来的积蓄,一点儿也不感到心疼,反 倒怀着痛快的心情带着一大包书 籍返乡,在满载的归途中,一种似风的幸福始终 涨满了我全身。也许是因为我不 成系统地看了一些中外诗篇和哲学著作,或者是 乡村的日头过长而难熬的缘故, 我开始尝试写一些连自己都不十分了解的诗。我 不想做一个诗人,写诗只过是帮 助我打发一份悠长无聊的日子罢了。混沌中,我 象乡村的一切种田人一样,以自 己的方式过着上天派定的一份生活。一天,我拜 访了一位回家乡度暑假的农家大 学生,并带去了一年来写的诗。这位校园诗人, 湘西地区高考的文科状元,看完 我写的东西后,稍稍露出了几分惊诧的神色,然 后不客气地说出一大堆批评意见。 之后,我们便成了朋友。从他那里,我知道诗该 怎样写,什么算是真正的诗人, 他还特意向我介绍了二位天才诗人海子和李杰波 。直至今天我还在叹服这位朋友 非凡的鉴赏力,因为若干年以后中国大地上真正 能留下诗名的只会是海子和李杰 波。当一个人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诗歌后,他便 开始幻想超越他所敬仰的对象, 在夸大的想象中他总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位诗人。 就是在这种近似于自我欺骗的巨 大漩涡般的引力中,我极其天真地辞去公职,断 然结束了二年乡村生活,把自己 抛向了流浪。三年的流浪,一段漫长而又短暂的 时光,我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凭 借一股什么力量挺过来的,其间我经历过多次流 血的疼痛,其间我结交了几位一 生的朋友,其间我写出了几首从心灵喷发的诗。 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别的收获。 苦于生存的巨大压力,我最终还是逃往了大学校 园。刚入大学那会儿,我曾在内 心发誓,远离文学,再也不写那种把人弄得一贫 如洗的诗了。然而在大学日子稍 长,我就感到莫名的恐慌,一种强烈的失落在血 管处涌动。总感觉有一件事迫着 我去做,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事。仔细一想,应该 是好久都没有写诗了。接着立即 打开笔记本,拿起笔唰唰地写出一些久憋的文字 ,继而便只有无奈地感叹文学的 魅力是多么地强大,不管我怎么回避它,总也逃 不过它对我的诱惑。
今年夏天,我在深圳找工作,寄居在诗人太 阿的家中。太阿曾无比忧郁地对 我说,深圳连张书桌子都放不下,你一个写诗的 跑到深圳来干吗?一时我竟无语。 后来反复询问自己,慢慢得出答案,这一切仅仅 是由于诱惑,一种致命的飞翔, 我一生都在尽力逃避它,同时我无时无刻不在走 向它。尽管它那么令人痛苦不已 甚至置人于深渊,然而我渴望飞翔,甘愿自己为 一只飞蛾,永远扑向有光的地方。
(1998.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