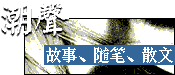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陈放歌·
在 火 车 上
我回家的时候,天正冷。火车上不冷,只是挤。有几次我拿起杯子, 想去打点热水,每一次站起来, 我都看着挤满人的过道,摇摇头对在火车上认识 的校友说:“人太多了!”得到 她的同情以后,我就再一次无奈地坐了下来。
车上的人的确很多,走道里全是人,他们大 多面色漠然,昏昏欲睡的。
天气很好,从上海站出来,一直到南京,沿 线的村庄、公路边上的绿化带一 样一直地流了下去,几乎没有间断。房子多是白 墙绿瓦的小楼,和北方的院落不 同的是,民房很少有院墙,村里也几乎没有什么 闲人。不时还可以看到新建的然 而好象没有生产的工厂。路上每到一个车站,走 道就下空了,但往往我和我的老 乡只能空欢喜一场,片刻,刚刚空了的走道就又 塞上新的人群。
车过丹阳的时候,走道又一次空了。一位乘 客抽空到走道里抽烟,一个刚上 车的男人就坐了他的座位。车开了,抽烟的乘客 回来了,接着就是一场争吵。
刚上车的乘客带着浙江口音叫道:“你有多 少钱?把钱拿出来,看一下谁的 钱多!没钱也敢坐车!”被抢去座位的带着河南 口音的乘客有点“软”了,但他 的同伴却不肯让步,大声地嚷:“你有钱怎么了 ?有钱难道可以把别人的座位占 去?”边上的乘客都小声附和着,浙江人看到自 己孤立无援,只好不情愿地站了 起来,一边往车厢的另一端挤去,一边嘟囔着: “河南叫花子,没钱也敢坐车!”
他这么说的时候,正经过我的身边。怒火立 刻充满了我的胸膛,我告诉自己 要克制,可身体却不由自主的跳了起来,我的手 指着那人,早就陌生了的家乡脏 话脱口而出。“浙江人”呆呆的看着我,好象不 相信有人在骂他,他神经质地摸 了摸提包,一丝惊慌从他的脸上掠过,他的嘴动 了动,终于什么也没有说。“欠 揍!”我边上的两个中年人说,“欠揍!”边上 两个回乡探亲的武警也附和着。
很快,我就镇静了下来,隐隐约约地感到有 点后悔。刚才我骂人的时候,我 的校友拉着我的衣服说了点什么,可那时,我大 约满面血红,顾不上听她说什么。
很幸运,能在火车上认识一个老乡。她是一 个身材苗条的女孩,刚刚知道她 是交大人时,我问她大几,她笑了笑说:“研一 。”老乡情和说错话的尴尬立即 冲淡了我们之间的生疏。等到火车开的时候,我 们已经俨然老友了,那时,她指 着窗外送行的男友说:“我以为他已经走了呢! ”那会儿,我真为她的幸福而暗 暗高兴。
火车的前半程,在骂“浙江人”以前,我们 一直谈着政治改革、文学,和大 多数交大人一样,她在这方面所知不多,而且也 不太感兴趣,后来就说起了就业、 待遇、工资了,女孩开玩笑说:“交大人分‘三 六九等’。”我不懂,她解释说 本科生月薪三千,硕士生月薪六千,博士生月薪 九千。那时候,气氛还很融洽, 但自从我骂了“浙江人”以后,气氛就有点微妙 了,我们几乎找不出话题。
车到蚌埠,走道已经空了,我到车厢头打水 时,发现“浙江人”不见了。回 来时却发现他换了个地方,很老实的样子,也不 象富人,衣服相当平常。我对他 笑了笑,他没有看见。
我对面的两个乘客,一个是二十年前从上海 到洛阳接替父亲工作的工人,一 路上不停地对我们大讲上海、洛阳人情风俗的差 异。另一个则沉默得很,我骂浙 江人的时候,他小声附和,等我安静下来时,他 小声的对我说:“我是郑州人。” 但他的口音却表明他不是地道的“河南叫花子” 。果然后来他说自己在湖北长大, 但已经在上海工作有十年了。
接父亲班的工人,和我们几乎聊了一路,我 们谈政治改革的时候,他迟疑地 看看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他找到机会说: “象你们刚才讲的政治改革,只 能越改越乱。”我和我的老乡都笑着什么也没说 ,他便受了轻视似地急切地说: “下岗,很多人下岗呢,什么也没得干。”说到 了腐败,他认为越改越腐败。我 们讲到上海的治安很好时,他摇着头说:“你们 在校园里不了解情况,上海到处 都是骗子。”然后他捅了一下那个深沉的“郑州 人”:“你说是不是?”“郑州 人”迟疑了一下说:“公开的不多,但很多时候 ,做生意要小心。”他便得胜了 似的笑着对我们说:“是不是,是不是?”然后 又讲上海的房子便宜的800元 就可以买一平方,这一次,不仅我和我的校友不 相信,连“郑州人”也说不太可 能。他接着说起了上海和洛阳方言的差别,说起 了他刚刚到洛阳时遇到的麻烦。 还说起了洛阳前几年两头东北虎在动物园里被人 打死,还有许多市政府高层的“ 逸闻”--大多都不是好事。
车过了徐州,我的老乡累了,我就坐到对面 ,好空出地方给她睡觉。于是, 我和“郑州人”又拉上了。
“郑州人”小时候跟奶奶在郑州长大,上小 学的时候,到湖北十堰“二汽” 工作的父母那儿上小学,他只上到初二就辍学了 ,后来由亲戚介绍到上海的一家 广告公司做事,一干就是十年,他才二十五六岁 ,还没有结婚。
他比工人沉默得多,一路上只是听我们讲话 ,极少插嘴。我问起了他广告业 的情况,说起广告业,他的话多起来了,他不停 地说:“生意不好得很。”他回 忆说九三、九四年生意很好,那时候几乎天天从 早忙到晚,现在生意清淡多了。 一年不过忙三、四个月。不过他承认对自己来说 生意好坏都没有关系:“我是合 同工,签好了合同,一个月拿1500元,有活 没活都一样,我们老板也一样, 是公家的公司,赚了,自己多拿一点,赔赚都不 会有多少。”
他自称所在的广告公司是沪上最大的广告公 司之一。我问他每年的产值,他 说大约七百多万元。看我不大相信,他便解释说 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而广告公 司却越开越多。令我吃惊的是这个公司竟然有1 00多人,还请了两个俄罗斯人 来操作电脑,我心想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车到兰考时,“郑州人”下车了,说要去接 一个人。那会儿,我正在半睡半 醒之间,听到他向“工人”告别,我便在心里默 默地为他祝福,希望他能多拿一 点奖金。
我的邻座坐着两个武警战士,一个在商丘下 车了,我就坐了过去,和另一个 聊了起来。他看上去很年轻,有着一个圆圆的可 爱的娃娃脸,中等个儿,身材不 算强壮,没说几句话就会带出一句“很没意思” 。
我有点唐突地问他是不是刚入伍,他歪了歪 嘴,看着自己的肩章说:“我已 经当了八、九年兵了。”我吃惊地问他的年龄, 他先是说二十四、五岁,然而立 即又局促地说自己虚报了年龄入伍,实际上只有 二十三、四岁,后来他问我的属 相,知道了之后,他说我们都一样大,都是七七 年出生。
他解释说他十四岁时上初二就入伍了,“我 叔叔在那个部队当营长。”他说。 他已经是志愿兵了,不过他对自己的职业并不感 兴趣,“当兵没意思,当三年还 可以,蛮有意思,再长就没有意思了。”他不知 说了多少遍。
志愿兵对自己的兵种很满意。“在部队里只 有两条出路,考军校或者开车。” 他说自己考了两次,第一次名额被人替掉了,第 二次名落孙山,于是就安心当汽 车兵。“再过两三年就可以退役了,我不想再当 兵了。”他认真地说,“部队里 没有意思。”
后来,他讲起了自己的战友,他称之为“河 南帮”在驻地打架的事。“有一 次,我的老乡被六、七十个人背着刀赶着砍,碰 上黑社会了,以后老实多了,再 也不敢惹事了。”
“志愿兵”很关心时事,很佩服朱熔基,“ 这人真厉害,硬是把军队企业给 关了。他打走私,太厉害了,走私把国家的经济 弄垮了。”“志愿兵”唏嘘着: “太腐败了,我们部队两道杠以上的军官,每个 人家里都有几百万。”怕我不信, 他说起了自己的团长在上海花了一百多万买了两 套三室一厅,还有一个以部队名 义开的路桥公司,现在不让部队办企业了,他干 脆转业接了过来,“注册资金一 千万。”志愿兵说。
“应该打走私,部队上走私太厉害了。”志 愿兵说:“要检查,就说是军用 物资,焦点访谈报道过。”志愿兵还提起了自己 出车时的见闻,说起了山里人的 贫困和愚昧,笑话他们都是近亲结婚。然后叹息 自己家乡的不变,“三年前我回 去过一次,和我走时完全一样,没变。”接着又 赞叹上海的变化:“别说三年, 三天就变了样。”
到郑州了,“志愿兵”要下车了。他拉着我 的手使劲地摇了几下,“再见!” 他说,他熟练地抻了抻上衣的衣角,拉了拉领子 ,带上了自己的大盖帽,提起箱 子走了出去。
车出了郑州站,在寂静的夜里行驰着。我的 老乡醒了,一个人跪在座位上发 呆。看见我坐了过来,她说:“要到家了,不洗 脸了。”我说:“不洗了。”
已经早晨六、七点了,天还暗得很。车里开 着灯,外面村庄的黑暗的轮廓在 一片静谧里缓缓地向后方掠去,大约还有雾。
车到了洛阳站,我下车,随着人流向出口走 去,路上大家全都急匆匆的,一 点也不顾及别人的目光。出了车站,外面是一大 片泊着的出租车。不断有人要我 上车,我说:“不用了,我家很近。”
这么说的时候,我很内疚,他们需要钱,我 知道,要不不会在这清冷的早上, 六、七点就等在这儿拉人,但我也没有钱。
我能给他们的只有祝福,但祝福没用,一点 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