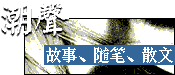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铁 璀·
再 见 故 地
还是那趟车,从广州到了英德已近中午。出了站,是大站镇,再往里过了北江桥才是英德城。趁等人的功夫,以东面的大山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已经受不了那份热了--六月的阳光还是那么炽烈,便赶紧躲进旁边一家小旅店避热。小店老板趁机来拉生意,好在李君很快就来了,雇了一辆三轮摩托去英城。由大站到宾馆,一路穿过了整个县城。还是那条江和横跨江上的桥,街景的变化也不惊人,只是街道拓宽了许多;不过依然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变化,那就是放松和平静,没有了举目可见的大标语之后的放松和宁静,没有了动辄就庆祝什么拥护什么声讨什么的游行、锣鼓、口号之后的放松和平静。
那场运动已过去很多年,仿佛已经淡忘;况且我们又属于一个善于忘却的民族。
不过很多亲历身受过那场运动的人,尤其是运动中深受其害的人是难以忘却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望埠承受了“冲击”之难之惊以后,次年随着地质队又流落到大站,依然充当钻工,住在蚕种场的半间简陋的杉皮屋里。
在游览了闻名遐迩的喀斯特胜景宝晶宫之后,我向李君提出想去蚕种场看看。
去那里看什么?他有点惊讶地望着我。
我说了当年的那段遭际。
三十来岁的李君当年还是个少年,但他对此很理解,很快做了安排,并且请了一位曾在蚕种场工作过的邓女士同行。下午出发,坐的还是三轮摩托。--此地到处都是这种出租车,小小县城竟有上千辆,李君说这是英德的“全国之最”。
在公路边下了车,走到一道围墙前,邓女士说这就是蚕种场。可是我没看到记忆中景物,面前是一片葱茏树木,掩映着几座白色小楼。墙上有个小门,但锁着。不过墙不高,很容易就攀了进去。寻觅良久,才发现一排带雨廊的平房还在,其余统统了无痕迹。当年我们蜗居的杉皮屋自然是早就拆除了,可是一开始住的那间砖瓦房呢?以我当时的微贱,能住上那样的房子,曾经大出奢望……它不会拆掉吧。它的大致位置我还记得,墙里是没有了,或许在外边。我们三人又攀出墙去。因此处院深墙高,颇费劲。邓女士跟着受累,到了外面,她还有点气喘嘘嘘的,用白话问李君:“干什么要这么费事?这人那时来这里做什么?”李君只极简单地回答道:“落队唠!”
落队,直译是“下队”,“信达雅”一些呢,可以是: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流落、落难……这落字很有表现力。
按方位,我终于找到了那间房子,可是已经破落得不成样子了,但还有人住。我绕到房后,核对它的特征--记得后部原来是突出小半间的,是个冲凉房,现在怎么没有了?或许是我记错了。就算是吧,现在能找到的聊以寄托回忆的也只有它了。
那年,夏天我刚结婚,妻知道我处境艰难心境苦闷,从遥远的北方来与我聚首,起初我们就住在这间当时还算不错的房子里。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也就是一个星期吧,便撵着不准住了。当我接到通知顿时愁苦交加,一筹莫展,这可到那里去住呢!与我同在一个钻机“落队”充当班长的老刘忿忿地说,“真他妈缺德。再怎么也得给间放张床的篷子吧!”要是连个篷子也没有,只有让妻回数千里之外的故乡去了。他说,“这事你先保持沉默,我去找他们。”第二天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没办好。争了很久,只答应让住牛圈边上的那个杉皮屋。没办法,就这年头。先凑合着住吧,我看咱们在这里也长不了。”
那是一排用杉皮搭成的真正的牛棚,一端是饲养员的住处,旁边还空着半间,就是我们的新居。其小其窄其矮连张单人床都进不去,还是老刘有办法,指挥着我合力把床举起来,从杉皮隔板上方空档慢慢挪进去。
单人床旁边加上一快木板,已占据了屋宽的三分之二,其余的可用面积仅容俩人并立。好在全部的家当只有蚊帐一袭、粗木箱一个而已。整排牛舍上方毫无遮拦地贯通一气,牛粪味弥漫过来,牛们也不时的哞哞地叫……这就是我的家!
然而总算有个蛰居的窝。在山野里风雨泥泞之后,在钻机的铁硬、油污、泥水中劳累之后,可以有几尺空间让身心歇一歇缓一缓,尚可躲避一下某些红人们的冷眼白眼;还有贤妻的照拂,又买了个小铝锅,常能吃到热饭菜,有时自己也煮一点较为可口的东西……聊以抚慰吧。毕竟才二十多岁,总还得活下去。
我在那老屋前留了个影,离开它走到下面的空地又拍了几张照片;李君没有留影,一张也不照,见我默默无语,他说,“不堪回首是吧。”
“恍若隔世。”我说。
回城的路上,他问我还要不要去望埠看看?若去可安排在明天。
去那里做什么呢?“班长”老刘他们已经离散,地质大队的旧址大概还在,在又如何?触景生情去重温当年“清队”折磨人的程序式场景吗--常常是夜半一、两点钟高音喇叭骤然响起,通知紧急集合。被惊吓而醒的人们揣着惶惶不安的心--又要揪斗谁了?--影影憧憧地站好队,走进礼堂。礼堂门口一边守着一个人,都横持冲锋枪。坐下后依然恐慌,特别是那些标牌不红的人们。先是革委会的上台慷慨激昂地讲话,一通“形势严峻”“人还在,心不死”“就在我们身边”之类,待把你的悬悬之心提到嗓子眼的时候,台下有人领喊起革命口号来,大家只能都跟着喊。口号喊过之后,接着是一声断喝:“把××份子(黑手、派……)×××揪上台来!”根本预想不到从哪个地方就会有谁被预先布置好两个壮汉一左一右反剪双臂摁着头押上台去,此时一条横幅标语随即通台展开,上书:把××份子(黑手、派……)×××批倒批臭!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批判者揭发者上台表演……
并不是所有熟悉的地方都适合重游的。
“不去了。”我答道。
“不去也罢。”李君很理解人。
晚上,我们到宾馆的歌舞厅去。有人唱歌有人起舞,都不大熟练,谈不到什么层次水平,但大多又挺认真。我坐在僻静的一隅,要了杯英德红茶--到底是产地,很正宗,甘醇微涩。恍若隔世的感觉又涌上来,一时间想起雪莱的一句话:除了变,一切都不能长久;还想起未读过内容却记住了书名的一本书,那书名是:保持信心。
〔寄自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