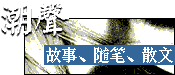大约是四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在这座城市里开了一家画廊,是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梧桐树枝叶繁茂,总令我想到朋友蓄起的“披头士”长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形形式式的艺术流派瓜分了绘画,画家或者说是艺术家在绘画形式中消耗才华,如演员一样表现自己,打扮得标新立异,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刺激。朋友画廊巨大的店招,黑底上蓝色、白色的中、英文呈现一种不安的气氛。租下这个店面的时候,朋友拆掉原来的门面,改装成整块大玻璃,店堂里放上沙发、茶几,四壁错落有致挂满了油画和水彩画,从街上望进去,犹如一家艺术情调浓厚的酒吧。我时常逛到画廊去坐坐,尽管从没有买回一幅画,但也是画廊的老主顾了。
画廊里其实只有一些美术学院学生的作品,镶嵌在简洁但略显单薄的木质浅黑色画框里。还有许多就是装饰性的风景画了。这个城市很少有外国人来寻找东方的艺术,一幅标价奇高的绘画是不会有人问津的。朋友赚钱的主要来源是承接室内设计、装饰,画廊似乎只是一个显示水准的标志。在这个绘画热衷于进入拍卖行的时代,金钱把绘画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就像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时时刻刻都在互相伤害。绘画收藏越来越成为一种投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名作的绘画不断被追逐者抬高价格,到了吓人的地步。据说莫奈的一幅圣母像,价格从1978年的25.3万英镑,跃升到10年后的671万英镑(1275万美元),现在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而另一面,在大多数人的客厅里,充塞着拙劣的风景画,甚至是无法从画面上找出一点匠心的东西,与裱糊在墙壁上的墙纸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书画的表现更让人泄气,书画家们到处奔波不是为了写生,而是现场为人写字作画,创作一幅美术作品已经同唱一首歌差不多,惟一的作用是每次都可以从附庸风雅者那里收到大量的金钱。真正的绘画爱好者,只有从大量出版的印刷品中去欣赏,绘画也变成了书籍形式的作品。画家究竟应该表现些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绘画还有什么样作用?这已经是一个被遗忘的问题。
至于我是这样来看待绘画的:一幅画如同一部小说和一首诗,在其中存在着一个灵魂,所表现的应该是画家的日常生活。一幅成功的绘画,除了装饰性的作用和视觉效果之外,还应该具备的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此,才会给观赏者带来艺术的感染,对画家本人无论是作品完成之后还是创作的过程中,绘画应该是自我满足的安慰。绘画就是日常生活的插图,表现手法又能算得了什么,那不就是光线、色彩、线条的不同组合吗?也许在这样做的时候,画家虽然摆脱了在潮流中疲于奔波的的宿命,但是又会进入一个孤独的世界,还是逃不脱悲惨的结果。当然这对功成名就的画家来说已经是不成问题了,对一些无名的画家却是性命攸关的事,肉体的生存虽然形而下之,却也不可避免要让画家撞得头破血流。绘画史上,大多数画家从未得到过作品拍卖成功的巨大物质利益,相反是在贫困中早早结束了生命,空留下种种遗憾。
1901年9月9日清晨,在巴黎近郊的努伊依医院,一个显示高度酒精中毒症状,下身畸形的病人躺在病榻上,他已经永远地关闭了眼睛。这是年仅三十七岁的法国绘画奇才劳特累克,临终守在他身边的,是他泪流满面的母亲。三十七岁对于画家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拉斐尔、凡·高、莫迪里阿尼都夭折于这个年龄。也许劳特累克比凡高幸运一些,他在闭上眼睛之前,得知自己的绘画收进了卡蒙德藏品馆和罗浮宫,使他的灵魂能够带着荣耀离开人世。
劳特累克短暂的一生是悲惨的,他少年时代遭遇了两次不幸。1878年5月14岁的时候,他从床上掉下,左脚骨折。翌年,在疗养区散步时又不慎跌入干枯的河床,右腿又骨折,长期的治疗休养都无济于事,最后腰以下的发育完全停止。有人认为,这些不幸事故的发生虽然似乎都是纯属偶然,但祖辈世代的近亲婚姻,或许是其体质不正常的真正原因。因为行动不便,幼年就对绘画兴趣浓厚的劳特累克,更加专心于绘画。在巴黎的画室里,他结识了贝尔纳和凡·高,通过凡尔纳他又了解了高更和德加。劳特累克尝试了自印象主义以来的各种流行的绘画风格和方法,从中吸取刺激和影响,但他本质上是一个直观的画家,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和手。劳特累克绘画的辉煌时期是他在巴黎蒙马特尔居住的那段日子。当时的蒙马特尔是新兴的娱乐区,夜总会、咖啡馆、酒吧里到处是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劳特累克的夜晚就在那里度过。有名的“红磨坊”夜总会,劳特累克是其中的常客,他的情人是出钱购买的妓女,他就在那里画了大量的写生。劳特累克的绘画大都以娱乐场所的绅士、太太们和舞女、妓女为题材,以荒谬的色彩、夸张的光线、丑化的线条来表现上流社会的日常夜生活。他对任人玩弄的舞女、妓女既抱有同情心,同时又充满了嘲讽的笔调。有人把他归类于印象主义的绘画,其实他并不重视绘画对象的光线,可以说劳特累克与印像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自己曾借用高更的话说:“想到有学派吗?有什么用?要使每个人像他的邻居一样走同一条路吗?”
欧美近代绘画的一个方向,就是从宗教性的重大题材转入对日常生活的描绘,绘画成为画家生活的一部分。画家本身也通过自画像或其作品中的场景出现在绘画中。而绘画史理论粗暴的分类,常常使我们不能正确理解一个画家。对绘画的阅读首先被引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派、野兽派、抽象派等等既定的框框里,阅读绘画的过程成了对画家和绘画进行分类的过程。
劳特累克正是这样一位以劳特累克方式带上我们进入日常生活的画家,他的一幅著名绘画《在红磨坊》,是这样的场景,酒吧柜台外有几个绅士和贵妇模样的人坐在一张小桌前;远处有妇女在对镜梳妆。“红磨坊”的常客和画家的几位朋友散处于四周,让他写生作画。而画家本人与他的表兄塔比埃,就坐在处于画的中景的座位上。我们看到的是虚掷光阴、借酒浇愁、没有真正快乐的夜生活,是一些冷漠、傲慢和疲惫的人物。色彩、线条和画中最为特出的夸张逆光,对于我们实在没有多少关系,重要的是阅读这幅画的感觉,是不是能得到一些全新的体验,再进一步也许我们还可以看到画家经历了一些什么。这就是劳特累克世界的插图。
劳特累克尽管非常仰慕德加,也和德加一样,热衷于把剧院、马戏团、音乐厅、酒吧等娱乐场所作为绘画对象,但是他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对象的光线上,不仅仅是一些造型的美感。劳特累克绘画中有的是对醉生梦死的揭示,是对日常生活的同情和嘲讽,是他的人生观的写照。德加当然是一位近代绘画大师,而正是从这里,劳特累克与德加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劳特累克所具备的,刚好是德加缺少的。在读过劳特累克之后,再去读德加,就会感到德加未免是一个把光和色玩得过于成熟的技术大家了。绘画《在红磨坊》的右边,一个盛装妇人的近景,夸张的光线自下而上照在她脸部,让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奇特。劳特累克使司空见惯的场景重新现出其本质,使日常生活引人注目地显示在眼前,就像一本书中的一幅幅插图。无怪乎连妓院的老鸨也要请他为妓院里的16位姑娘画圆形框肖像,悬挂在磨坊街新开设的妓院客厅里。
当然,通常的观点认为,现代绘画是从保罗·塞尚开始的,以致有了“塞尚以前”、“塞尚以后”的说法。塞尚以前的绘画,从根本上说是模仿自然或再现自然的艺术,讲究作品再现自然的逼真程度,强调“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而塞尚的出现改变了这个传统,他认为画家应该面对自然的直接感受,经过重新安排,创造出第二个自然。在塞尚看来,绘画毫无社会功利可言,只是光、形、色和空间在平面上的构成,是“为构成而构成”的。他琢磨研究最多的是静物,探索从不同的视点,用色彩的冷暖对比来表现物体的立体感,在四十多年的绘画生涯中,他画了三十多幅自画像。他的代表作品《厨房中的餐桌》,就已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点,带网的水罐口和餐桌是从上到下俯视,水壶和篮子以及水果是从侧面观看,篮子看上去像浮在空中。塞尚直接导致了毕加索等人的立体派的产生,特别是打碎了焦点透视,使毕加索从焦点透视中解脱出来。由塞尚所带来的问题是,从此在绘画中过多地强调了形式的探索,脱离了内容的形式至今仍成为绘画中致命的流弊。塞尚是纯技术性的画家。其实,塞尚也主张把个人的主观意念在画面上表现出来,画出“我心灵的作品”。
萨尔瓦多·达利可以说是一个怪才,他说过:“什么是超现实主义,我就是”。达利的作品,完全是妄想的超现实景象,他著名的作品是《记忆的永恒》,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画成像面一样柔软的物体,一个叠挂在树枝上;一个呈九十度直角耷拉在方台的边沿,好像马上要溶化掉似的;另一个横卧在像长着婴儿脸的奇妙生物上。在荒凉的海湾背景衬托下,像是一个时间绝对停止的世界。达利热衷于描绘梦境和妄想,以似是而非的客观真实记录最主观的奇想和潜意识中的幻觉。1950年,达利画过一幅《利加港的圣母》,他用完美的古典主义写实的手法来描绘无理性的情节。圣母和圣婴的刻画有着近乎照相的写实,可是他们的胸部都开了一个圣柜型的洞穴,在大洞之中的小洞正中浮着一个圣餐面包,面包正处于画面四角对应线的中心点。圣母身后的门洞分裂为几个写实的立方体,毫无依托地飘浮在空中,身后的背景则是达利家乡利加特港的风景。就是这幅画,达利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圣婴是以卡达克斯渔夫的孩子为模特儿,圣母是以他的妻子加拉的形象为原形。在另一幅作品《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里,圣母也仍然是照加拉的写生来描绘,而画中将十字架紧紧抱在头上的人,则是达利本人。在达利的绘画生涯中,画妻子加拉是他最偏爱的主题之一。
达利的意义,是通过有意识的方式来表达梦境和妄想,把超现实主义绘画从脱离现实的歧途中拉回到现实世界中。达利的超现实,是一种重新组合的现实,是一种张狂的现实。达利本身是一个倾向于奇异化的人,在学生时代,他身穿一套异国情调的斗篷大袍,因为煽动学生运动而被抓进监狱,后来又由西班牙国王亲自署名开除学籍,以至他父亲也对他大感失望。他的性格里含有妄想症特征。妄想症作为一种偏执性的慢性精神病,表现在幻觉或无幻觉的自大和受迫害妄想。妄想症患者与达利之间的区别是,前者是真的有病,而后者往往是装病。达利自己说:“我与疯子的惟一区别,在于我不是疯子。”他在自传性的文字作品《达利的秘密生活》中说:“我斗争--反对比剽窃更坏的单纯,拥护复杂;反对单调,拥护多样性;反对平等,拥护等级制;反对集体主义精神,拥护个性因素;反对政治,拥护形而上学;反对音乐,拥护建筑;反对自然,拥护艺术;反对进步,拥护永恒;反对机械,拥护幻想;反对抽象,拥护明晰;反对青春,拥护成熟;反对约束,拥护不受约束的狂热;反对菠菜,拥护带壳的蜗牛;反对电影,拥护戏剧;反对佛陀,拥护德萨特侯爵;反对东方,拥护西方;反对太阳,拥护月亮;反对革命,拥护传统;反对伦勃朗,拥护拉斐尔;反对原始偶像,拥护世纪初的精美器具;反对非洲艺术,拥护文艺复兴的艺术;反对哲学,拥护宗教;反对医学,拥护巫术;反对高山,拥护平缓的海岸;反对幻觉,拥护幽灵;反对女人,拥护加拉;反对男人,拥护自己;反对时间,拥护消逝的时光;反对怀疑,拥护信仰。可是,我同谁斗争呢?我的敌人是谁呢?是除了加拉之外的一切人,或者几乎一切人。”这些错综复杂的口号,正好是达利的个性发出的喊叫声。
在达利的另一幅绘画《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里,我们看到的并非是西班牙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哥伦布驾率三艘木帆船,冒着惊涛骇浪,历经七十天抵达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史实,仅仅是达利借用的一个形式,我们所看到的是达利的冒险精神,或者可以看做是达利对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逃避,是日常生活中达利的写照。甚至在他的宗教绘画《最后的晚餐》中,也把耶稣和十二个使徒置于一个现代状态之中,画面的背景可以看到利加特港湾的海面和小船。达利的《内乱的预感》如同充满血腥的噩梦,湛蓝的天空布满乌云,茫茫大地上残破的肢体伸向天地,痛苦的面孔似乎在挣扎、嚎叫,山河破碎,惨不忍睹。人们把它看做同毕加索的作品一样,是对西班牙内战的谴责、抵抗、呐喊。达利对这幅画的预言性作用,很是感到得意。他说:“内乱的预感老是缠绕着,激发我创作的欲望。在西班牙内战前六个月我便画了《内乱的预感》,在撒满熟扁豆的地上,竖起一具很大的人体,其手、脚、腕、脖相互交错。在战争爆发六个月前就给它起名为《内乱的预感》,这完全是达利的预言。”达利是一个颠覆了超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
凡·高可以说是一个比达利更疯狂的画家,狂热地执著于自己的表现形式,以绚烂的色彩、奔放的笔触表达狂热的感情。欧文·斯通把他那本著名的凡·高传记,称为《渴望生命》,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凡·高的性格。1901年,在巴黎伯恩海德姆画廊里首次举办凡·高绘画展,一位维也纳诗人豪夫曼斯达尔在看了画展之后,写过一段对凡·高的评论,“这几天,我心情不佳……偶然走进僻静小巷的画廊,看了一位画家的作品展。我在那些为命运撕裂的风景、静物、食土豆的几个农夫的画面前,不禁愕然……我不得不承认奇迹般地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树木,黄色与绿色的地面,残破石块铺的山丘小路,锡水壶,陶瓷盆,桌子和粗糙的椅子,各自都有了新的生命。那是从没有生命的恐怖的混沌中,从无底的深渊中,向我投射的生命之光。我是感觉到的,而不是领悟到!这些被造物是由对世界绝望而极其恐惧的怀疑中诞生出来的。它们的存在,将永远地穿破虚无、丑恶的裂缝。我确实感觉到作者为了摆脱恐怖、怀疑和死的痉挛,以这种绘画来回答自己那种人的灵魂。”凡·高自己也说过:“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为了它,我甘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
凡·高的终点是法国阿尔,在小镇北部拉马丁广场边上的一所房子,凡·高画过一幅画《拉马丁广场上的“黄房子”》,他把它视为“撤退的地方”。在这里凡·高画了大量的风景画和人物肖像。初到巴黎时,凡·高曾画过大量的静物,其中有一幅是《一双鞋》,那是一双破损不堪的旧鞋。这双鞋似乎是在向我们诉说它的贫困、不幸和毫无尽头的旅途劳累,直至完全磨破为止。这双鞋紧紧靠在一起,如同兄弟一般,暗示着凡·高和弟弟的情义。人们可能认为凡·高的《向日葵》是他刻意找到的象征物,其实向日葵在凡·高的阿尔是普通、平常的植物,对凡·高来说向日葵是情人节玫瑰一样的东西。那幅割掉耳朵之后的《自画像》是一个真实的凡·高,在与世俗的殊死搏斗中,他拿起一把手枪,先是瞄准朋友高更,随后就走到一片麦田里对准了自己。人们一般这样认为,凡·高一生画了二千幅作品,却只卖出一幅,而一向支持他的弟弟已经结婚生子,经济拮据,凡·高不想再给弟弟增添麻烦,所以才结束了自己不幸的一生。他最后的遗言是:“痛苦便是人生。”凡·高对死的选择,是不是一种理智呢?现在,凡·高本身也已成为一个象征物,1987年在伦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他所画的向日葵以3990万美金的高价售出。回过头来看,凡·高确实是画完了他应该画出的一切,我不能想像再给凡·高一些时间,他能画出些什么,那就不会是凡·高了。我们拿过凡·高的画册阅读,可以见到凡·高各个阶段的生活,所以在凡·高的传记里,他的绘画是最好的插图。这也是做一个画家的好处,倘若是作家,那就必须有一大堆照片来做插图了,或者也得请其他的画家来根据作家的照片通过想像绘制插图。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画家,是著名的乡巴佬--美国当代著名画家安德鲁·魏斯,他一生都住在乡村,从没有去过外国,也很少到外地旅行。魏斯的故乡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外的查兹弗德村。70年代时,这个村仅有140口人。夏天,魏斯则到缅因州濒临大西洋的库辛村避暑,这个村当时也只有25口人。魏斯的许多知名的风景画和人物画都取材于这两个小地方。魏斯在这里“开垦着自己的宇宙”,他把许多日常习见的人物、事件、场景自觉地在自己内心升华,然后创作出作品。有人讥讽他是“摩登的原始人”,有人劝他到外国去旅行,开阔视野,增广见闻。对此,他总是答复:“我连身边的宝藏都还没有尽心探测,为什么不应该在一个地方长住,以便发掘得更深一些呢?”。读魏斯的作品,首先抓住你的是伤感、孤独和深沉体验的抒情性,通过墙壁的罅隙、剥落的壁纸、破旧的衣服、被弃的破马车等等,引动人们对往事的感怀,对亲人的追忆,触发“生之须臾”、“岁月不驻”、“田园将芜”之类的兴叹。魏斯的技巧是,对构图和人物动作的选择,都很特别,使人觉得既真实又奇特。魏斯自己称之为“思考性绘画”。
魏斯为人称道的绘画《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是一个穿粉红色衣裙的女人倒在枯草连绵的斜坡上,远处是一座小村落,隐隐传来无声的神秘呼唤,这正是魏斯从乡村生活中体验到的呼唤,也是他生命里的声音。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在我看到的为数不多的魏斯的照片中,照片上的魏斯与他背后的景物与他绘画中的人物、风景在气氛上竟是完全一致。在佩服摄影师的深刻理解之后,我也怀疑这些照片的作者就是魏斯本人,不然也是来源于魏斯自己的构思。1946年魏斯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插图画家)在一场车祸中死去,稍后魏斯又生了一次重病,这一重大变故使魏斯对生命的价值又有了深刻的理解。《1946年冬天》这幅画很简单,就是一个从山坡上直奔下来的青年,但却把魏斯的失措和彷徨表现得极其入神,既传达出一种紧张不安的戏剧效果,又有点冷漠、孤寂,暗示了生活的冲突,宿命的感觉特别引人注意。魏斯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普通的画家,大部分作品只是虚有其表。”因为普通,魏斯始终置身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之中,得以从高度写实的作品中抽象出一般人难于达到的精神。
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并非没有一些值得记录的场景,发现需要敏锐的眼光。一位小说家就这样认为:每个人只要活了几十年,都会留下自己的记忆印象,差别只是多数人都是乱七八糟地放在心灵抽屉里,若请他们把属于自己的记忆印象整理出来,他们可能会觉得不知如何着手。但是,只要经过训练,通常多数人都能够把自己脑中的印象整理得很好。一部小说只是把自己内心的抽屉一个一个打开,把那些应该整理的整理好,又把那些能够让大家引起共鸣的东西用文字表现出来,呈现给大家而已。而绘画的不同,也只是以色彩、线条、光线来表现一门艺术。我的另一位画家朋友,就是一个敢于这样来进行实践的艺术家,他的家乡在八百里太湖的南岸边,至今仍然经常去那里写生,积累绘画的素材。他也擅长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人生的感慨,尽管他现在还不为人知,却是我内心敬佩的画家。他的许多油画都是湖畔的风景,是芦苇、船只、桅杆之类。试图在他的绘画里找到某种艺术主张、重大题材之类,难免要令人失望。我们经常要见见面,聊天是我们交往的主要内容。坐在他杂乱无章的画室兼书房里,周围是油画、素描,堆到天花板上的书籍,我们一聊就是半夜。有一回突然停电,他翻箱倒柜,不知从哪找出一支红蜡烛点亮,随手插在一个玻璃烟缸里放到一叠书上,这一幕情景使我留下一个难得的印象。过一段时间,我再去的时候,竟然就看到了一幅油画,只见黑暗中一支红烛在燃烧,周围是一本又一本随意堆放的书,背景是一把大提琴。我不禁想起了闻一多的著名诗篇《红烛》,几乎比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鹏的《红烛颂》还要自然、传神,更接近闻一多的诗歌。相比之下,闻立鹏的《红烛颂》显得过于直露,重点是在表现闻一多的政治思想了。
魏斯还曾经这样说过:“我的作品与我生活的乡土深深结合在一起。但是我并非描绘这些风景,而是通过客观存在来表现我心灵深处的记忆和感情。”读他的《遥远的地方》,一个男孩独自坐在枯草丛中,我简直要以为那个男孩就是我,但是又说不出为什么要坐在那里,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事情是不可能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故所以才会有绘画艺术。还有一幅《下雪》,画的是一个男人站在窗前,凝望着窗外沉思,那神态总使我觉得这是一个诗人,一首关于下雪的诗歌正在诞生。而且,魏斯的艺术世界确实让我想到了一位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内,他的诗像素描一样朴实平易,对生活细节写得具体、准确,忠实于“事物的纹理”。希内的诗歌也是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出来的惊喜,他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重大题材,也没有把太多的社会责任、时代见证、民族良心等等堆到自己身上。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希内也没有忘记时代和民族,但是这样来补充说明一个诗人的全面性,其实完全是多余的。对于一个阅读者,我要说的是一种阅读的方式,在这里我可以声称,把魏斯的绘画与希内的诗歌放在一起读,那是很少会碰到的奇迹。读魏斯的画,似乎是在读一首希内还没有诉诸文字的诗歌;读希内的诗歌,常常会觉得魏斯正在画这幅画。类似的艺术家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勃莱的诗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个人生活的抚慰,显得清新而亲切。勃莱的道德力量,使我们从喧嚣中平静下来。在他流畅的诗中,柔和的“深度意象”是一种个人性的生存体验。就连他的《反对富人之歌》也排除了口号、嚎叫,“我活着,天天都有汪洋般的光明/升起,我仿佛看见/石头噙着泪水,好像我的眼睛在地下面凝视”。我们从勃莱的诗中可以领悟到日常生活中飞翔的快乐,“一天早晨我觉得会长生不老,我裹在兴高采烈的肉体中,好比小草裹着一团团青绿”,勃莱把握了一个世界。
也许可以说,这些画家和诗人,是从现实中逃离到内心的艺术家,就连达利也不过是换了一种逃避的方式而已。一些重大的现实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当然也会出现、存在,也会在一个时期鼓舞我们。但是,我要说的是,抛开了日常生活,从理念和形式出发的艺术,是艺术的灾难,是危险的倾向。在我阅读的经验中,很少对这样的作品引起过足够的兴趣。我既不会拿那样的绘画挂在日常生活的场所,也不会反复去翻阅。远离日常生活的绘画,同样也使我感到离生活十分遥远。在我们周围,还有一些可笑的书画家,终其一生都在画固定某种程式之中的绘画,花鸟山水之类,看过一幅再不用看第二幅。更有甚者,一个画家竟可以不了解动物,却一生都在画老虎,人们也居然会称他为著名的画虎大师。遇到这种情况,我宁愿去读一些生命气息浓郁,富有创意的广告画了。美国曾经有一位真正的插图画家诺尔曼·罗克威尔,他的作品大多是一些杂志封面画和书籍插图,他极端写实的绘画,从不打算在某个场面中去揭示什么,只是质朴地把日常可见的生活凝炼地加于展现。罗克威尔作为一个通俗画家,果然没有在传统的美术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却广泛地为人们所知,深入普通人的内心。一个人翻阅最多的应该是他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影集,因为那是他们逝去时光所留下的一幅幅插图。能够画出类似于插图的绘画,或者是读到这样的绘画,无疑是极大的乐趣,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寄自浙江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