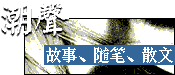新西兰诗人艾黎曾说过,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一个是福建的长汀,另一个是湖南的凤凰。凤凰,正如它动人的名字,是一个生产传奇和歌谣的地方。那里,白塔、流水、吊脚楼在风中展开,俚语、与朝霞同升的山歌在叙说着新鲜而古老的故事。当我每次走在返家的路上,我无不是在走向凤凰,如鸟返巢,如兽归于林。虽然凤凰的人情风物让我牵挂,但真正浸染我心灵的还是那片土地所孕育出的精神。因为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拐弯处,我遭遇到了一颗颗从窄巷中走出却拥有与世界一样宽广的心灵,其中这里面有从一脉清波吸取灵思的作家沈从文,有依据凤凰山水泼墨人生的画家黄永玉,在某些特定的日子,他们如水一般,喂养着我的灵魂。
春节放假,我整整坐了两天两夜火车,从福州赶回家去参加妹妹的婚礼。年初二,湘西本地风俗是拜丈母娘的日子,我既无未婚妻,也无丈母娘,便向父母提出到凤凰城走一趟。父亲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冒(娃),凤凰城个(那)地方有么子看头,石头街木头房,咱乡下到处都是。”而母亲只是用一双柔和的眼睛打量着我,仿佛在说:“冒,你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回,就不能多陪陪阿爸阿妈?”然而母亲是知道我的犟脾气的,从小到大很少有拦倒我的事。母亲只好强作高兴的样子说:“快去快回,赶回来吃夜饭啊”。当我爬上一辆四面敞开的大货车,被一群挑着一箩箩红猪腿白猪腿去远方拜丈母娘的小伙子围挤在一端时,耳朵一边听着年轻的女婿们说些粗野的笑话,脑子里在不断回旋出门时父亲对母亲所发的牢骚:“冒,每回回屋都要行凤凰城,好像凤凰才是冒的窝。”是啊!父亲说得对。每次返回故里,我每次都在向离家五十里外的凤凰城靠近,与其说我在走近凤凰,不如说是心儿要去它离开已久的地方。
车至凤凰后,脚踏上青黝的石板路,我就像一条长时间搁置在沙滩上的鱼,突然间回到了流水中。闭上眼,我也能在曲曲折折的窄巷中自若地穿行。我知道哪条巷子的尽头有一位身着对襟衣的老嬷嬷,摆着个直让人流口水的酸萝卜摊子;知道哪排吊脚楼的门槛边或蹲或坐一个个抽旱烟的老爹。走动在滚瓜烂熟的风景中,我快乐得简直就像一个孩子。一会儿登上斑驳的古城门去俯瞰远近错落有致的吊脚楼;一会儿溜到河边提心吊胆地去跨越竖立在激流中的跳岩;一会儿赤脚踩在冰凉的青石板上,趁着无人一个人偷偷地高唱湘西山地随处可拾的情歌:“阿妹好比高山清凉水,救活几多年轻人。”偶尔从远处某座吊脚楼上传来一位阿妹回应的歌声,那颤悠悠的声音,勾起我长时间的痴想……
拐入城南一个叫中营里的小巷,往里走几步,抬头一看,我又来到了沈从文的故居。这是一座典型的湘西四合院,温馨而古朴,院子正中有一小天井,用红岩方石板铺成,天井四周为古色古香的屋室,右边的房间悬挂着沈从文生平的照片和摆放着从文的书稿手迹,左边厢房则陈列各种版本的从文著作。在所有记念沈老的物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女士的撰联,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我想,这不仅是对沈老坎坷一生的公正评价,它同样适合于百年以来为理想献身的中国知识分子。每回访从文故居,我都会忍不住买一叠书籍回去,有些是沈老的作品,有些是介绍凤凰风俗民情的小册子。这次故居之行,当然也不例外,当我从一位慈爱得就像阿妈的管理员手中接过沈老的作品集时,不料她不经意地问了我一句:“后生崽,你也尊沈老?”当时,我多么想告诉她,我这个后生辈不仅敬重沈老的为人,更多时候我把先生当作一个知己,一个灵魂深处相通的朋友。因为我从先生的作品中懂得什么是爱、怜悯与同情,从先生诚实的自传中读到了:“一个人只有向远方走去,才会有希望。”
从故居出来,也许是受刚才管理员问话的影响,我突然决定去沈老的墓地看看。虽然我从未去过先生的灵地,但在淳朴的湘西,一个异地人永远不会迷路,因为当地热情好客的苗民是最好的路标。在路上,偶然碰上一个中年苗人,他陪我走了三四里山路,一直把我送到沈老的墓地,才放心地走了回去。目睹先生的安息地,其简易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与鲁迅并驾齐驱的作家,墓地竟是如此地简朴,墓碑采自湘西山地随处可见的天然五彩石,墓志铭是先生晚年经常思考的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倒是先生豪放仗义的表侄黄永玉,在墓地入口处为先生立的五尺高碑,给墓地添色不少。高碑上镌刻着黄永玉对表叔一生透彻的理解:“一个士兵不是战死在沙场,便是回到故乡。”黄永玉还真没有辜负表叔对他曾有过的教诲,他这番话触及到了先生骨子里头的根。回想先生一十五岁就走出凤凰,在沅水流域各地漂泊,十九岁只身闯入北京,凭着一股横竖要活下去的蛮劲,经过千锤百炼终于成了一代名家。沈从文、黄永玉的成功事迹,至今都在激励着湘西人,它将永远告诫年青后辈:通过奋斗,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回到家时,夜已深。一直等我的母亲拧亮了灯,并悄悄地告诉我妹妹的婚礼推迟到年初六。我明知道母亲的期待,但我还是残酷地告诉了母亲,无论如何我得初四动身回福州。在妹妹上花轿、母亲唱着哀婉的哭嫁歌之日,我由一列火车把我带往灿烂的南方,正如沈从文当年走出湘西那样,进入了一所永远无法毕业的学校,去学习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1999.5.1,草于福州)■〔寄自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