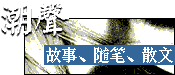小 家 国
一滴水可以映现大海,一粒沙是一个世界,一个小家庭呢?
◆民族问题
我是个满汉混血儿。母亲那一族是满洲旗人,父系则是从浙江(好像是嘉兴一带)迁居到河北的。在我出生的时候,姥姥给我去报户口,就填了满族。后来我爸爸不同意,说只有四分之一满族血统了(因我姥姥嫁了汉人,妈妈那一辈就不纯了),就应该是汉族了,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汉族,失去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待遇和作为少数民族的自豪感。在北京,当少数民族滋润得很哪,没有任何民族和宗教迫害不说,在凭票供应的年代可以多得油啊副食啊,馋得邻居家孩子涎水滴滴,高考分数能优惠好几十(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一分定终身哦!),别的方面还会有照顾。就凭这,可以对任何汉人实行反向歧视。
我小时候中了帝国主义权力话语的毒,真的以为“民族”是很神圣的,民族的边界是不可逾越的,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语言、民俗、传统、艺术风格、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是说,那个“文明”和“文化”都是完全不同的,非常独特的。后来才看到新的权力话语说民族只是个“想象的共同体”,才从理论上知道中国人被蒙了。在解放后,中国人根据那套鬼话创造了一堆民族出来,给它们找历史,定服装,甚至造文字,满足了博物馆野人展览的所有标准,最后栽培了56朵花。每年,中央民族学院都要办至少一场全体出席的花展,规定要有56种服装在争芳斗艳,人家老师都烦死了。
我的姥姥爱唱旧戏,对于《四郎探母》之类的是百唱不厌。她一口一个“番邦”,自己当然是昭代箫韶的杨家将,还会给我讲“正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她很瞧不起蒙古人,说他们就是过去的匈奴,鞑子,朱元璋杀的就是他们。我上小学时常笑她,说你不就是鞑子么?你看戏台上的鞑子穿的都是旗装,花盆底。这时候姥姥就大怒,骂我是南蛮子。那时候我有点困惑,我的姥姥既是异族人,怎么那么有正统的思想,而且自己一点都不见外呢?后来我才明白,人之归类划界,乃在于他接受了什么样的文化,不是看他出身什么血统,所谓“民族”之类的界限很多都是人胡编滥造的。蒙古人在元朝末年给打跑了,退居漠北,还老想反攻倒算,最不可原谅的是又分离出去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是铁了心不跟我们用一种语言,一个文化传统了,不是鞑子又是什么?满族则不然,满汉都混居了那么长的时间,早接受了孔夫子传下来的全套子本事,满族人汉话说得倍儿溜,满语倒是不会说了,如今流毒天下的京腔就是他们说惯了的老北京话的变种,在文化上早是一家子了。雍正皇帝曾经为着夷夏之辨痛心疾首,编出神话来说汉族和满族都是大禹的后代,怎么不是一家子呢?亲写宣传小册子《大义觉迷录》,勒令原反清义士巡回全国演讲。到了乾隆就更痛快了,他说咱们都学了孔夫子的礼数了,凭什么还打入另类呀?把那几个原教旨、制造分裂、挑拨民族关系的杀了,《大义觉迷录》禁毁。从此满汉就更透着亲近了。推翻清朝的统治,满族人还留在北京,也没受什么破家丧命的大迫害,还渐渐开始通婚,连血统也不见外了。中国人最心爱的传统之一就是大一统,这个传统,蒙古人背弃了,所以他们是养不熟的匈奴;满族人则是坚决的拥护者(溥仪不能代表广大的满族人民,尤其是老北京满族人),这是最能体现中国人风格的试金石,还有什么不是一家子的呢?
从小,我就开始怀疑书本上说的东东。姥姥给我上了最早的OOP课程 ( Object Oriented Processing ),教我抛开一切既定的条条,直接面对现实和人性本身,通情达理地去看世界。她是个文盲,不会说什么,这个身教使我终生受益。
◆异族通婚问题
在上山下乡如火如荼的时候,我老姨疯了似的要下乡。我妈要姥姥把户口本紧藏起来,决不要放她走,就担着心去外地演出了,家里只剩下姥姥和不懂事的三舅。最终三舅没顶住老姨天天闹,把户口本偷了出来,我老姨如获至宝,拿着就去街道销了户口,兴致勃勃地插队到内蒙古去了。她是个有才华又浪漫的姑娘,对大漠风光,风吹草低见牛羊迷恋得不行,是当时少见的自觉要去广阔天地炼红心的人。临行在北京站与另一位同学合了张影,摆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常青指路”的经典造型--那女同学在前面高扬手臂,她在后面踮起脚第一阿拉贝斯克,还是仰拍的英雄风格角度。从此这两个满脸幸福和淳朴笑容的姑娘就和北京站的大钟一起留在画面上了。那时她们是16岁。
到那里的第一年,她还很有兴致地给家寄了照片来,上面是她手执羊鞭笑指远近白云一样的羊群,题字云:“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直觉那羊鞭是套马竿,因为杆儿立起来比她高,鞭索还更长,但这么一大鞭子比较有气势,视觉效果好,角度线条质感都好,所以她就选用了。我老姨是很有艺术天赋的,那时候家里其实没什么条件教她,她也就是上了个女二中。
后来她爱上了当地的一位蒙古族小伙子,我姥姥拿牙根儿咬的“匈奴”。我的老姨夫从小是个苦孩子,后妈,逼他干所有的活儿,不给饱饭吃,大雪天出去捡粪烧火拦羊放马……小命儿日日悬在一线。他在县城里上了个高小还是什么,略识几个汉字,但家里供不上学费就休学了。后来他一直在各处做工,直到碰上我老姨。
以我老姨那么一种到现在奔知天命之年都不改的浪漫脾气,当然对这身世凄绝、志向不俗(怎么个不俗后面再表)的青年生出惊奇、同情、知己进而爱恋之情。她把他的身世和他们的恋爱过程写成长篇叙事诗,我有幸拜读过。他们都读了些书,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置换进去当了主人公,这也是集体无意识之“原型”吧!她象纡尊降贵的天女或公主,爱上人间善良而不幸的青年,以温暖和知遇抚慰了他那饱受创伤但还执著追求真理和幸福的心……后来老姨随知青大流回北京的时候,带回来两块手绢儿,一块上是文成公主,一块上是王昭君,这都是老姨夫当年送她的定情之物,也是他们之间感情的共识。但他们当初可能不会知道,这两位女性没有谁愿意嫁到那苦寒穷塞去,她们是政治的牺牲品,葬送了一生在孤独的人群中。更可恶的是后来还总被涂上金粉放在祭坛上烤,生前出卖其肉体,逝后侮辱其灵魂。如果她们能自由选择的话,一定要回到故乡的,就像我老姨一样。我老姨的命运和心境奇妙地叠化在这两位女性的身上,她们也成了我老姨生活遭遇的谶语。
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大的女孩叫斯琴高娃(聪明美丽),二小子叫额尔德尼(宝贝),三小子叫阿斯翁(老虎)。生大表妹的时候,姥姥带了5岁的我去伺候月子;生二表弟是到北京来生的,条件最好;到生三表弟时,我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爸妈工作都不在北京,居然就把我寄放到外地转学去了。我倒是入乡随俗,在那里与比我大3岁,高一头半,打遍附近小学无敌手、连中学生都敢打的大王决斗一小时,打个平手,顺利地扬名立万,学习又好,文体技艺为校争光,到现在老师还记得我念叨我呢。
我老姨夫多才多艺,车工、铣工、刨工、其他工都会;收音机、电视、汽车什么的都会修;各种乐器,无论弦乐、管乐、弹拨乐,拿到手里拨拉拨拉就弄出五音来,接着就成了调儿;做木工、铁匠、各种手工也是一把好手……我从未见过他那样心灵手巧的人。而且这些还都是他自己学的,没人教,因为他是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兰浩特旗的牧区生长的,只上了高小,受的教育太有限了。他对人极温和,虽然身高体壮,象高大的骆驼或骏马,壮得能推倒一头牛,但性情象羔羊一样良善,尤其对老人、妇女、儿童顶好,总是抛下自己的一切去帮助人。比如他后来招了工住的小县城临河,每年到春节会卖一屉到两屉点心渣儿,大家都排队去抢,他就会扛了猎枪去维持秩序,看电影时亦如此,自己却不买点心渣儿和看电影,人称“活雷锋”。同事出差了,他会去帮那家女人挑水干重活,并无半点非份之行。到现在,他仍是不能发达,就因为他虽有一身好手艺,但给厂子修着车呢,来朋友说电视坏了,他立马儿扔下工作就去帮朋友,闹得谁也不敢跟他合作。盖因他是遵守游牧时代的道德,不遵守工业时代的道德;只懂朋友,不懂客户。他挣了钱,朋友一来哭穷,哪怕那家伙以前骗过他多次,这次也明着是骗,他还是立刻把钱都拿出来给人去乱花,自己苦着,说还能再挣。
他自己苦着也罢了,但连老婆孩子也苦着就不妙了。我老姨怀孕七、八个月时,还得自己蹲地下拉风箱做饭,他能悠闲自得地在炕上吹口琴,从不帮忙一点家务。邻居同事乃至不相识者的大小事儿都管,就是不顾家,还没事没非狠打老婆打孩子,这是他蒙古男子汉的威风,他那大蒲扇手,唉……这使我那读了太多浪漫小说,惯于想象骑士来吻她的手、为她出生入死的老姨完全无法忍受。当他们初识时,一切还象传奇,后来就变成悲剧了,是《娜拉》还是《玛丽亚·玛格达莲娜》就甭管了,反正他们一直在闹离婚。文成公主和王昭君真正的命运显现出来了。
老姨开始闹的时候,条件完全象汉唐盛世那么严酷,关山阻隔,鱼雁拒通,知青政策(不许回城)、民族政策(不许离婚)都在那里,还有粮票儿油票儿副食定量,更恐怖的是户口,她又有孩子,真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我姥姥和妈妈只能在家里陪眼泪,大包小包吃喝拉撒的东西往那里捎,悄悄换了全国粮票托人带过去,使她实在过不下去时能跑回北京,就算是个黑人儿,我们家死扛到底养着罢。我姥姥经常戟指向虚空怒骂:“匈奴!野蛮!哪儿有这么欺负人的?”
后来拜政策活动之赐,知青可以回来了,但是她有民族婚姻,按我们绥靖怀远的政策,是根本不能回来的。我妈疼这个老妹妹,昧了良心去向老姨夫作说客,希望他能痛快离婚,这样老姨和三个孩子的户口就可以回北京了,然后我妈再帮他在北京郊县找户口和工作,慢慢一家子就能重图恢复了。我老姨夫是很尊敬这位大姨子的,流着泪答应了。后来我猜他那时知道这一去破镜难圆,但出于他宁被人骗也不愿意怀疑人、从不让龌龊的心计玷污自己的荣誉感,他放手了。
我的老姨终于挣得了比文成公主和王昭君更好的命运,乌头马角,绝塞生还,把老姨夫一个人留在了漫漫的大漠风沙之中。
后来当然他们没有复婚。老姨夫出于对失信的报复,坚决带走了两个表弟,但他们的户口还在北京。老姨夫又结了婚,生了个女孩,对老婆还是那么不经心,不顾家,我表弟们都听到过抱怨(他们住在后山姑姑家,免受可能的后妈气,这是老姨夫对孩子的爱的一种笨拙表露)。但他的儿子们还是不能忍受那里闭塞的、没有前途的生活,在成年后坚决回到了北京。父子们为此大打出手,我二表弟头破血流地争到了自由,在北京站稳脚跟后,又把弟弟接了过来。尔后几年音问稀少。
今年他突然来北京看孩子,还想看看老姨,被老姨坚决拒绝。老姨接受了他后妻的礼物并有所致送,因她对孩子还是挺不错的,但再不想见这个毁了她青春、梦想、骄傲以至绝望的人。我老姨后来再没有结婚。
◆教育问题
我老姨夫是我生平(到现在为止)所见最伟大的天才。他只上了那么几年学,自己学通了汉语,会蒙语,能看蒙文的《红楼梦》(他当时说是《红楼梦》,我想《红楼梦》哪会有这么薄呐?读了点文学史后,猜想那可能是《泣红亭》,被称为蒙语文学之《红楼梦》的),还会些英语!这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到北京来,给我的印象。他会画素描,有许多阴影结构,我上小学时学的都是平面线条上涂色儿,我好像还被要求当模特儿,但楼下小夥伴一喊就跑了,失去一幅可能涨价的杰作。
当时宿舍大院里堆了许多加气氢条板,是种建筑材料,我们小孩子看了就是跟石灰做的预制板似的,但质地上有许多小窟窿眼儿。那种板酥脆又成型,很适合雕刻,我老姨夫从第一天就看上了,摸了好些回来,开始刻花盆。他刻的花盆有六角型的,上面大下面小,底部有很好看的涡形流水托,六个面上都镂了花草,撇的兰轻透纤逸,我觉得有郑板桥风格,梅花呢我觉得象王冕的,若有藤萝就一定象徐渭。还有长方型的,但四个角都刻进涡线,就起了变化,方正中有了圆健秀美。还有圆型、四角、菱型的,不一而足。
花盆虽然小,但整体的造型却有讲究,盆口的形状只是一条,还有盆体高低,盆身倾斜的角度,盆壁厚薄,盆沿伸出去的多少、上挑还是下浑,盆底宽窄,刻狮子爪座还是金刚座……反正至少有盆沿、盆身、盆底座三大块的点线面,空间结构,还得考虑它们之间的搭配,还有画龙点睛的小细节。我见到过太多难看的工艺品,其体格搭配惨不忍睹,更别说什么细节的刻绘了。我老姨夫却有天生的审美情趣,无论他做个什么东西,总是那么美妙、妥帖,间架结构,经营位置,无不尽善尽美,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人的眼光到了上面,都会变得调柔和雅,开胸顺气。他给我姐姐做了个小木头箱子盛宝贝,我看就是个黄金分割的长宽高;给我妈崴个铁条的脸盆架子,看着那么长挑舒展又大方轻盈,其线条有若波提切利,人在上面洗脸是享受,脸盆给搁在上头也会满意。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常常想起他,这阿拉坦嘎鲁般的英雄,惊叹于他的天才,更对这天才成长的环境百般困惑。按照完美的教育理论,玉不琢不成器,我们有海量的理论和实践范式,有批处理人才的整套机制,有蒙台梭利、马卡连柯、皮亚杰、奥尔夫、柯达伊……无远弗届地普及了义务教育,但是成绩也就一般吧。而我的老姨夫从小是在苦寒的塞外,荒凉的沙漠,生活已是最低水平,正规艺术教育更完全绝缘。他没念过几天书,还因为家里穷,曾被送到庙里当小喇嘛。这种美感和才具,是从哪里来的呢?莫非有个仙女怜他命苦,就在他手抱羊鞭,脚插在粪里,偎依在老羊的尾巴下困着了的时候,悄悄来至身边,用晶莹的珍珠换掉了他脸上的清泪?
所以我成了个根深蒂固的天才论者,从不相信什么努力成材之流的。那没有天份的,打死他也上不了架子,不如让他去做适合做的。而在自然的运行之下,即使是沙漠里,也会有海市蜃楼,空中花园,超出人类愚蠢的定理和想象。奇迹本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是我们自己逼仄了心性,划地为牢罢了。
◆阶级问题
我妈妈家不是旗人吗?怎么和汉人结了婚呢?
我小时候看《古文观止》,读到《陈情事表》和《出师表》就号啕大哭。长大后看有的评注,说读《陈情事表》不哭是不忠,读《出师表》不哭是不孝,我从小可是个忠孝双全的好种子,但水土不合适,就不容易发芽成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爸妈长期不在身边,见也是短暂的,我想当二十四孝都不可能。直到我成年,妈妈退了休,我们才能长在一起,我又被工作逼得白天黑夜加班,竟没多少时间陪老太太去玩。今年5月份,我累得脱了形,想这么着可太过了,老板并未要我如此牺牲,现在就死了也是大不孝,所以就干脆申请了 PART TIME 的工作,在家睡起大觉来,睡醒了就陪老妈去逛街。我妈妈是什么热闹都要看,什么价钱都要问的人,我经常在后面拽她。我妈妈多年来持续申斥我:“你跟你爸爸一样!总在后头拽人,让人看了笑话!我一买东西就怕带你们爷儿俩出来!”但她又得带我们出来,否则她那些能让分类学家暂时休克、猪八戒掉头就跑的东西谁给她拿呢?老太太还热爱祖国的文化和各种人文景观,颇有文艺修养(人家是专业文艺工作者,曾与梅兰芳、乌兰诺娃等同台演出)和诗意情怀,总喜欢指点江山,感慨兴亡,一出去逛景儿就一定拉上我,说我肚子里掌故多,什么都能讲出个道道儿来,说话儿有意思。
我带老太太一连气游了几天后,轮到了北海公园,可那时平安大道正在修,暴土狼烟的,我们遥望了一下生了退意。我脑瓜一转说:“咱们去恭王府吧,看九十九间半和王府花园,比北海公园也不差什么(规模小多了,不能比),原来是康熙朝名臣明珠的府邸,他儿子就是纳兰性德,大诗人,花园人家还说是大观园的影子呢,贾宝玉在那儿住过。”过去的恭王府,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有无数的研究所在里面,当然不收门票的(花园要收)。老太太高兴地同意了。
那里确实是个好地方,幽静又阔朗,后面的九十九间半(恭王府是原北京仅次于皇宫规格的建筑,故宫不是有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么?这里就是九十九间半房子)看过,雕花木头楼梯上咯吱咯吱走过,艳红的石榴花摸了几朵,我们就去看层叠的跨院儿。东边的音乐学院是我喜欢的地方,经常弦歌阵阵。在那么古色古香的地方,迤俪传来零金屑玉,寻声转过雕栏,一个清秀的学生肃穆地坐在树荫下,流离的碎影撒在他身上,和着铃铎和鸟声,专心拉着大提琴或抡着琵琶,几疑凝碧旧池头,萨尔茨堡一会。
那天好些学生在排练钢琴与民族管弦乐队,我妈凝神听了听,说有几个学生调儿定高了,而且不齐,很满意地享受了会儿后,又评论起身边的建筑细节和功能。我一向轻视妈妈的智商,可那天她说得极专业,倒教我吃了一惊。我妈自足而有点惆怅地一笑,说我们家原来就在这儿不远儿的地方,是个中等大小的门脸儿,高台阶儿,朱漆大门,厚门槛儿是活的,进车轿时提起来,平时顺放着。门洞外靠门槛的地方两侧有石鼓,上面雕有石狮子,使门槛有依托,不走形儿。门前有拴马桩,上马石,饮水石槽,老榆树,国槐。进门迎面是砖雕的影壁,转进院子来,地上是大瓦金鱼缸,青灰色或黄、蓝琉璃瓦的,里面有小叶荷与慈姑,给鱼遮荫、甩籽用,里头也放些蝌蚪喂鱼,有逃脱了馋吻的,就变成小青蛙,跳上荷叶来。院子里种着石榴、丁香,低矮观赏的是芍药、牡丹,靠墙阴是玉簪(北京话读如春,轻声)棒儿。院子两三进,正房内宅住主人,东西厢房是花厅、佛堂、书房、客房、下人住处等,正房厢房都有回廊连接,雕梁画栋带到跨院儿和后房……进了正房八仙桌上摆着帽筒,是穿海水江牙补子的姥爷放顶子的,墙上也有时髦的照片,他们都穿马褂,旗装,梳两把头,穿花盆底鞋,女人不裹脚。妈妈尤其喜欢的是桌上一架玻璃丝(是真的玻璃)编的桌屏,上面是彩色的八仙人儿,可好看了……
我妈妈家原住在后海一带,和过去的醇王府、现在的宋庆龄故居在一条街上,过去这里都是亲王、贝子贝勒、镇国公之类的府邸。她祖上跟过老罕王,属第一批进关的鞑子,家里有家谱,宣纸的记功簿子上有骑马射箭的小人儿,后来大约是出了五服。她姥爷原是内务府的,肯定贪污了皇上许多银子,民国时已经败落了,把原来的院子卖了搬到小地方住,犹能给三个姑娘一人一个四合院,他们家没儿子。在满清破落后,他们把花盆底和长辫子收拾起来,心下有些惶惑,本来满汉是不通婚的,但为了共和,急切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旗人小伙子,大姨姥姥和我姥姥(三姨儿)就都嫁了汉人,我二姨姥姥怜惜一个亲戚家人口多又没房子住,把宅子给了他们,自己出了家。
我姥爷家本是北京东郊的富户,恰在我现在住的牛王庙一带。他受过西洋教育,会说洋文,年青时浅色遮阳帽,吊带西裤,三接头皮鞋,完全是个西崽。他们当初也算是门当户对,姥姥嫁过去的时候头上手上黄的白的,私房宝贝,还有房子;姥爷家也是有好几顷地,拴了好几辆大车。但这些都被好酒贪赌的姥爷给败光了。他落魄到喝人家的剩酒,没下酒菜就指使儿子扣蝙蝠打乌鸦烧了吃的地步。到后来,房子地都卖光了,他又不肯好好做事,干一个被人辞一个,家里就困难起来。他们旗人的脾气,都是好闲惯了,不知道劳作,倒肯去要饭,于是我姥姥就带着一大串孩子(5男2女哦!但并没有全可的福,抛弃封建迷信!)过起了要饭的生涯,直到北平解放。
刚解放报成份,我姥姥福至心灵报了城市贫民,得以免遭历次政治之祸。其实那时她手里还攥着些东西,金银首饰都有,只是藏着不露。我姥姥坚持不变卖那点珠宝,宁可要饭,就是防着大变,也是因为她根本不能相信我姥爷。予生也晚,还见她用一柄雕镂得很精的象牙小勺儿舀茶叶。他们那时去要饭,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带个篮子,上面还要盖块蓝布,以免让街坊见到是剩饭寒碜,对人就说是做工去了。老北京人是很要面子的。
姥姥顶着城市贫民的帽子顺利过完了后半生。大约她说:“我们是城市贫民,贫农!”说惯了,又被政治吓破了胆(我爸妈都没能免去“老九”的灾难),口里总远没提过家里的事。我是她从小抚养大的,竟然不知道她们家的历史,她不爱说话,我也不爱说话。
在蝉声和鸟声中我听完了妈妈的故事,排练厅的门开了,年少的学生们呼隆隆跑出来,净是松糕鞋、彩指甲、露出小蛮腰的女孩子。眼前梦影截断了,我和妈妈站了起来,妈妈说走,我带你去看看老家去吧。
我们出了来,旁边就是母校辅仁,本想带妈妈去看那后花园(当过许多电视剧场景,到了夏天什么鸟儿都有),叵耐看门老太太磨牙,号称未见过我,学生出了校门就变脸,竟问我要学生证儿,哪里找去!我给扯回到现实中来,拉着妈妈越过呼噜噜的人流去她的老家。绕过前海长长的河边绿柳,走过银锭桥高耸的陡弯儿,我的心情竟比妈妈还要急些。妈妈一路说着房子的地理位置和特征:“就在河边第二个拐弯儿的地方,门前有棵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槐树。”待我妈熟视着河边的拐弯儿,又前后撒摸了几眼终于确定地说:“就是这儿!”时,我转头一望,那真是扇中等的乌漆门--灰瓦--漏窗歇山墙--门口有圆的石鼓--墙壁全给建筑用的布围了起来,越过围布看得见里面气派的房子好几进,组成个大型四合院儿,黄白的柱子、椽子、门窗,还未上油漆,地下一片青砖、条石、瓦块儿--正在盖新房子呢。我张口结舌,叫了位师傅来问:“这儿是干什么呢?”师傅说:“是盖新房子呢。”“旧的呢?”“拆了呗。”“盖新房子干嘛?”“是房地产开发,准备卖呀。”“那这儿那棵大槐树呢?”“唉哟,那我可没看见过,早给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