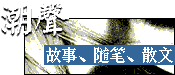1
……(“杭白菊”,这三个汉字所隐藏的植物之光,闪烁在自嘉兴到杭州的公路两侧。)杭州。汽车东站旁闷热油腻快餐店的位置很高。恶俗彩色的坚硬座位周围,复杂的气味狰狞袭人。我和阿福在吃清汤寡水的“杭州牛肉面”。开往浙江各地的各种汽车迟疑着、鸣叫着、拥塞着,在脚下不间断地放气、移动。磅礴的水泥钢筋立交凌空压迫在不远处。城市的空间被粗暴吞噬并宰割。桥洞内是一个世界。水果摊杂乱流动;盛茶叶蛋的酱色面盆内蒸腾热汽;空空的三轮车夫倚伏于车把在渴盼货物;还有无数的人,那些衣蓝着褐的外来者,目光茫然沉郁,在这个异乡的都市寻找着生存的明天……。吃面。离开。然后继续上车。
古老的曹娥江在漫长时间里早已流逝了悲伤。夜色中耀晃的粼粼波光,此刻含满的,是90年代末膨胀的低浅欲望和遍街洗头房门口转动的暗红霓影。坐在高高的防洪堤上,无数灯火的上虞县城就陷在一侧的低地。江上的夜风擦洗着稀疏碎星,我们专心注视的,是身旁黑暗里钢铁纵横的过江铁路大桥。一头身材奇长的钢铁怪兽,心脏燃着红焰,嘴里喷吐小山样浓烈的白色汽雾,尖叫着撞进了脆弱高矮的密集民居--这只是幻像,现实中黑影纵横的跨江铁桥仍是空空荡荡。……真实刺耳的火车尖叫在午夜来临,它首先击醒了五层楼上简陋旅馆内两个外乡人恣肆的眠梦,并且,使曹娥江边这座深渊县城在显示虚无的同时,又带上了某种金属意味的逼真与灼切。
2
灵异却又沉睡的一处地方。寒冷的6点钟的夏晨,如烟似雾的雨丝,隐在浓密河道与树木阴影中的旧时代风格的砖木楼房,枯黄潮湿的草间落叶,一只野猫,长廊,水池边上灿烂欲腐的红绿美人蕉,白光(白马湖偶尔漾闪过来的荒凉白光)……时间在这里已经完全失去前趋的惯性,春晖中学北端校区现在所存留的,仍然是20世纪20年代的图景与声音。一个住校的过去年代的男人,穿着白背心,睡眼惺忪地在有暗旧红栏的二楼走廊上,往铁皮漏斗里倾倒昨夜的剩菜。通往破败河埠的甬道上空,飘舞的雨丝使夏晨寒冷;美人蕉持续肆虐地盛开;……令人怀旧的强烈氛围。被群山与湖包围--春晖--灵异却又沉睡的地方,像有巨大的引力(源于美好、洁净而又神秀的浙东山水--我认为),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此之多的精英(夏沔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俞平伯、叶圣陶、弘一等)聚来此处,在闪着菱香的白马湖的昼夜光影中,他们教书、写作、喝酒、散步,或者短暂闲居着,享受湖山翠色的沐洗。1924年3月9日,应老朋友、春晖中学青年教师朱自清(27岁)的邀请,人在杭州的俞平伯(25岁,“穿了一件紫红的缎袍,上面罩了一件黑绒马褂,颇有贾宝玉的样子”--当时一位学生的描述)到白马湖作客。那天晚上,当时主持春晖校务的夏沔尊(39岁,他的《白马湖之冬》在中国散文史上应该是不朽的经典之一)就盛情请朱、俞二位到他家,著名的“平屋”--1999年8月3日早晨我在紧闭的屋门前留影--吃饭。那是白马湖边一处普通却“雅洁”的住宅,屋内摆着瓷器、铜佛和名人字画,还有栽在小白盆中的青竹,“上灯时,影子写在壁上,尤其清隽可亲”(朱自清语)。那晚是一场畅饮欢谈,应该新开了一坛绍酒。俞平伯回忆,“沔佩二君皆知酒善饮,我只勉力追陪耳。”一个“追”字,于谦虚之中,俞平伯实际也透出了自己的酒底。(白马湖作家似乎都有酒囊,上海开明书店时期,他们曾创办“开明酒会”,酒会每周一次,入会条件之一便是一次要能喝5斤绍兴加饭酒。)畅饮之后,辞别夏家返回时的情景,在俞平伯的笔下现出至今浓烈的诗意:“饭后偕佩弦笼烛而归。长风引波,微辉耀之。踯躅郊野间,纸伞上沙沙作繁响,趣味殊佳,惟苦冷与湿耳。归寓畅谈至夜午始睡。”……现实八月的春晖丧失了生动的声音,苔藓爬上裂坼的墙壁,绿得发黑的植物在暑假的校园内寂寞疯长。从北校门出去,过春晖桥,平屋、小杨柳屋(丰子恺住宅)、晚晴山房(白马湖诸君为弘一法师集资所筑的住所)等昔日住屋皆锈锁闭门,以拒绝与沉醉的姿态,继续浸在自己酣眠已久的梦中。那条蜿蜒在白马湖边的,通往甬绍铁路驿亭站的窄长煤渣路,现在已经换铺成水泥小道。像朱自清当年在这条小道上往来于春晖与宁波四中一样,我们步行前往驿亭。阳光这时从淡墨的雨云间射出来,水稻田上清脆的鸟语与满眼波动的旧日湖光,令人在绿色的恍惚中觉得,一步步,我们现在走入并置身的,正是过去曾经存在过的某段时间。
3
虽然近海,但陌生章镇世代所拥有的,仍是我熟悉的那种喧杂自足、色味斑驳的内陆式生活。因为,连绵苍翠的四明山为它挡住了从东方吹涌过来的咸涩海风。从浊闷的中巴内下来,满视线所呼吸的,便是突然涌现的、八月上午的……章镇气息。空旷的偏于镇尾的小车站,一面旧墙上已被风雨漫漶的演出海报,臂弯里的篮中装了活鸡和柏枝米糕的蓝衫老太……我们向镇中走去……旧街布店前的法桐树荫下,两个男子在凳面被磨光的小方凳旁坐着喝茶;狭小音像出租店内的那位少女,在巨幅“还珠格格”的印刷图片下,正埋头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到达的丁字路口应该是章镇沸腾俗世生活的中心。载人的机动黄包车挤成一团;“华联超市”将彩电、落地电风扇、塑料浴盆、散发油味的新自行车、糖果、制作八宝饭的小包装原料等几乎所有商品都搬上了街道(因此幽暗的店堂里--为省电而关灯--显得格外空空荡荡);庞大熙攘的农贸市场就在近旁,透过瓜菜肉蛋的繁忙交易,我看见的,是黑暗里当地居民鲜红强劲的蠕动之胃。章镇还是葡萄之乡,结实的、紫色的、沉甸甸的硕大雨珠子成捧成堆地积聚、滚落在小镇各处。收获的汁液在空间激射。激射的、舌尖的……汁液,如此甜蜜。章镇,跟中国文章有关的这个古老小镇,我们来此寻访的1900多年前在此疾写文章的寒门王充,如今何在?
王充(27-约97)含满茶香。浓厚的白云,无边无际起伏茶树的青色群山,断续而悠远的鸟鸣,正午寂静却强烈的阳光底下,墓地清凉,王充和他线装的《论衡》含满茶香。这里是自然世界的偏僻一隅,风向着遍植茶树的无人山坳轻轻走去,一只蜻蜓的翅膀,在蟋蟀草的叶尖,变幻银梦似的斑斓细辉。章镇的喧腾已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在此之前,从章镇出来,烈日下沿发烫的104国道步行,再拐进山里,穿过一个破败的国营茶场(团团浓荫下碉堡状的青砖建筑很是奇特),终于,我们找到了在此长眠的前辈王充。大地所喷吐的清淡茶香包围并浸润着这个生前“贫无一亩庇身”的哲学家的轻细睡息。……就是前世的孟轲和荀卿,近世的扬雄、刘向和司马迁,都不及他的才识和德行--同乡挚友谢夷吾曾这样上书朝廷力荐王充,然而,这位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还是贫病交加,于垂暮之年凄凉地病逝于家中。“文章憎命达”?!又一个多么让人悲伤的典型!但是,尽管身处寒微艰难的环境,他的脊梁始终骄傲地挺直着,无论面对世俗或意识领域的权重者,王充所表现的,始终是“我与你平等”的无畏果毅的任侠姿态。孔孟在西汉时已渐渐被神化为“圣”,而王充在他的《问孔》、《刺孟》等光辉篇章中,以明快犀利的言辞,揭露了孔孟著作中所存在的自相矛盾的论点,显示了他卓尔不群的伟大学术人格(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祖国历史中我所尊敬的李贽,则已是王充1400年之后的优秀学生了)。……充溢故乡之音的山岗上,一生进击的身姿终于可以安享长眠(美好的地方,令谒者安慰);而费20余年心血着成的不朽《论衡》,则将永恒地,在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书籍建筑内,闪射东方式的战斗的精神光华。正午寂静、强烈的阳光在茶树的墓地奇异地变得清凉。白云下的墓道上荒草茂盛。用手触摸黑色的粗糙墓石,我感受着温度--无边无际涌过来的清淡茶香里,由冰凉黑石所传递的、我懂得的一种内在温度。
4
明月的深夜,即使睡在附近老乡家中,仍能强烈地感到国清寺四周千年老树汹涌过来的夹杂微淡香火的黑绿清气。波涛般的、浓劲的、无声的……黑绿清气。较之俗界,交错如云的深色树冠使古刹每天总是提前进入它所热爱的黑夜。有少许落叶的寺旁山道洁净,涧水在深沟里溅响。我们下去。树的夜。浑圆的大小岩石,像山中的白色奇兽,蹲立在挤泻的冰凉涧水之上。……盘结虬曲的老树根桩在夜半总要将这座黄颜色的隋寺抬高几分。诵经时闪烁若星的磬音早已停歇。依然汹涌的黑绿清气--酣眠时难以辨别的寺或树的沉醉呼吸。
〈天台的想象图景〉天上的神安放的一张台子,巨大的石头台子,用近旁的东海擦洗过一遍的石头台子。台面上,杂乱堆放着砍伐的森林、梦、斑斓的南方矿产、白袍诗人和数不清的疼痛青竹……,是谁,用正午的毒太阳将它们轰响点燃,大海边南国的大火瞬息熊熊。天台,巨大的石头台子,昼夜激燃着南国大火的石头台子……
〈天台的现实图景〉黎明即起,于青色的群山万壑间乘农用中巴上山。在山顶龙皇堂暗湿小吃店等吃早餐时,测绘专业出身的自由撰稿人阿福指着地图对我说,从图上的水流分布情况看,这里确实是一处面积极大的平台。龙皇堂是天台山上石梁小镇的行政机构所在地。我们到得很早,挂着破牌子的镇政府边上,两个肉墩头上的鲜肉尚未卖出多少。一个山民,支好两头弯起的竹扁担,正往铺在地面的塑料纸上倾倒茄子,蛇皮袋中塞满的沾着露水的紫郁茄子。剃头店刚开门,一脸盆的脏水泼出来,令一只正在门前徘徊觅食的老黑狗(一条前腿短了一截)惊慌奔跳。地面凹凸不平,装满石料的拖拉机冒着黑烟左摆右扭,跟在人家挂着竹篮的载重自行车后吃力蜗行。两家烟酒铺前的炉子已经生好,端碗喝粥头发未梳的妇女向下山的熟人高声说着笑话。太阳升起来,一滩一滩潮湿的、有公鸡散步的灰尘地上蒸腾起微微水汽。在拐腿女人的小吃店吃早饭时,我看见光着上身的黑男孩啃着棒冰,拿着一包香烟正从坡上的那个石头房子商店里走下来,天台山动人的晨光,在那一刻,将他微小的轮廓描上了灿烂的金色。
蝴蝶像黑色的鸟掠过头顶,给人的额角带来一羽突然的微小凉风。“群山万壑赴荆门”,从龙皇堂步行前往天台的最高峰华顶,随便在盘曲的山道上一站,眼前就是此景。不过这里应该用“赴东海”更为贴切。天空下身处的群山万壑,其实也是波涛起伏的青碧大海--起伏、然而凝固的大海。“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人在这凝固的海浪海谷里移动,宛若飘浮的草屑或蝼蚁。……华顶。青碧山岳的波浪之顶。僧影往来。破旧的门楣上读到悼联:证果已全,音容先到莲座侧;事功未竟,心迹长留白云间。--悼正海法师圆寂。流云擦着山石树草越过山脊,被密硕的紫藤、山楂、柳杉、野核桃和杜鹃树(灵奇的树种在此竞生)簇拥的若干寺房,让人无法拒绝地感受到华顶深邃的佛气以及,难以见底的、正透露着勃勃生机的,古老。
5
邮政大厅狭小的电话间。未见过面的台州青年诗人、专营筛网滤布的个体老板余跃华在电话里大声对我说:你们在旅馆等我,我马上从黄岩赶回椒江。椒江。曾被台风中的海水冲刷、浸泡过的这座崭新现代小城,现在漫拂黄昏前的清爽海风。商店闪耀。袒胸露臂眼影很深并且对着手机大讲方言的海滨女郎,正在走逝于玻璃的巨幅深渊。街头的快餐店已经摆出了色彩艳丽的美味海虾。大海的声音隐约可闻。……夜晚八点,风尘仆仆的余跃华在椒江大酒店请我们吃饭。《台州文学》编辑、老家在天台山深处的胡明刚也一起见面喝酒。美好的谈话、啤酒和……海鲜。他们的生存心态和对自身所处位置的自觉以及虽不张扬却明显凸现的勃勃野心,给人刻下很深印象。话题中谈到“人与地域”,细细检点一下,确实令人大吃一惊,在狭长的浙江东部沿海一带,仅限20世纪,随口之间便可举出一长串闪射光芒的人物名字:俞樾(德清)、夏曾佑(杭州)、章太炎(余杭)、王国维(海宁)、秋瑾(绍兴)、刘大白(绍兴)、鲁迅(绍兴)、周作人(绍兴)、夏沔尊(上虞)、徐志摩(海宁)、郁达夫(富阳)、茅盾(乌镇)、丰子恺(石门)、应修人(慈溪)、夏承焘(温州)、夏衍(余杭)、许杰(天台)、柔石(宁海)、王以仁(天台)、陆蠡(天台)、金庸(海宁),等等。又一个崭新的世纪就要来临,作为这片“人文之域”的后来者,于奔波尘色的底层谋生中,他们在内心,已经默默领受了一份承继的责任。……从吃饭的地方出来,入夜的椒江似乎突然挤满了媚艳的灯彩、嚣杂的车流和纷拥的人群(而黄昏时还是空阔而寂静的)。通往海边码头的街道两旁摆满商摊。冷饮摊内座无虚席,冰淇淋和激旋的可乐在夜色里散发甜味;一长溜行军床上的港台和外国碟片被翻得乱七八糟;在旧书摊上我们找到老版本的《都柏林人》;街头练歌铺最具特色,大屏幕彩电中正在放着《想和你去吹吹风》,那个头发染黄的青年唱得投入又极具专业水准,但他的声音对于在服装摊丛林内游弋的人来说,宛如无数车轮在人流中的某次急刹一样无动于“耳”……站在浮动的码头上,昏黄光线下的海水褐黄而浑浊。身后的城市,此刻,正在走向它所迷恋的、夜的璀璨巅峰。
6
黄皮肤陆地的一处尽头,海湾山旮旯里密挤石屋的小小渔镇,石塘。码头腥臭--在国家版图东端的、微若水滴的渔镇石塘,我们始终遭逢的,是惩罚,大海对于人类肆意掠夺的内心痛苦的惩罚。所有的屋瓦上都恐惧地压着沉重的石块--显示过去或将来从海上刮来的巨风的痕迹。揭开盖的舱中,银光熠熠的成堆死鱼,连同岸上角落里乱七八糟的塑料筐中的发白细虾,正一起散出浓烈的腐烂气息。飞舞的黑色蝇群近旁,破败制冰厂似乎日夜繁忙,呼啸闪亮的碎冰通过黄锈驳蚀的铁质管道泻进即将出海的渔船。披红带彩、刷有“以马利内”的新船在港湾下水,船上站满的古铜色人正为即将增添的钱额而热烈燃放鞭炮。纸屑与死物的水面荡漾。--无法避免的现实与生活?……海洋开始摇晃,两舷挂满黑色车胎的木船升起继而坠落,我们离开岸地,向大海的深处前进。“青春和海洋……愉快而强大的海,咸湿而苦涩的海,它能够在你耳旁窃窃私语,它能够对你怒吼咆哮,它也能够使你精疲力尽……这就是海的奇妙之处。是海本身就是这样,还是人们的青春使它这样,谁又说得清楚呢?”康拉德。我所热爱的表述。渐渐地,暗蓝大海瞬息激溅继而堆起的絮沫,和天上翻卷的云山开始呈现为同一纯粹的颜色。真正属于大海的、一种伟大而磅礴的清新也突然来临并深深浸彻了身躯。……但是,大海仍然摇晃。寂静、难以诉说的海洋的巨大力量,仍然在拍撼着近旁的陆地,拍撼着陆上代继一代埋首人类的世俗生活。--我知道,这是提醒,海洋对于人类尚未放弃的最后的提醒。只要仔细观察,谁都会发现,这种善意、迫切并渐生郁闷的巨大内心情感,在20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已是如此焦灼。
(1999.9)■〔寄自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