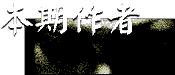<戏仿的严肃性>
II 入 调
当没有听者在跟前的时候,伯牙会习惯性地沦陷在自己的听力之中。他比任何听者都更注意倾听,他体内的听者更甚于他体内的那个演奏者。趺坐在已经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烫的前甲板上,这一次,伯牙抵达了对一个像他这样的琴师而言近乎致命的幻听。这幻听的象牙球玩具里,层层相套着对钟子期的倾听之幻想、幻想中的钟子期之倾听,以及钟子期的幻听中对他的一切倾听之遥忆、回味、幻想和臆测。所以,这一次,在光阴之城,伯牙沦陷于其中的其实是一个听的漩涡,而带来这漩涡的正是流水。作为境入希夷的奏弄大师,怀着当红影星翻看画报封面上自己的大幅美人照的那种心情,伯牙也曾在旅程中听到过几位自封的识琴者聪明、却难免误会的由衷赞叹。而这一次,要表示称许的将会是奏弄大师自己。因为钟子期的倾听,特别是因为他的沉默,伯牙得以真正入调,自孤高岑寂、淡入悠远的弹拨间,辨析不仅从自己的七弦扩散的琴音和仅仅从自己的七弦扩散的琴音,以及,那并非不被听见,而是被听见忽略的弦外之音,甚至并非被听见忽略,而是被听见以确认的方式无视的音外之象直到象外之意。有一支黄铜号角忽然在离小码头不远的水兵营地吹响,几乎打断了琴师伯牙的幻听而不是演奏。不过,很快地,那喇叭也汇入了听的漩涡,并通过这漩涡漏斗成为流水中不能分辨的新的暗流。只稍微浮出了一小会儿,伯牙又更深地沦陷进幻听。他同样会误会。他并不能想象,钟子期的沉默是如何以话语镂刻进玲珑的象牙球玩具的。
10.言说与意会
一注水流要映现多少莫测的幻象?时而是云影,时而是星空,是雁阵和人面,是博物馆的尖顶因瞌睡而弯曲。在某个黄昏,被映现的也许是影子乐师,飞过逝川,接着又飞回,素琴的焦尾被溅起的浪花打湿了一半。素琴奏出的那个乐句,你知道,也会有一样繁多的言说。言说在乐句之上,令乐句将它们映现。几乎是因为言说这幻象,影子乐师抚弄的一曲才成为音乐。世界因言说而变得迥异!不过,在逝川岸畔的老红灯区,在有着九扇水晶屏风的承露夜总会,影子乐师迷恋每一个粉妆艳姬、小蛮腰淫娃,抱定的却必然是与他灵犀相通的夜女郎。影子乐师要让她脱去障眼衣饰,呈现身体的本来面目。而在另一侧,在这座小码头,撇开众多的言说幻象,我所意会的,也正是你已经入调的这一曲流水。
*
意会乐句或乐句连缀的这支琴曲,听者的表现是他的沉默。而奏弄之先,或当你奏罢,你的表现也一样是沉默。在你的沉默里,听者以沉默意会流水;而当听者有所言说,沉默被打破,你奏弄的曲调浮现出音乐。实际上,在这座小码头,奏弄本身已打破了沉默。曲调也就是一次言说,是所谓音乐。至于听者,其言说的也正是他所意会的。而如果意会是脱尽言说衣饰的裸体,那承露夜总会的夜女郎裸体却依然在言说,被惯于抚琴的一双手抚弄。她眉间的朱砂、唇边的美人痣、小小的乳晕围起的乳头、肚脐和阴蒂、嫩大腿上隐约的胎记,是影子乐师所一一比拟的恰巧的金徽……。既然,水晶屏风后,弧形睡榻上,那影子乐师以夜女郎身体的幻象之琴奏弄了音乐,我又为什么不放弃沉默,去言说意会中入调的这一曲流水?
*
伯牙啊,当影子乐师因抚弄唤起了夜女郎的舞姿,从小码头望过去,你会说舞姿才是那音乐;正如逝川,它的流动才是那音乐。只是因为舞姿贯穿,夜女郎的霓裳羽衣或无碍的裸体才相关音乐,那言说或意会,才相关音乐。又正好是由于影子乐师的曲调贯穿,夜女郎领受抚弄的身姿才成为舞蹈,才被言说或意会成音乐。而如果那裸体并不意会影子乐师忘情的抚弄,而如果那抚弄并不被裸体用姿势言说,在承露夜总会迷乱的氛围里,影子乐师将如何使他的一曲成形?舞姿在那边光影里暂竭。这边,泊靠小码头的旧船甲板上,你的琴曲依然继续。奏弄的手指在弦索间言说,一个听者则用心意会。或许,不一样,素琴将意会传达给空气,听者却言说,你正在入调的这一曲流水。
11.文字谱
不必想象
被奏出的音乐
在素琴上
手指的雁舞
手指的凤舞
或手指像文豹
在横过月影的松枝下偃卧
将带来想象所难以想象的
一次惊心
一种颤栗
仿佛正埋入
情人发丛的
寻欢的鼻子
被静电击打
每一个乐音都不可预料
唯有指法,虚点
细吟,让空气传达
一支曲调,触及了鼓膜
奇迹在世界的绝对真实里
更像这世界的事物本身
不带有
一丝想象
不带有
一丝神秘
只确切地存在于
平静自若的奏弄之间
12.意会与空无
从光阴之城旧城墙高耸的一座角楼,能够看清楚与之遥遥相对的宝塔,寺僧在最高的那一层凭栏,跟角楼旌旗间摆开素琴的乐师对称。在他们之上,像三角形越来越清晰的顶点,一钩新月把黄昏过渡给到来的晴夜。那寺僧听不到影子乐师月下的抚弄,他能够听到的仍只是隐形的一曲清风。空气传递音乐,将抵达宝塔和寺僧之时,音乐却已经变成了空无。不过那寺僧未放弃倾听,即使是空无,他也能从中意会到音乐。遥遥相对于素琴奏鸣的渐暗的空无,乐师心灵虚幻的不存在,像月光为他带来的影子,甚至已不需要加以意会了。而那个寺僧依旧凭栏,他意会角楼上乐师的曲调间更深的空无,虚幻中真正的秩序和绝对的宁穆。在这样的意会中寺僧令空无超出了空无,一支已经被不存在熄灭的曲调又复燃,呈现属于空无的形式,和超出了空无的意会的形式。当寺僧又意会这再获的音乐,意会也肯定超出了意会。他听到未曾被空气传递的所有的音乐,包括你还没有奏出的一曲。
*
这样的对称里,另一个对称的反例出现,目的则几乎是为了打破这对称的格局。--就是在同一堵城墙之下,仿佛被同一钩新月照耀,一个以推断见长的将军有一次失误。他曾经率大军攻打不设防的光阴之城,却受阻于城楼上同一位乐师匆忙的一曲。那将军仿佛听到了音乐,并且被灌迷糊,并且在迷糊中收兵和退却……或许他未听到曲调中近于颤抖的寂静,不懂得意会军心涣散中混乱的烦燥?事实上他听到的仅仅是空无,当空气把音乐从高高的城墙上传递给大军,能够抵达将军和马耳的,也无非是空无。那么,推断将军并非被一支琴曲击败,他遭遇的是那支琴曲背后全部的空无。那么他如何意会这空无,那怕是外行地,以毫不意会去意会空无?他的撤退似乎表明他一样触及了更深的空无,意会到城楼上乐师内心的镇定和安祥。他也从空无超出了空无,从而使意会不仅是意会?……然而,伯牙啊,真的是由于意会的失误吗?那推断将军意外地从空无获得了音乐,包括乐师还没有奏出的,能够把大军击败的琴曲?
13.空无与期待
绕过邻近水塔的中医院,穿过两排夹道的青榆树,从那座出售曲谱的木拱桥过河,你会看到,由兵器库改建的实验小剧场半隐于暮色,迎接并不会太多的观众。月上高杆后,巡演到光阴之城的流浪人剧社,要搬一出老戏上台,要让一支琴曲,由隐形乐师在暗中奏出。音调渐低时,现身的男主角会被你认出。更多的时候,看戏的人们却忽略这男主角,一心只期待琴曲有可能带来的音乐。而那出戏关涉的也正是期待,那个男主角,在舞台上表演的也正是期待。当月亮已经向光阴之城的宝塔和正西门偏去的时候,兵器库小剧场,正演变为一座期待的小剧场。这期待的戏剧令期待以外的都成为空无,甚至期待者也只是空无,甚至期待,也只是空无。众多的空无,为了更凸显那被期待之物,仿佛它随时会到来,不仅来到剧场的此夜,不仅来到反复的戏中,也不仅来到涟漪般散开又聚拢的期待……。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必然:那被期待之物、终于向期待现身之物也只是空无。流浪人剧社如此完成此夜的戏剧,令期待本身即期待的戏剧性,即空无的戏剧性。它延伸到它的戏剧性之外,在兵器库小剧场岑寂之后,又月光般映照有流水琴曲入调的小码头,似乎想问及,在你的演奏和我的倾听间,同样的戏剧会不会重演?
14.文字谱
然而,奏弄
把声音从梦
运送到指法
向七根弦索
恰切地低语
那七弦转达的
却可能已不是
最初的那个梦
有如经历了
一次混血
婴儿的瞳仁
异色于父亲
曲调在空气里
成为它自己
成为它想要
倾听之耳产生的
那个梦。比预料
生动,却不够准确
令双手唯有
再一次奏弄
啊奏弄
再一次
去恢复一个音
去恢复一个梦
去找回指法的
精神之父
15.期待与梦想
在光阴之城里,几个到火车站附近的一片幽林去玩耍的小男孩,在游戏间歇里,会安坐于道边的旧枕木上,等一列梦想的火车经过。而在一列到来的火车车厢里,在硬卧的某个晦暗的中铺,隐形乐师以一个乘客的身份现身,半躺着朝窗外偶然一瞥,会把那几个期待的小男孩当成自己早年的梦想。换一个场合,在一幢因梦想而建筑的花园里,那期待情人的惊梦小姐要返回一个梦,要让一个乐师为漫长的下午奏弄一曲,而那个乐师从隐形中现身,会把这下午也作为他经历的又一个梦境。跟他们不一样,在倾听深处,我不敢去期待不可能的音乐,而仅仅把它们归于梦想。可是,当不可能的音乐从你的手指和七根弦索间到来的时候,我有所憬悟,我意识到自己也一样期待过不可能的梦想,并且仍然在期待更难以想象的一个梦。几乎是因为你即兴奏出的不可能的音乐,唤起了听者更大胆的梦想。而由于这梦想的存在,期待才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倾听深处,出现在花园里一个越来越憔悴的身形之中,出现在铁轨弯曲处,在摹仿世事的两个游戏间,在一声隐约的汽笛长鸣里。这期待当然更被你铿然的琴音所蕴含,那琴音却已经是又一个梦想了。在攀向更高的奏弄之梦时,你,伯牙啊,也带来了更为过份的期待。
16.梦想与虚构
伯牙啊,多少年以后,你我的相遇很可能会变为一个传闻,一种虚构和一位诗人重临逝川时短暂的梦想,只不过被当作一阵风过耳。在这阵风之外,有时候,别的故事也会像一阵风刮过光阴之城的街巷、院落、屋脊、老虎窗,改变风信鸡的姿势和指向。那隐形乐师曾倾心于茶楼上说书艺人的演义传奇,讲的是睡美人,被一位王子以一吻唤醒。当那个乐师低眉抚弄,茶楼上虚构故事的说书艺人,是否又反过来成为听者,并且从一个鼓琴的影子里,看到了相似的梦想或虚构?手指所释放的,并不是藏于素琴的弦索间,藏于岳山、龙池和凤沼之间的美人之梦吗?琴曲呢喃,难道不正是出于梦想?但说书艺人会假设素琴里并没有可能的梦的寄居地,那仅只是一段被拨弄的梧桐木,就像睡美人,也许仅只是倒伏于林中的石头塑像。那么,是手指以一吻虚构了素琴睡美人的音乐梦想吗?或者,梦想是虚构的一个借口,一面镜子,折射太阳光芒的月亮,使流水发出声响的卵石、水槽、滩涂、杨柳岸或流水本身?
*
带来曲调的是你的手指,它在素琴上完成其魔术,像另外的戏法,会需要礼帽或火焰为障眼法。但如果鸽子或金鱼并不被隐藏在礼帽之中或火焰之下,但如果素琴并不是可以被奏鸣的乐器,戏法或魔术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呢?光阴之城的一座茶楼上,说书艺人又提起另一个传奇故事,关于动用符咒的方士,如何用大雨把旱季淹没。抵靠着半面石灰墙听书的影子乐师或许会发问:是方士在晴天里虚构了大雨,还是仿佛胸中的梦想,大雨早已蕴含在飘来的乌云之中了?当说书艺人转而又成为一支悠然琴曲的听者,他另一个设想,就近于一个委婉的回答了。手指在七根弦索之间的虚构无非是可能性,是一种努力,是一道咒符或王子的一个吻;而睡美人并未入睡的双唇,云中的雨意,弦索所蕴含的万千音响,则呈现为梦想,并不是可以被凭空虚构的。那说书艺人是否又认为,虚构才仿佛一个借口,而梦想是被照亮的月球,被唤醒的睡美人,被催降的大雨,被卵石、水槽、滩涂和杨柳岸塑造的流水本身?
17.文字谱
工匠在塔上
敲打银瓦爿
电视台的飞艇
悬浮于近旁
一朵玫瑰云
离开得稍远
而云中那醒于敲打的
母龙,沉吟着现形
沉吟着现形了
不再去梦见
声音带来的
天际幻象
幻象中一条
折腰的母龙
这近乎一个装饰指法
在弦上拨弹
让虚音浮泛
却不让虚音
成为属于其自身的
那个音,而仅只
点缀,如塔上的
银瓦爿传递光芒
电视台的飞艇空自悬浮
一条母龙沉吟着
醒来,不再梦见
从弦索迷宫间提升的手
18.虚构与凝神
天文馆坐落在稍稍隆起的丘陵之上。它的下面,有逝川的急转弯,隐士的洗耳处,和新近用花冈岩修建的古琴台。作为雕塑而现身的乐师,在古琴台的香樟荫阴里凝神,让游客于无声中各自去虚构可能的琴曲。他的影子则可能在天文馆附设的光学博物馆的铜镜里映现,说不定只是被铜镜虚构。而如果他面前是一面透镜,当焦点聚拢,正仿佛凝神,影子乐师将会在光中被放大或缩小,一个投影,也许是更为虚幻的影子。乐师又参观了凹镜和凸镜,能复制无数镜像的对镜,然后止步在一颗旋转的水晶球前。那水晶球演绎整座天文馆,它下面的逝川,隐士洗耳处,古琴台上乐师的凝神,和游客虚构的一支支琴曲。讲解员解释说,那是被虚构的琴王星一景。
*
影子乐师继续参观,并现身在天文台最为雄伟的望远镜前。通过望远镜,他看到漫无边际的真实的宇宙,宇宙中飘浮的巨大石块,缓慢移动的星座,发光的太阳和企图吸呐光芒的黑洞。那虚构的琴王星则必须靠凝神才可能看到,那坐落在琴王星隆起的丘陵之上的天文馆,它下面一条河流的急转弯,隐士的洗耳处,古琴台上的雕塑,香樟和过往游客,则正是凝神观望中被虚构的一景。这也是水晶球演绎的一景。这也是他身在其中的光阴之城的一部份现实。那么,虚构,不过是凝神中现实的光学变化吗?乐师未找到向他提供解释的讲解员,但却在一幅抽象的星图间,找到了虚构的星宿可能的位置。那只是星图的一角空白,或一片黑暗。可是,当影子又一次凝神于空白或黑暗的现实,就又会有琴王星现身,被虚构。
*
在并不存在的琴王星上,在水晶球的透澈和光阴之城渐渐晦暗的天色之下,虚构是凝神带来的海市蜃楼吗?如果凝神是过于专注而灵魂出窍,那真实的灵魂,也一样进入了被虚构之物吗?得到了确切答案的乐师,其凝神的影子或偶尔的现身,又是否也将化入虚构?从乌有之星或缩微风景的水晶球里,是否也有一样的凝神,把光阴之城作为镜中反映的灵魂或自我,去虚构可能的琴曲、游客、香樟和雕塑,去虚构确切的古琴台、洗耳处、丘陵之上的天文馆和一位变来变去的乐师?小码头上,你奏弄的流水近于激湍,使一个听者如天文馆下急转弯的逝川改变了他所关注的方向。然而关注却仍然继续,并且这关注已经成为对你的琴曲的凝神倾听。在我的凝神里,伯牙啊,你虚构了多少灵魂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