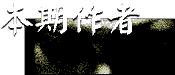<戏仿的严肃性>
VII 入 慢
被某种内倾力牢牢攫住,在又一个黄昏来临之际,对上一个夜晚奏罢流水后听者钟子期的沉默之演绎,几乎要变成伯牙的自我阐释了。他发现,因为对倾听的追究,其思想和语言的转速在加快。只不过,如同车轮在冰面上打滑,那个幻听之中的世界并不真的迎面掠过。他没有说出,或没有从沉默里找到象牙球玩具的最核心部分,那也许会是玉米粒大小的、精刻细镂的象牙珠子,但更可能是一个空心,就像想象的内倾力,总是会归结于中心的空虚。光阴之城里,一种繁复的壮丽到来,十万扇窗玻璃共同反映那一颗落日。而当落日已经与逝川上它被拉长的倒影融合,终于没入流水之中,其幻象仍映现于光阴之城的十万扇窗玻璃,仿佛一曲终了,这曲调还会在听者的耳朵里反复不已。因此,他想说,在光阴之城里时间是缓慢的。特别当黄昏来临,落日隐没之时;特别当一曲奏罢,听者以沉默相对之时;特别当那个奏弄者,在听者离去后陷入其沉默带来的幻听之时;而尤其在幻听里,思想和语言飞旋,企图战胜摩擦系数,追上因无声而光速推进的沉默的音乐之时;时间,或流水,很可能就是缓慢。甚至比缓慢还要缓慢,当需要用沉默去复述那音乐的流水时光,那流水时光就可能重临,上个黄昏和紧接其后的夜晚会被再一次经历。伯牙正处身于这种再一次的经历。而他的疑问是,曲调能否被弹奏之外的方式重述,像有人用话语重述一部史诗的情节,或有人用龟兹文翻译老子的八十一章。尽管那复述方式是长时间的沉默,缓慢的沉默,但曲调是否可以被复述?如果并没有沦陷于近乎致命的幻听,伯牙知道,他将会借用他也许梦见过的爱琴海畔一位哲人的格言作答:人不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即使弹奏,也无法重述同一架七弦琴奏出的曲调。但钟子期的沉默正被他听见,以言辞的,可能更是乐曲的方式虚幻地铺陈。并且,在他上面,大宇宙深处,丝毫不同于他顺着逝川的水上之旅,一张镀金碟片正漫游星际,要百分之一百地向虚空重述此夜的,也许,可能,是上一夜的流水。
55.时间与技艺
逝川流淌;贸易风往还;一枚月亮从圆满到亏空,又从亏空到再次圆满,照耀枯荣之间的草树,四季里嗓音变幻的雀鸟,和纵横的街巷间一幢幢楼宇的渐渐失色、黯然、老化、颓废、直到坍塌又重新兴起,以及一个变幻的女性,她白色衬裙被初潮染红的枫叶形血污、她呻吟中的第一次受精、她数次受精之后的孕育、她涨满的乳房、她的分娩、她的吐哺、她乳房的垂落、她的闭经;而一艘艘装运纯水的机器船趁着大梦又抵达了小码头……。光阴之城里,这一切并不能表明时间。甚至朝不同方向投下阴影的钟楼上指针与指针的相互追逐,市长家后阳台私养的公鸡的引颈报晓,从天文台的望远镜所见的木星的移位运行,也并不是可能被确认的时间。至少,不妨说,那不是技艺的时间方式。
*
陡然急转的玻璃防波堤凸出的部份,一个垂钓者高挑起竹竿,却没有向逝川放下丝线;或者他朝逝川垂放了丝线,却不在线端系上一枚细小的金属钩;即便那金属钩在线端反光,它能够诱引的,也必然不会是入水之际想诱引的游鱼了;尽管锐角度折返,那条鱼也许将逆行上溯,回头去咬住曾打算放弃的闪亮之物……。跟那个垂钓者于无望和希望间的微妙不一样,技艺在光阴之城里,总是能得到那最为生动的时间之鱼,并且在技艺的自我忘却中,又一次次复得被放归的时间。技艺在空气里激荡一个音,时间就必然激荡于这个音。这一定比垂钓更为微妙,无须等一尾游鱼折回,无须把一枚金属钩系上,无须高挑起竹竿,也无须有一块陡然急转的玻璃防波堤凸出的部份。
*
剑的锋刃上一线寒光快于瞬息,却又在接近永恒的静止里耀眼,一个在两座塔楼间绷紧的钢丝上空翻的杂耍人,有着尽可能缓慢的平衡姿势,和必须尽早完成的一整套动作;儿童乐园上空的忧郁间,旧时代的猎手放飞的老鹰一动不动,展现出一个虚无中疾急的十字形幽灵;而你,正仿佛我,会被一个消息震惊,奔过短距离的漫长街巷,到断头台下,听一个觉悟者被宰首之际把素琴拂掠,在他的拂掠里,一颗人头已落地,一柄杀人刀,还不曾启动和见血……。光阴之城的时间放式里包含着技艺,为了让技艺产生时间。技艺有如空心,令时间硕果轻于料想,却又比料想的更难以承担。这无非由于,在另一种比附里,技艺是时间汽车里弄险的司机,比乘客们要求更多的刺激。
56.文字谱
没有一个音不出自琴弦
而仅仅是一番
奏弄的心情
一种对应于技艺的
魔幻。就像不会有
仅属于弦索的纯声音之物
不依靠魔幻
居然被听见
不因为一颗心
而被铭刻于另一颗心
手是半神
暖昧的英雄
以不同名目
跨骑同一匹奏弄之马
那手也可以
幻化马匹
负载奏弄的
影子骑士
穿行于曲调
文字谱、灵肉相间的
可能的音乐
一个仿佛异域的祖国
手是所谓的三位一体
出自琴弦
也出自弹琴人
奏弄的心
57.演奏与时间
在光阴之城里,演奏的意义总是在最后的演奏里到来。而一个人一生漫长的演奏,只不过令他的时间在演奏中燃尽。这就像一炷被点亮的檀香,当它已计时完毕,它自身也告完毕。演奏在空气里震颤音乐,也有如空气里飘浮的烟雾,有一派好闻的气息,终于要散失于无迹。唯有当紧接着又一次演奏,又点亮一炷香,让香火继续,让烟雾再缭绕,让馨人的气息在空气里更甚,让音乐在空气里不放弃鸣响,时间才又在演奏中进行,--时间才成为,或已经是演奏的真正主题了。于是,在那个人最后的演奏之中,当那个人觉悟,时间将终止于这次演奏的终止之处,会有一炷香,被点亮在摆放素琴的明窗之侧,而那个人低眉,会回到另一时间的演奏之中。那可能是他的第一次演奏,如果他坚持,那就会是他的第一次演奏。几乎是因为在最后的演奏中那个人坚持了第一次演奏之中的时间,他一生的时间被留存于最后的演奏之中了。并且当最后的演奏终止,演奏的意义,会延续那个人一生的时间。
*
在焚香低眉的最后的演奏里,他一生的演奏以不同的时间方式到来。甚至,如同在一个一闪即逝的掠影之中,不仅有一只鸟儿飞翔,它以往的每一次成功的飞翔,它的试飞和试飞的失败,那掠影里还有着鸟儿作为蛋卵的黑暗,和这一族类的飞翔历史及漫长的进化史;在最后的演奏里,你也能追溯他第一次演奏之外更悠久的演奏,更悠久的演奏中他从未经历的时间方式和无始时间。而如果时间又将在演奏终止后延续,直到无尽,这演奏就不会是最后的演奏了。在光阴之城里,一炷香又已经灭为灰烬,一次演奏却仍没有结束,那演奏的人,将抽身从演奏的时间里离去,有如大地上疾掠的鸟形从飞翔中离去。真正的演奏必然如此,当那个人建立了演奏的时间,他不再属于这演奏的时间了。所有的时间在演奏中到来,因为这演奏也将不属于正在演奏的那一段时间。演奏创造自己的时间,无限时间之中的无时间。这样的演奏,正属于那个人最后的演奏。
58.倾听与技艺
倾听。在素琴综鸣的每一个乐音里做到无视。光速中急行军的形象世界会调整步伐。它们的新编队或许像盐粒,溶化在不能够两次涉足的流逝之中了。物质的波澜掀动,翻卷于其上的激浪是迟缓悠长被音速慢递的。这拉开了侧耳者跟他的处身空间的距离,并且,几乎,他处身的空间已隐匿和被消解,无视中侧耳者化身为倾听。而如果同时并没有技艺化身为倾听,无视在倾听里就会是盲目的,唯有去忍受耳廓的张开。有如盛夏午后的逝川河滩上,一个人要忍受强光中一副瞳仁的刺痛和被墨绿所蒙蔽,声音的蛮荒灌入被动的听觉器官,其中也难得有音乐到来。必须要动用倾听之技艺,在耳朵和声音间,划出那怕是象征的界限,去对应,听者的跪姿和一架素琴间实际的界限。在界限的这一边,一个人听觉里辨析的过敏性,会睁开眼睛把音乐观看。当恰切的,却难免不是幻视的手指拂掠素琴,触及了那根隐晦之弦,技艺的耳朵里就会有仿佛被看见的一个音,扩展为群星,漫上天际,甚至是灿烂的。在如此晴夜里,在群星之下的光阴之城里,听者又向前迈出一步,超过象征技艺的界限,如此,伯牙啊,倾听之无技艺会展现群星间最为寂静的那片黑暗吗?听力中一对观看的眼睛会被什么刺瞎,令倾听更纯粹?
59.文字谱
迟疑地,解开女衫的
第一粒钮扣
像孤鹜念群
徘徊下顾
那手生疏
缓慢而犹豫
然而指法却变得
果断。螳螂
一前一却,去捕获
长吟自乐的蝉
直到胸衣
完全被打开
弦索近乎一种喘息
急切得就要被
曲调绷绝,一双手暂时
移开了音乐
那手又回来
恣意抚弄
有如一辆
冰上摩托
轮子急旋
在急旋中停滞
因毫无所阻而
深深地受阻
那手将又一次移开音乐
为了更惊喜地触及乳房
60.技艺与演奏
风,演奏一对残损的河螺壳,逝川之水,演奏河滩上被弃的废金属,防波堤上的夹道青榆间,一根马鞭演奏空气,作为回声,雷霆滚过云的牦牛群,一场大雨,演奏光阴之城的瓦爿、玻璃窗、塑料遮阳板和熟铁皮落水管。所有的铃铛,所有的钟鼓也正被演奏,香樟和银杏,塔松和梧桐也正被演奏,飞机的翼翅划破冷空气,那尖啸是演奏的超音速疾急风。在一架素琴之上的演奏却几乎是缓慢的,几乎是静止的,然而在它的缓慢和静止间,万物的轰鸣、喧哗、呜咽和轻击,被蓄势于一触即发的指法,要从一个低音里展现。并且在这架素琴之上,演奏之技艺要超越演奏,要让一根弦成为十根弦,要让七根弦成为精神最有效的嗓子,而一双在其上隐约的手,将不仅是一千双更曼妙的手,甚至是神秘的灵动本身。技艺要让演奏释放每一个可能的音,不可能的音,世界的轮廓,嵌入世界轮廓的物质,物质之血和血液在脉管里流淌的声息,这声息将抵及的死之寂静,寂静中演奏的终极完满。正是在演奏的终极完满里,技艺的繁复从十指间消退,仿佛光阴之城里功成业遂的远征军元帅,匿迹埋名于西区一幢新村公寓顶楼的明亮、昏暗、平淡和琐碎。剩下的将会是定、远和澹、逸,是虚壹而静,大乐必易,是清、洁、幽、微,是徐、细,和无声。
61.倾听与时间
一声鸟鸣如果透过了悬铃木叶片细密的筛选屏,如果它又透过市声吵嚷的噪音封锁线,如果它从一座教堂尖顶的陡峭银瓦上快速滑下,又拐向一条螺丝壳弄堂,并且再拐向荒芜的小花园,从一个已难抿逢的窗隙挤进早餐的客堂间,准确地落入一张鼓膜微颤的耳朵,光阴之城里,会有人因此从一重时间到另一重时间。每一次倾听,甚至仅仅是小于一次的瞬间倾听,都足以让一个人摆脱以往的时间惯性,驶上铺设于乐音之中的时间新轨道。新轨道两侧,新风景吸引更专注的倾听,并且令倾听成为迷醉,成为加速度,成为那个人生命时间里新的惯性。倾听总是能改变一个旧时间向度,直到又一次倾听到来,专注、迷醉和加速度产生,乐音又展示,一片更新的时间远景。再下一次倾听,再再一次倾听,一曲流水,它卷起的又将是一片怎样的时间波澜呢?……几乎是带着这样的悬疑,那个人的倾听在时间的网路叉道间迷失。然而带着同一个悬疑,他为什么不会是以一生的倾听去走通时间迷宫的那个人?
*
从一重时间到另一重时间,在经历了众多的倾听之后,光阴之城里,已经不再倾听的那个人仍然在倾听。这有如一架已经不再被奋力推向远处的秋千仍然在摆荡,大幅度向上,以同样的幅度回落又掀起,扇开荒芜的小花园地坪上去年的枯叶和散乱的纸屑。那个人体内,以往的倾听建构起一座乐音的迷宫。被乐音改变了向度的时间,时间和时间,则仿佛一块块打碎的镜子,足以攘拼出万花筒无限又近似的图案。他可能因此而又有了倾听之外的倾听,为了从繁复的时间图案里,寻获最为理想的一幅。那会是最为确切的一幅,最为明快和最为简洁的,在一个清澈的乐音里透明。如果,伯牙啊,这乐音仅仅是一声鸟鸣,透过了悬铃木叶片细密的筛选屏,又透过市声吵嚷的噪音封锁线,从一座教堂的陡峭银瓦上快速滑下,又拐进一条螺丝壳弄堂,并且再拐向荒芜的小花园,从一个已难抿缝的窗隙挤进早餐的客堂间,准确地落入一张鼓膜微颤的耳朵,光阴之城里,那个人是否因此完成了倾听的一生?
62.文字谱
一场雨中断一支乐曲
特别当雨已经溢出
乐曲,雨已经成为
乐曲之外那真实的雨
它中断乐曲
天气侵入了奏弄和倾听
一场雨添加
想象的流水
一场雨联接
流水和青空
那雨中不能够继续的左手
停留在弦上
遗忘在弦上,像一只
栖止和丧我的斑鸠
那无名指弯曲
欲跪欲按
在雨之滂沱和喧哗中
收敛,还原,却又仿佛
正召唤更为豪迈的
大雨
斑鸠会抖去
浑身水份
为了让雨意再一次充沛
为了让左手
在雨的交响里
成为不能够中断的奏弄
63.演奏与倾听
在光阴之城里,白昼和黑夜并不是彼此轮回和互相替代的。作为完整一天的两个部份,它们又是共同的部份,相互摄取和彼此交融。不仅在黎明或黄昏,像站在两条大河汇流的三角洲,看出于各自源头的鱼群贸易,交配和混淆,你,有如我,会看见月亮,被从黑暗递交给光明,或者,相反地,又由光明送还给黑暗;甚至夜半或正午,昼夜也会是对方的核心。在正午,有时候,一组星宿会显现,与光阴之城的塔楼和纪念碑构成仿佛被漂白的夜景;而夜半出现在塔楼和纪念碑之间的阳光,不可思议地,会是一个略微黯淡的白昼之镜像。正是在这样的昼夜流转和昼夜渗透里,又如同春分和秋分的昼夜平分,一个被称为音乐的场合,由演奏和倾听共同构成了。
*
在演奏深处,如同在黑暗深处,在正欲把素琴弹拨的那个人深处,一种控制力无以名之,要由你来命名。而在你,伯牙啊,还没有将它命名之时,倾听已经令演奏开始了。倾听在演奏里,如众人频繁的日常生活在光阴之城里,成为这城市的使命和目的;倾听又有如一粒注入子宫的精子,几乎能诞生演奏的新生命;但倾听更可能是一次演奏的死亡方面,像新生命上空必然的鬼魂,总是降临在光阴之城夜半一线黯淡的阳光里,却会因天鸡的一声啼鸣而悄然隐去。无以名之的仍未能名之。要是能够从倾听深处为那种莫名的控制力命名,那么,我,钟子期,在其中相遇的又会是演奏。演奏也分明是倾听之诞生、生活和死亡,是光阴之城正午的黑暗。
*
当你把倾听从演奏中分离,那么,钟子期,会有一个异于原先倾听的倾听,再次从演奏深处诞生。这有如一座光阴之城的变数之城,沉浸在永无夜晚的白昼,那里也总会有按时的睡眠,睡眠里一连串反复的梦境,以及得以在梦境里断续的另一种夜晚。不假于自身之外的演奏之倾听,是演奏的一个绝对控制力,终于要被我命名为灵魂。不同于那个从演奏之外注入演奏的倾听之鬼魂,它是演奏在自我成长中自发的神启,是白日梦中黑色的觉醒。几乎是由于相同的觉醒,一个把演奏分离出去的倾听也获得了自己的灵魂。在不假于演奏的倾听内部,你又能从寂静里听取怎样的造化之演奏,怎样的天籁,怎样令倾听不再的音乐。对于我,伯牙,它们仍然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