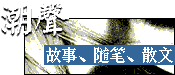我的日常习惯是晚睡迟起,大多数夜晚,总要躺在床上读书到午夜,直到书上的字迹模糊不清才仰身睡去,我是一个爱睡懒觉的人。我也知道这样的生活习惯很不健康,却屡教不改,不可救药。后来,由于工作环境的改变,我身不由己,必须在早晨六点起床,才能百分之百地做到准时上班。时间一长,倒也渐渐适应了早睡早起。不过在周末,还是起床较迟,睡懒觉的习惯还残存着一点影响,可见生物进化是不容易的。这是一个星期六,我的起床时间是9点。洗漱之后,我赶紧骑一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回到家又连忙把两条鲫鱼剖洗干净,削掉莴苣的皮,又拿过一个塑料盆将田螺养在清水里。同时,也整理好顺便买来准备明天吃的菜,用保鲜纸包起来放入冰箱冷藏。接下来,泡上一杯茶,稍事休息,就开始一边开动电饭锅煮米饭,一边操起菜刀在鲫鱼背上划好规则的刀痕,以便烹饪的时候让佐料透进整条鱼里,又把莴苣切成一些不规则的小块几何体。随后就起油锅炒菜。等到一切就绪,已经是11点。整个上午,简直是一种战争状态。在家庭生活中,做饭是一个类似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没有当初恋爱时候所想那么浪漫,不管有多大本事,也无法把俗事搞得充满情趣。
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是那种在夜晚写作的作家,夜深人静中,王小波调动全部智慧,写出那些趣味无穷的小说。一条鞭子抽在身上,没有疼痛,而是上半身腾空飞起再掉下来的感觉,唯有王小波能够想到,大概也只有在深夜才会出现这样的奇想。我妄自以为王小波思考清醒的随笔,那个《我的精神家园》应该是白天的产物。王小波是不修边幅的人,从他头发蓬松的照片上,可以略知一二。他是生活简朴的人,符合生活向低水平看齐的标准。我不禁要想,他是如何在家里做饭,他家中的厨房有没有煤气灶、锅瓢碗筷之类俗物。但是,据说他和夫人李银河,最大的奢侈是经常不在家里吃饭,而是上餐馆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固定有一个餐馆,要是有的话,那个餐馆的老板,倒是可以写点王小波印象记一类文章,更进一步还可大做特做广告,或者干脆称为“小波大酒店”也是可能的。一个著名作家吃过饭的餐馆,是属于精神文明含量丰富的场所,年代一久常常可让人看作是一种文化。
有人访问日本回来,说去过一家别具一格的餐馆,那里仅有一张餐桌,老板是作家之类文化人,不接待一般散客,必须提前订桌。据说在预订时间上,得有一年以上提前量,连2000年某月某日的宴席也已订出。可想而知,去那里就餐,客人仅有一桌,绝无旁人打扰,感觉上已近似于家庭宴会。如果席间再来点烘托气氛的小节目,可说是妙不可言。当然此类餐馆,应属高雅而奢华一类,不是日常可去之处。王小波是不大会经常光顾的,消费总得计算一下自己口袋里的金钱,况且还得看看实际需要。美国作家海明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曾在法国巴黎打天下,为写作拚命。他写了一篇很有魅力的小说《流动的宴会》,里面谈到巴黎一些文人聚会的小餐馆,虽然不至于让人流口水,但却使人从内心非常向往。不过这些喝酒、喝饮料、吃面包的地方,称作“咖啡馆”,是文人们休息、培养灵感的地方。
海明威这样写道:“这是一家令人愉快的咖啡馆,温暖洁净,备感亲切。我把旧雨衣晾到衣架上,把饱经风霜的旧毡帽放在板凳上方的帽架上,要了一份牛奶咖啡。服务员送来了牛奶咖啡,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一支笔,开始写起来。我写的是在密歇根生活的片断,因为天气寒冷,风狂雨虐,我便把这种天气写了进了小说。……笔下的小伙子们在畅饮,这使我感到自己也渴了,因此,我要了一份圣·詹姆士酒。冷天喝这种酒挺好。我继续写下去,自我感觉良好,感到清醇的酒温暖了全身,也温暖了我的精神。……我合上完稿的笔记本,把它放进里面的口袋,然后向服务员要了一打葡萄牙出产的牡蛎和店里现有的半瓶不甜的白葡萄酒。……我吃着海味很浓、带有淡淡金属味的牡蛎,冰凉的白葡萄酒去除了金属味,而留下了可口的海味和多汁的肉;我用清澈的酒将每块壳里吸出的肉汁送下胃,这时,那种空虚之情烟消云散,而快乐之感油然而生,我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计划。”海明威写得有滋有味,可以读出良好的食欲来。国外的咖啡馆好象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的文化环境里,咖啡馆过去曾经是电影里充满接头暗号的地方,现在又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谈情说爱甚至是调情的场所。进去一落坐不免就感到有些异样。在那种暗淡的灯光下,神秘而紧张,要说写作灵感等等,恐怕就算是海明威坐在那里,也是摸不出头绪了。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民族特色,照样让洋人们羡慕不已,比如象北京的“老舍茶馆”这种中国式的咖啡馆,大模大样坐在厅堂上听戏、品茶,又是另一种民俗文化了。
在北京地坛旁边,我去过一座北京特有的庭院式仿古建筑,叫“坛根院食坊”,是色彩明快的民间生活的一部份,属于热闹的大众生活。店内外雕梁画栋,气势古朴。大厅宽敞明亮,清一色的八仙桌、长条凳。里边有一游廊,内有风格各异的单间。单间里还有热炕头,墙上裱了一层旧报纸,悬挂着几串玉米棒、红辣椒。再现了老北京胡同的风情。餐厅里还设了一个戏台,每晚都有老北京风格的文艺节目上演,烘托气氛。菜式也全是老北京寻常百姓津津乐道的,有市井街头的各色小吃和民间百姓的四季家常菜,当然也有一些紫禁城宫廷美点、名贵御膳供你选择。还没到食坊,老远就看见了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一水儿的身穿中式对襟布衣褂,灯笼裤,足蹬老头乐布鞋,肩搭白毛巾,一幅老北京店小二扮相的小伙子,早就远远地在躬候,拉着《骆驼祥子》里的旧式洋车载上你,利落地迎入店里。到门口,笑容可掬的老堂官一声“来客人了”,以老北京茶楼酒肆的特有方式把你接进门去。服务员殷勤地擦桌掸凳,落座后,送上浓浓的盖碗茶,容你慢慢点菜。其间,戏台上,相声、京剧、评书、大鼓、杂技风味十足。品着盖碗茶,喝着老陈酒,尝着京味小吃,赏着老北京曲艺节目。既饱口福,又欣赏了老北京文化,巧妙融和,回味无穷。整个氛围的喧哗、生动,只有我在电影上所见的美国西部牛仔式酒吧尚可媲美。不失为一种独特的体会,但与海明威所写到的“咖啡馆”小餐馆对照,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情调。
相反,还是我们周围的许多小餐馆,倒比较接近于海明威所说。我曾经到过北方一座城市,在一条有着众多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的大街上,我和一位朋友钻在书堆里淘书,每人手里都提了一大捆厚厚的书,一个上午下来,不知不觉,疲倦就越过找到好书的兴奋进入我们的身体,精神一松懈,顿觉又渴又累。走出书店,抬头只见对面有一小餐馆,招牌只有两个字“爆肚”。冲着这个“爆”字,我们闯了进去,坐在简单的折叠式餐桌上,要了四菜一汤和啤酒,实实惠惠地吃了一顿。店里顾客不多,显得十分安静,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翻阅刚买的书,过瘾的感觉让人难忘。结帐时一看,总共还不到三十元。其实,许多小餐馆都有一些独到之处,也能吸引一些回头的客人,令你愿意反复光顾。还有一次,我和两位同事在宁波出差,因为急于回家,出发就已近傍晚,途经杭州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都该播结束了。我们把车驶入小巷,随便找了一家小餐馆,急急地点菜吃饭,阴差阳错地点上了八宝鸭这种土风大菜,端上来一尝,不禁连连叫绝,美味少有,顷刻间一扫而光,价钱也还算公道。后来还有几次机会,我多次重返这家餐馆去吃八宝鸭,就为痛快一下。类似的餐馆,犹如民间潜藏的世外高人,时不时会显露一手绝技,只是一介布衣,不那么耀眼罢了。在从浙江到上海的318线国道上,经过江苏境内的小镇芦墟,公路旁水面开阔,一些汽车司机光顾的小餐馆紧靠河岸排开,店中所卖尽是刚从河里捞出的鲜活水产。我有过一次尝到乡间风味的经验,一碗红烧鲶鱼,使我等俗人如尝仙界佳肴。
自古到今,形形色色的小餐馆有着无限生命力,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在要紧处,也有种种描述,常有一斤牛肉、四两花生米、半斤上好烧酒的豪气扑面而来。现在那一座城市没有“大排档”这种广东化的餐馆,可以说是大众消费热点。在勤俭的居家生活中,总也有懒惰的时候,确实不想做饭,往往要去“大排档”、小餐馆满足满足。选一家附近的小餐馆点几个家常菜,消费也是在偶尔为之的能力范围内。有时候,与餐馆老板混得熟了,还有可能得到一个优惠价,那也算意外的快事,让人倍感亲切。在我原来的居所旁边有一家叫“老面馆”,我是老顾客,经常得到一些例外的关照。那是售卖面条、馄饨,同时也可炒些小菜的餐馆,比不得一进门服务员就送上一本漂亮菜单的餐馆。我经常吃的是青菜肉丝面,这青菜肉丝可决不是事先放在大锅里烧好的菜,而是在面条刚入锅时用小锅现炒的,一碗面端上来,青菜碧绿爽清,一顿中饭吃得十分惬意。说来还得感谢店主人掌握火候的那份认真和技术。虽然我没有象海明威那样,坐在餐桌上写过什么文字,而且也不曾在那里悠闲地看书读报,在这种背脊挨背脊的地方,只能全神贯注地狼吞虎咽。自从我搬家以后,已没有机会去“老面馆”,时常要回想起青菜肉丝面。或者,我会找到另外一家小餐馆,与记忆中的小餐馆遥相呼应,也许我还可以带上一本杂志去坐在店堂里,一边翻阅杂志一边等待。在这些日常俗事里,把以往的记忆一件件拿出来看看,碰到运气好总会有所收获。
■〔寄自浙江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