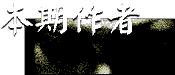盘旋在迷宫之上
--与Siegfried Shiva的访谈
......Couldn't find the exit, Daedalus made wax wings so that
they could both fly out the labyrinth......
Sieg:我只顾一味写小说,写出来后才发现原来还有个归类问题,这一点很是让我窘迫。由于我孤陋寡闻,所以我不知我这种写作归属于何种流派,我暂且把它命名为结构写作,在这里,结构这词可以在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里找到差不多的定义,或者,直接把列维.斯特劳斯那里的结构人类里的结构概念挪移过来,也能表达个差不离吧。在中国文化图景里,我想来想去,在文学方面能接近的,也就只有王小波了。其他方面我想可能是刘小枫吧。不过,我怀疑我的小说是没法镶嵌进中国文学里的,虽然我的一些古怪想法能在一些青年中找到共识,自然,他们基本上是欧化倾向的,自由主义的,有诗人气质的。
舒伊:你觉得你走的路子,近似或关联哪派传统或者大家?
Sieg:大概法国新寓言派里的图尔尼埃式的写法是与我关系较密切的吧,或者说,我写《迷宫》时,心里总想着的就是:超过他,超过他,死活也要超过他。:)
舒伊:你的作品有个很鲜明的特征,那便是极具美术感。能否介绍一下你从事美术的简历,及它怎样融进你的写作。
Sieg:天哪,这怎么回答?文章本天成哪。要我把这梳理出来,那准是隔着月球给人搭脉--有一拨没一拨了。我写东东的时候,想象中的景象会自动出现的,它们不必很清晰地展露每个细节,只要达到梦境里的那种水平就可以了。可能以前长时练习过素描水粉油画使我对具象的远近形状明暗颜色等等有了更为刻骨的观察能力吧。
舒伊:你的作品里多处提及音乐,藉此你意欲表明或传递什么?
Sieg:音乐这事我是这么想的:叔本华当年说:一切艺术向往音乐的形式,那时我不懂任何乐理知识,以为音乐是一切艺术的终极呢,后来稍微懂了些后,才明白原来这话的重点是落在形式上,我现在体悟最深的就是这里面的复调关系。再说,瓦格纳的乐剧我是一直欣赏的,这次写作,里面或明或暗几乎已动用了所有瓦格纳的作品了。而我在写几处特别需要激情(比如那后来投靠日方的中国青年内心焦虑的时刻)的地方,就是在瓦格纳的背景音乐下写就的。
舒伊:你的作品采用了不连贯的,可是重复循环的叙事体。多重的叙事角度,这点你做得很Faulkner。明显地,你喜欢使用第一人称,可是因为第一人称叙事来得更为直截,主观,触及个人内心深处?更具感染力?
Sieg:第一人称叙述有个好处,它一方面可以避免全能叙述这种伪上帝式的代言形式,另一方面也能给你一个限定的视界,事实上有些段落即使我用要离这个第三人称进行叙述时,仍然是把视界尽量集中在他的眼睛所限定的范围里的。而且,通过这个“我”的工具,我可以直接切换到意识领域,再从意识领域里转出去,转到现世层面上去,作为一个转换点,它很适合,并且,暗合了我整部小说要求的“我”是一个道具这样的想法。
福克纳这个天才真的很影响我,我还曾以为自己一辈子脱不了他的阴影了呢,当我看完《喧哗与骚动》后。不过还好,在陆续看完《圣殿》、《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八月之光》后,我知道他的水平也就这么些了。
现在的对手是图尔尼埃(这名字又出现了),这个法国人书写得不多,可一本《桤木王》让我读完后马上就去翻看他生于何时,瞧瞧他还有几年好活还有多少余地可以发展(这行为与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嗯,还好现在他是个老头子了,看来我还有机会超过他。
舒伊:《迷宫》是一幅巨大的拼图。这是我初读后的第一印象。现在我重读下来,还是同样认为。我看过你的油画,你似乎对毕加索式拼图情有独钟,或绘画,或写作。
Sieg:也许给你的印象是拼图,但我实际上是想努力让它成为一个立体写作的结构,若算是拼图的话,也应是立体拼图吧?
我是想给它承载住一些逻辑的悖论,一些剜除时间后的空间状态,一些把空间打碎后的叙述方式,以及其他一些我难以说清楚的东西。是不是成功了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就是制作者,身在此山中了。
舒伊:对时间的单向性和经验性的再度破除。作品中出现大量关于时间的往返,以及相对应的空间错位。
Sieg:穿越时间并没有什么稀奇,很多科幻电影及科幻小说都这么尝试过了,自然博尔赫斯及三岛由纪夫他们也都玩过,但是,他们玩的时候,还是遵守时间的顺序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是重排了时间顺序,但没有重排时间顺序的标签,因为他们认为时间还是如同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先验的。
转到胡塞尔的结构里来,我们假设我这个载体是存在的,那么,重新考察时间的顺序性,我们会发现除了经验的时间性外,还有另外一种顺序在那里等我们去标签化为时间,海德格尔想了半天,想出个向死结构来描述,后来的伽达默尔则进一步为海德格尔的这个结构里的阐述方式(即释义学循环)拼了老命辩护了一番,他们沿着印欧分歧点后的那一条越走越远,却从未想过,南下的一支雅利安人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走在分歧点后的这一条的--在这一条上,时间和空间感觉或都不是先验而是经验的,甚而都是妄识,是法执,然后,他们把胡塞尔的考察基点:主体(或主体际性)也抓到经验里去,认为那也是妄识,是我执。破此两执后,他们认为将迎来涅磐。--涅磐到底怎样叙述这很困难,在我看来这困难不亚于言说上帝。
看了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让我在对中土佛教更加蔑视和鄙薄的时候,却对佛教的原典尤其是陈那和法称他们更是敬仰:真正的智慧向来是不必在乎悲悯的,因为悲悯者是无暇智慧的:我没见耶稣写过一篇好文章,我也没见乔达摩推理出一个命题。而当悲悯所指称的背后是不可证的时候,我更是如此了,虽然我知道,这是一种很不好的情绪,一种歧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达利说他宁愿有等级,也不要平等,唉,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才是即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的呢?可以说,是《佛教逻辑》这本书让我坚定了自己的这种破除时空框架的写法,甚至,我还故意在叙述中借用电影镜头那种化进化出的手法,或是音乐里那种钢琴键盘与管弦乐队呼应的手法,或是绘画中那些在视觉上没有矛盾但在推理上发生矛盾的接的手法,总之尽量把许多不同时空下的情或意识给融在了一起,使文本的排列顺序不再根据日常的时空顺序进行。
舒伊:一些后现代主义文字游戏。拼版:上下左右辐射镜像文字;将哲学家名对应排列成星宿图等。
Sieg:这些都是灵感而非结构中的必须,当然我知道结构需要它们这些点睛的要素来撑一把。
舒伊:对爱情的一种新定义:To delove is to love。(我也可以玩玩造新词,你说对不?:P)
Sieg:当然,这个词造得很好,就和德文里Ent-这前缀也造了不少代表“去除”概念的词一样。以前小时候看通俗作品,见一作者写“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爱你”,觉得很佩服(怎么样,小时候我够傻吧?:)),因为这话在逻辑上明明不对吗,怎么我就能看懂它要表达的意思呢?当时小,也钻研不透,现在从赫拉克利特他们的角度来看这问题,觉得这实在是好玩。
舒伊:在《迷宫》里你写到上帝,你写他忽彼忽此的萍踪,你写他开口发话,你甚至写对上帝的“第一次”祈祷。既然祈祷,也就是暗许其间有上帝,虽然你犹豫不肯承认他的存在,进而否定他。请问你怎样看上帝?你试图在你作品显示上帝什么,人与上帝之间怎样的关系?
Sieg:首先要申明的是:里面开口的是圣子耶稣,不是圣父耶和华,所以说是上帝开口这并不合适,因为我一直很小心这点:即一不小心把书中人写成了上帝的伪代言人。但由于耶稣有人性,所以我直接让它开口,还不至于打破神人之间的天然界限。
关于上帝的问题:我就是沉在科学家的上帝、哲学家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里钻不出来了,要我说出个我的立场,可我又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说出呢。弄不好,一个文学家的上帝倒翻出来了。:)--添乱。
还是保持沉默吧,我实在无能为力。
舒伊:你认为你的写作是关于哲学胜过关于生活?如此那么你要传达的哲思是什么?能否简短说说?
Sieg:传达哲思的问题:我觉得要能传达,我会在哲学语境里传达,可正是由于我要说的在哲学语境里是说不出的,我才转而用文学语言,真要强说之,那就是尽量接近上帝之类的一个可能有的目标吧。
舒伊:我就知道这次你会烘出些更非常更热火的性描写。从前读你的小说《屋子》,多多少少从你身上看到一点直陈无讳的D. H. Lawrence。较之《屋子》,这次又读到一些新的:屈原着女装,要离失精阳。Queer理论的某种引进?
Sieg:同性恋理论我读得不多,但我猜想同性恋是个很粗糙的概念,其实其下的个案表征是各式各样的,甚至有些是超出同性恋这个概念的。《屋子》里只是性别的对峙,最后通过个体的湮灭来消解矛盾;这回我准备好了,就让它们在一个共同的个体里发生对撞,最后同归于尽好了:本来它们就是从一个个体来的,当再回一个个体中去。--无论是在肉身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
很抱歉,与其说是劳伦斯的作品,还不如说是台湾和日本的色情文学给我的影响更大。那些作者的叙述是远离道德概念的,这样就能达到一种叙述的纯粹,我很认同这一点:当艺术一脚踹开道德这个老处女后,它将起飞。
舒伊:你似乎企图勾销所有界限,甚至两性间的界限。你难道不认为这些界限都是确凿存在,无法抹煞的么?
Sieg:勾销障碍的问题:其他的说起来忒烦,单说性这一事,巧的是这次我到北京,刚买到一本李银河译的关于性别性取向错位化模糊化方面的书,即是关于Queer理论的,你那里性文化比这里发达,应该听说过这个比gay或lesbian理论更进一步的东东,我想我的一些想法,也许是暗合这个理论的。
舒伊:你一定知道这本《迷宫》极具要求,理解起来可能会有艰难。你创造了一个超自然的绝对主观的玄妙世界,一个浮满了能指的系统。不同断面的结构并解构,迁移的场景,诡变的时间和人物,多重幻视的角度。要将《迷宫》看仔细些,得需要具备一些关于哲学、文学理论、心理学、语言学、历史等等多元的系统知识。要想完全看懂得花时间。《迷宫》这种博学性是在建议它的读者必须是学者。可想而知这样会减少你可能的读者群。想想当年的Joyce,Pound,Williams,Faulkner。这些可是你写作的初衷?
Sieg:本来就没打算让笨伯来看,不是我不想深入浅出,实在是因为:假设深入浅出这种功夫是存在的,那么我就是没这份能力;假设深入浅出这种功夫是不存在的,那我何必为一个笨伯们没词批评你时便常用的伪概念而努力呢?戴文坡认为博学小说没必要让读者看懂所有的内容,他的小说虽然很不好看,象没什么水份的柑橘一般,但他这主张我倒是赞同的。
我以为真正的文学是只管自己跳舞的(要离的妻子好象很懂这一点呢),看得懂的人自己会跟上舞步,看不懂的人就让他们去,如果为了照顾大多数而牺牲小部分,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数量不是衡量总体幸福的标志,至少这种公平只是一个断言而非一个普适公理。那么,当有很多人奉行在这个断言下的时候,我自当为少数人服务,这也是强选择下的一种生物多样性的平衡表现么,虽然是发生在文化领域下。
舒伊:你说你的作品恐怕不会为大多数所理解,你只为那一少数舞蹈。有没有可能你所说的是本不该说的而你强说了的缘故?如果是这样,你知道Wittgenstein的话:凡能言者,我们都能言之历历;凡不能言者,我们都应该保持沉默。如果你是在强说不能言者,或许你也应该保持沉默?
Sieg:不是,主要是由于写作手法太怪,意象过于奇诡,一般人看看寻常小说罢了,没必要到我这里来耗脑子,浪费他们的时间。而且,维特根斯坦又不是文学家,他沉默不语的地方,就是我种植文学语言的田野啊。
舒伊:语言的晦涩问题:我觉得一个作者,不论从事文学或哲学写作,不可用文字困惑或吓唬读者,仅为显示自己高人一级的才智。如果他必须使用某种特别的文字,那么他必须是“有所言”,有真东西说。比如说Heidegger,他不得不生造那些特殊的术语,来说明他的想法和理论,可是即便如此,到今天他还常常因他晦涩的文字而被批评。人们读他的著作是因为他“有所言”,而不是因为他的文字多么异怪。我提到Alan Sokal,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事件对上述很能说明。Sokal发表在“Social Text”上的仿本,证明了那些后现代主义理论不过是些无稽之谈,他们的文本太多用艰难的语言来作假掩饰。
Sieg:老实说海德格尔那套比黑格尔更变本加厉的写法我是反感透顶的,但对同样以晦涩著称的胡塞尔的文本,我却不敢这么不敬:因为后者的晦涩里有凭着理性可以读解出来的东东,但海的就比较少,海的文本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一种先知的言说,甚至是一种小说,但既然他的文本是诗性的,那为什么我不能通过小说来试图走得比荷尔德林(后期的海特欣赏的一位诗人)更远些?但我这次做得很小心,我其实并没有怎么玩弄人名或术语,相反,由于它篇幅较长,这可以使我不必为了效率而损害它的可读性:我可以用耗字较多但更具形象性的各种意象来刻画些什么。只是由于我的一些意象过于用险用诡了,所以当它们和一些纯理性的文字并行乃至交错出现时,会让一般人有头晕目眩的感觉。
我知道能说清楚的,就用清晰的说清楚,但这里有两个困难,一个是:小说能说清楚的和怎么说清楚之间是有区别的;另一个是:小说里能说哲学里不能说清楚的事。对于一,你看下面这个例子:“他紧抿着嘴,严肃地说道。”象这种句子,自然是把一些事情说清楚了,可是你觉得这样的句子有视觉和听觉等知觉上的冲击力吗?根本没有,纯是些日常用语的堆积,平日里都看腻了,还在小说里这么来串门似得占地方,不是垃圾又是什么?如果这样的垃圾少一点还能起到让文字阅读起来稍稍简单些的可能,可这样的垃圾一多,那么,我的小说和外面那些知名作家写的小说还有什么区别呢?根本就没区别了,都成废纸小说了。他们总是在痴人说梦般地以为大白话能说大道理,是啊,众生皆苦是个大道理,但是,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这些个缺乏描述乐趣的道理,这些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常识性道理,是不配进入小说的:真正的小说,载的是有描述乐趣的道理,而我所看到的描述乐趣,几乎全是建立在复杂的和谐上的。
至于苏卡尔事件,我以为他只是构造了一个不和谐的复杂文本,但他不能由此推断后现代文本是假学术,因为后现代文本里有部分是复杂和谐的,所以苏卡尔事件在实质上我以为并不能颠覆整个后现代文本资源。相反,从他写的一些对唯心论批评的文章看来,他也弱智得让我啼笑皆非:他说你们如果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因心而起的相,那你从窗口跳下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瞧他那得意劲,都赶上文革那批革命小将了。这笨蛋自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现象世界的一切都是在不可证实的领域里的,他犯了个领域前设误置的错误还洋洋得意,可见此人哲学素养之差,差得让我不想再看他的任何作品。
而另一个关于小说里能说哲学不能说清楚的事,更是由于我认可了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梯子比喻后所做的努力。为什么小说能说得更多呢?因为在这里逻辑是不起作用的,但象征以其模糊而恍惚的能力在理性层面之外起了卓绝而有效的作用,但这也需要象征本身能足够的繁复,让各种意象并置叠加前后左右上下来回地纷飞起来,否则,清水光当的意象群将无法让人在沉迷中失去自我进而认同无我,当然,我不认为我的这部小说是在神之言和人之言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但是,这又的确是我站在无神论这一方,向可能有的神的一方所做的一次努力。
舒伊:你说你追求一种脱离生活的写作。你说“脱离生活”,指的是什么?你的小说和生活全然无干?如果与生活无干,那是什么?难道你不觉得你的写作本身便是生活一部分?即便你说你写“脱离生活”,事实上你写“脱离生活”这本身就是你在生活这种生活。
Sieg:脱离生活写作的问题:我是气不过那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狗屁道理而反说的。这道理听起来很有道理:又有谁的小说不是来自生活经验呢?又有哪个作家不把这经验提炼一番呢?但是,真要从小说而不是从写小说来看这道理,就会看出毛病:不管是源于还是高出,都是在拿生活在做文本的基始,于是生活就成了牵扯文本的堕力,这样写出的小说,永远只会是贴在地面上象土狗一样的爬行,据说,这些个叫现实主义小说。
然而,摄像机可以比这土狗爬行式写作完成得更出色。
脱离生活写作,并非是要失去参照系统后乱写一气,而是在说,当文本的基本要素排列好后,上一级的要素就可以以这些基本要素为依据继续排列,这样一级一级排列上去,直到把整个文本的结构完全彰显出来。在这个彰显结构的过程中,一切是以文本结构为导向的,生活只是提供某些要素,它不能作为导向资源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小说为人经常垢病的原因:他们看惯土狗是怎么爬的了,看到一只天狗竟敢在空中狂吠,便自然着急了起来。:)
舒伊:你写作时可有筹划?当你打算写文字,对你将写的东西是否有个清晰的轮廓或主意?或者说,你不设计情节,任由你的想像力驾驭你去四面八方,自动式写作?
Sieg:写作时的状态问题:我想我真的是结构先行的,这里的结构,指的是关系的关系,奶奶的怎么说清楚好呢?打个比方吧: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商朝铜器和秦朝铜器的关系,是两种因为其中的要素不同而不同的关系,但是,这两个关系有一点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关系里前一个要素要比后一个出现的早,这个共同的关系,就是关系的关系,即结构。我写小说时,始终在构造一个大悖论结构,这个大悖论结构以各种变体关系出现过好几次了,比较明显的有:要离杀死妻子-出门-大屠杀纪念馆-…-保龄球馆事件-击杀椒丘诉-要离与妻子做爱-要离杀死妻子-出门-…你看,这不是一个简单言语反复,虽然在表面上是这样,实质上,在这里我构造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东东:画面上崇山峻岭,远处有溪流过来,按透视关系它越来越大,到了近处又拐弯远去,逐渐变小,最终它又按透视关系接上源头,于是再次远处有溪流过来,…艾舍尔,呵呵。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结构我也要同时处理的,自然,故事情节总线我也同时考虑着。至于具体的句子乃至情节,好多我是没预先计划的。说实话,写到二十万时,我还不知结果是什么,我永远处于偶然写作中,让灵感尽量不被事先的计划所压制--写不好还可以擦去,可压制着写就彻底没戏看了。
舒伊:你说《屋子》同《迷宫》比,其臭无比,这两篇小说区别在哪里?不会仅是篇幅的问题,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
Sieg:与屋子不同的问题:就是在于屋子虽是个四重奏,好象有些牛逼烘烘超越传统的样子,其实它的叙事结构仍是贴着地面的,所以它仍是一条土狗,大不了这条土狗漂亮些。
舒伊:为什么许多有学识有理解力的读者不能分别作者和作者笔下的角色?而且常常将角色的想法混作作者的观点?比方读过Lolita,读者会想Nabokov对幼女也怀畸爱。Nabokov做的也许是拔下他自己身上一根毫毛,放在高度显微镜下。你的小说《迷宫》里的主角要离,有几分是你自己?
Sieg:对这个问题,本来我很想说,要离和我这个生活中的人没有一点关系,因为这样一个回答是很有面子的,至少它可以按世俗要求来标志你在写作上的成熟,而不至沦落到一些年轻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写完了就没得东东好写了的那种倒霉处境。
但仔细想想,真的没有吗?也许要离身上的气质我是没有的,但难道不是我所向往的吗?更让我惊讶的是,随着写作的推进,我发现自己身心的某个部分逐渐在向要离这个虚拟的形象逼近,我创造他,他影响我,最终虽然我不可能和他合二为一,但他的确使我在有一段时间里强化了我固有的狂傲、好斗、决不妥协等品性。
舒伊:《迷宫》里有段关于屈原的戏,很有味道。你有没有将来写些舞台或电影剧本的打算?
Sieg:嗯,我很想这么做,但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假使我有这方面机遇的话,我会先去看一堆别人的作品,看别人怎么做,然后跟着学。但无论如何,孟京辉式的痞子话剧我是肯定不会去跟的,虽然我的朋友财神白眉他们对他很是欣赏。
舒伊:你对《迷宫》作何感想?
Sieg:本来要写30万的,但没到就结束了(26万多),这可以说明什么呢?
1.有可能我在总体规模的设计上不够精确;
2.有可能这个文本结构先天就只能容下这些字数;
3.有可能南京大屠杀死的人没有到3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