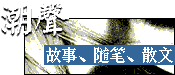父亲从老家来,谈起故乡的人和事,告诉我:隔壁胡伯到天津儿子们那里去了。老房子和准备盖新房的砂石都已卖掉,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和父亲都很感慨。在我的印象里,胡伯曾经是一个非常热爱土地,依恋土地,孜孜不倦地侍弄土地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对土地的热爱几乎达到了贪婪地占为已有的地步,使得他因此常常与邻里关系紧张。如今,他离开了那片曾经为他养育了儿女及家人的土地,离开了有劳作的艰辛,收获的喜悦,生存的快乐的土地,与他的儿子们汇入了茫茫人海的城市。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全新的环境里开始他的晚年生活,他会习惯吗?
胡伯中等身材,精瘦、黝黑,两肩爱习惯性地左耸右耸。从我记事起,胡伯就与我家相邻而居。那时,两家挨得太近,常常因为春天栽树,秋天扎篱笆一些与两家地界有关的很敏感的事而发生争吵。而每当胡伯在吵嚷中,两肩就耸得更加厉害。从母亲与胡伯一家人的吵嚷中,我知道了胡伯不是本地人。
胡伯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他刚满周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挑着一担箩筐中的他和他的姐姐,逃荒躲难,讨米要饭来到了我的祖辈们生活的这个小村。在这个小村,胡伯的父亲找到了一份给一户大地主做杂役的差事,并在地主的作坊里栖下身来。后来,胡伯的父母又主动地将他的姐姐与这户地主的族人联姻,因而能够在这家族人的土地上,也就是我家隔壁的空地上暂时地搭起了一个小小的茅草房。解放后,我们这个小村也一样地瓜分了地主的家产。胡伯一家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一夜之间由穷无所依变成了这块土地上名符其实的主人。并由此与我家相邻。翻了身的胡伯对土地的珍惜,就象一个无人搭理的乞丐好不容易得到一枚硬币一样,是如此地爱不释手,是如此地喜笑颜开。他肯定在内心发过誓,要用勤劳的双手来珍爱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要在土地上耕种希望和未来。
我家前面有条公路,后面有条小河,村里人沿路而居,临河宿饮。与公路和小河相接的一块不大的土地,都让勤劳的村民开垦出来作了自留地。
小的时侯,我最记得胡伯家门前的菜地里,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尤其夏秋时节,在那片菜畦里,地面上藤牵藤,根连根地长满既能消暑解渴、又能做咸菜的绿色瓜果;瓜果地旁边成块成块地生长着红绿交错的辣椒、西红柿,连小枝杆都压弯下来;每块地的沟边,还间种上玉米、高粱。玉米杆、高粱架上爬满了绿色的豆角秧,挂满了长长的豇豆条。隔几天,他家总能从地里摘下一菜篮子五颜六色的蔬菜瓜果。有时,胡伯也让家人给站在旁边围看的邻居孩子们解馋。即使在冬春青黄不接的季节,他家也能从菜地的地窑里挖出埋藏的甘蔗,或者从地里扛回如小猪一样大的粉扑扑的冬瓜。
胡伯家的屋后,紧对着他家后门是一条通向河边的小路。路的两边种上了各种树木,高大挺拔。紧靠房子,种了两棵酸梅树,枝繁叶茂,酸梅树的中间是两棵很大的桅子花树。再往河边去,在大树的阳光地带,种上了小黄花树,小木棉花树。河埠两边,还有芦苇,端午节前后,青翠的竹叶婷婷玉立,倒映在清澈的水中,如纯朴的农家少女,清秀、美丽。每到一个季节,他家都有各种花、果,很令人羡慕。酸梅子熟了,胡伯会教家人摘打下来,给隔壁的小孩们你家一碗、他家一瓢地送去。桅子花开了,也摘下送给邻里的姑娘。我那时就常常希望我家的后院里也种上一棵花树、果树的。
胡伯家的篱笆墙也与其他邻人不一样。邻居们的房前屋后,也栽种了各种树木、菜蔬。但大多数人家的菜地不如他家品种繁多,丰富多采。种的树也是一些杨、槐、楝、柳等土树。有的人家还任由杂草丛生,没有什么树木。顶多只能捡些树枝,扫些树叶当柴烧。因此,邻里之间也就只栽上一种称之为冬青树的灌木丛,作象征性区别。而胡伯家的篱笆墙不仅栽着冬青树,还在冬青树中间插上一些干竹子,扎得严严实实。有些调皮的孩子想到他家地里偷摘花果,就从没得呈过。而且,每年都要重新扎一次。每次扎篱笆,都要向外扩展。靠我家这边扩展时,就会常常与我的母亲发生争执。我那时记得,他家每次扩展一点,母亲就会拿着铁锹挖掉,总是在为“寸土”争吵。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母亲总要给他讲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父亲就会生气地说:“一点见识也没有。”母亲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一个讨米要饭的,一担挑着来的,还这样霸占人家的地方。”但父亲终于有一次忍不住,拿出梯子,爬上胡伯紧靠我家墙壁栽的一棵树上,砍下了遮住我家窗户的许多小树枝。
胡伯很忌讳村里人把他当外地人看。他曾耸着两肩与人辩解:“我的孩子都快长大成人了,我家在这里也有几辈的人了。”然而,人的观念的转变有时却是如此地固执。就象我的母亲,并没见过流浪中的胡伯的父母。她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这点传闻,却使她总在潜意识里要把胡伯当外人。而胡伯又顽强地努力地要把自己融进这片土地。
大人的争吵并不影响孩子的情绪。胡伯家有六个孩子,与我家姊妹相差都不大。我们常常等大人们吵过不久,就玩到了一起。而天性善良的我的父母和胡伯对孩子总是很友善。因为孩子们的无意间的穿针引线,大人们又很快融解了往日的矛盾。但胡伯却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地操持他的房前屋后的那片土地。只要一有空闲,胡伯就在菜地里翻土、捡沟,或者吆喝家人孩子掐枝、打叶。有时,他就拿一把铁锹,在后院的树林里,培土、帮台。很少见他闲着。
每年农闲或者春节前,胡伯还组织家里人从小河那边的荒地里,挑土填充门前的坝子和屋后的土台,每次都要专程挑上两三天。因此,他家门前总是最高、最宽、最平整。小孩们都爱在他家门前玩耍、游戏。
胡伯是那样地执着于自己的小家,也的确如父亲讲得那样,没有见过世面。他只去过一次城里,那是因为他的一个小我三岁的儿子犯小儿麻痹,他带孩子到城里看病,在城市的水泥地上睡过夜。孩子的病也始终没能看好,由此终生站立不起来。在他的内心,一定既自卑又无奈地憎恨过城市。后来,他有个亲戚在天津工作,想让他的小女儿去帮忙照看小孩,并许诺等孩子上学后,给他的女儿安排工作,帮助成家。他坚决地摇头,硬是没有答应。
胡伯对城市印象就象村里人对他一样,是如此地难以改变。多年后,当人们已经习惯或者感到重提那些旧事毫无意义的时候,胡伯的思想也开始了悄悄地蜕变。
我对胡伯并无爱憎情感,但有一事却使我印象很深。那是恢复高考制度后不久,我被唯一面向全县招生的县重点中学录取。在父母送我搭乘交通车的公路上,胡伯赶来送我伍元钱。耸着两肩,说了许多祝福的话。那时,一角钱就能吃一餐饭,伍元钱对胡伯来说,也够他积攒的。当时,我和父母都非常感动。母亲对这事还念叨了好多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从外地回来,发现他家有了些许的变化。桅子花、酸梅树没有了,大树已放掉,又栽上了挺直的水杉,篱笆墙也只稀稀疏疏地长着冬青树。这时,他的女儿们已出嫁,大儿子也结了婚。并且,他的大儿子去了天津,投奔当年的亲戚。几经周折,在城里找到了打工的活计,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打工族队伍。不久,大儿子一家人也去了城里,留下一个孙子由胡伯照看,在老家读书。
胡伯自从大儿子结婚后,就把这套老房子给了他,自己到小河那边的责任地里,搭起了土屋,又置备了砂石、水泥板,准备给小儿子盖房并住在一起。再后来,听说小儿子也去了天津。走上了他哥的路,在城市开始了打工的生涯。这时,村里陆陆续续地有年轻人外出打工,也断断续续地带回许多新的信息。胡伯因为孙子的缘故,儿子经常有书信回来,并向他介绍他们的情况和城市的见闻。胡伯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新的潜移默化的知识与认识。这年底,大儿子、儿媳回来,从头到脚,已经彻底地变成了城里人的模样。就象电视中见到的人一样。他们要把孩子接到城里去,也流露出此生不再回来的愿望。
胡伯第二次到城里,是到天津看儿子们。回来后,他就告诉村里人,他要到城里去。不久,他就卖掉了房子、树木和土地,带着他的家人,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片给他无限欢乐、希望、梦想的土地。
走进城市的胡伯,他会象我一样地想念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吗?我想,会的。那一片土地,一定会令他魂牵梦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