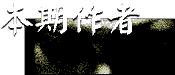死亡是不可能的事(小说)
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县城,是我刚成了寡妇的母亲带我去的。应该是八岁,因
为我的第一个父亲是在我八岁时死的。那是一个晴朗温暖的冬日,我母亲带我穿过一条
污水河边的石子街道,来到香喷喷的百货大楼。我让母亲给我买了一块手帕,上面印着
一只彩色的公鸡。后来,手帕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到。
那家商店还在,当然是洋气得多了。我经过这家商店外前去一个高中同学家,突然
想起我初中时的班主任,我记得他就住在这家商店对面三楼,他就在另一条街工作。
现在是古历五月底,上午的街道显得阴凉,街角几十年如一日的水果摊熟悉的气味
使我想起他。
一切都还在,班主任也还在,他不可能不在,只是那么多年来我忘了他而已,他每
天好几次经过这儿,只是我没看见而已。
我外婆今年九十多了,去年也九十多了,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是这个样子。我所
有的亲戚都盼她死,已经盼了十几年了。去年正月我去看她,纯净的阳光照在她的脸
上,她散发着健康的微笑。我说:
外婆还可以活十二年。同行的继父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我相信她是永恒的,或者
说,我们谁也别想死在她后面。
她不会死可怎么办?
我奶奶说:要你这么愁干吗?你去买点老鼠药把她药死呢,顺便也给我带一点。
我妈妈说:有什么办法呢,都这么大了,她总会死的。
我爷爷说:长命是长命了一点。
许多盼我外婆死的人都倒先死掉:
我大娘舅放牛时掉到山谷里死掉;
老是骂外婆老不死的二舅妈也已死了好几年了;
大表哥吃农药死了;
二舅和四舅妈我出生前就已死了。
外婆唯一的女婿--我父亲死后,她就把五个娘舅家给她的米省下来给我家,她念
佛经、织鱼网赚来的钱和别人送给她的礼物都给我家。
我奶奶告诉我:后代人早死,寿命就折给了上代人了。
这么多年了,我已从婴孩长成教师,而外婆还是老样子,有时突然想起,真有点不
可思议。她渐渐耳聋、眼花,可牙齿仍可以咬炒豆。她看上去像一段树桩,但脸上的笑
意又有点湿意,像一张画上的伏尔泰。
我在大学毕业前夕老想:每学期回来,总会有些事情发生了,这学期该死谁?外
婆、爷爷还是奶奶?可他们谁也没死,人们都说奶奶命长,她老是吐整脸盆的血。可我
见到她时,比我离开时更健康了。只是我二姐夫的手被锯掉了一只,邻居的阿公死了、
阿妈脚断了,有人离婚了。
阿妈的脚是在村口的庙门前摔断的。邻村一个会替鬼魂说话的人说,是刚死的阿公
把她推倒的,因为她把他生前念来卖钱的“高皇经”拿到庙里去烧掉。那人替阿公的鬼
魂说:我一直跟着她,看她把我的经拿到哪里去,我一直跟到庙里,等她一走出庙,我
就把她推倒了。
跟阿妈不说话的我妈说:她自己也对人说,当时是好像有人从后面推了她一下,你
知道,庙前是平地,她就像一捆柴倒去,骨头就断了,骨头又把脚经戳断了。
奶奶告诉我:另一个会替鬼魂说话的人说,她是被庙里的白马踢倒的,你知道,庙
里的墙上画着一匹白马,是神爷骑的,因为它那天拿到庙里的豆腐不到一斤,只有九
两。阿妈对人说,那天她买的豆腐好像是不到一整斤的。
我更相信第一种说法,因为我觉得阿公还没有死,我相信我会在田野上看到他提着
一篮菜走来,他仍旧每天在楼上念经,他还会像以前一样,拿着一张香烟壳纸,问我一
些冷僻的字--他只要知道大概读音就好了,并不需要它的意思。
好多人已经死了:
那个老是晒太阳的老太婆,老是抽老烟,脸像一颗干枣;
那个老是跟人吵架的老头;
经常给大家讲故事的老头。
我父亲死后,有人说他还在村后的山上见到过他,听说我母亲在楼上也见到过,我
问她却被她一声怒斥。
死亡是层出不穷的:
一个老是喝酒的老头子与媳妇吵架后喝农药死了,那天雪好大,我在离村子四五里
的地方念小学。
一个与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脖子上烂了个大洞死了,从此,村子里不管谁死
了,他老婆总要哭一夜。
去年,一个比我大五岁的男子全身发胖死了。
今年元宵节死了一个老太婆,因为家里一共只有一升米,老头要吃饭,老太婆要吃
稀饭以多吃一餐,结果吵起来,老太婆吃农药死了。
去年,一个比我少两岁的已怀孕的姑娘从外村买来农药,边走边喝,快到家门口时
就已断气了。
一个生过七个女儿一个儿子的老头,因为女儿逃计划生育,他被抓到镇政府打了一
顿,房子又被拆了,他就在还没被拆掉的自家屋脊上吊死了。
而我早就八十多了的爷爷,他见到的死亡就更多了。村子里比他早出生的已死光
了,比他迟出生的也已死了不少了。他老是盼望我们给他打一块全村最好的坟碑,他老
是参加别人的葬礼,因为他最内行,他老是生病,老是埋怨我们不给他医。他老是说:
我知道你们巴不得我早点死,我也早就想死了,可阎罗大王不叫我去我有什么办法
呢?这不是真话,他想:我父亲活了95岁,我大嫂活了99岁,我老亲家比我大十岁
也还在活,或许我能活到120岁,那些没良心的子孙盼望我早点死,我偏偏不死,他
们又不能药死我,那是犯法的。我长命,因为我苦命,我从小在山上风打日头晒,所以
身体健康,我不能听子孙哄,让我别上山,我只有继续上山才会身体健康。十几年前我
就做好了坟,可我还活着,或许我会成为这一带最长命的人。我头发还没全白,小儿子
给我剃头常把我胡子剃掉,我看以后该把它留起来,画上的老寿星都是有很长的胡子
的。
假期里,我是睡在爷爷家的,他住楼下,我住楼上里间,奶奶住楼上外间。一天早
晨,我还在床上,我听见爷爷上楼,奶奶生病后都是他烧饭的,我想他是上楼来取米。
我听他的脚步声在奶奶的床前停了下来,后来我听奶奶说:死都要死了还这样,别人听
到好听啊?然后我听到取米的声音,下到半楼梯时,他停了一下,叹了一声气。
村里的人老是猜测那些老人谁先死,老是猜错后,他们得出结论:眼看就要死了
的,往往不会死,你根本没想到的人却突然死了。
我去看过阿婆,她有点弯曲了,但更加眉清目秀,脑子更加清晰,她告诉我她女儿
村里某人的儿子当小偷,常被人家打死,谁家今年做什么生意赚了好多。她对我说:我
还以为你见不到你奶奶了,一天吐一脸盆的血,死老太婆又逃过这一劫了,只有我老倌
头说没有就没有了。说着就哭了起来。我说:是啊,我以为他肯定要死在你后面的。她
说:哪里来的福气呢?我不要多,阎罗大王只要再给他四五年阳寿我就谢天谢地了,宁
可把我的寿命折一点给他呀,我的囝。我说:阿婆,我觉得他并没有死。她说:你是大
学生也这么说,我女儿不让我说,我一睡去就看到他,他就躺在我边上,可一醒过来就
不见了,想拉也拉不住他。听母亲说,阿婆最不喜欢人家说她快死了,我说:阿婆,我
有点会看相的,你至少还可以活十年,长命一百岁。她说:囝,你不要哄我高兴。我说
:
我跟你那么老的人还开玩笑啊?她转悲为乐,她说:那我还可以吃到你的喜酒呐?
我说:那还用说,你还可以吃到我儿子的喜酒呢。她忽然又哭了起来,她说:老倌头走
了,我活再长都没意思了。
我爷爷已学会了烧饭,这样,万一奶奶死了,他也不愁吃不上饭。自从我断然反对
给他刻全村最大的坟碑后,我爷爷就不理我了。我就对奶奶说:奶奶,爷爷以后如果想
我钞票用的话,叫他对我不要太老三老四。果然,第二天他就给我递烟,并讨好的对我
说:坟碑吗,其实与小毛爹那样也蛮好了,石狮子小一点也不要紧,还是你说得对,死
了就无所谓了,活着时有鱼有肉就行了。我说:还有酒有烟,不过,小毛家的还是太浪
费了。我打量着他的神色,没想道他咧开的嘴里露出两排尽管发黄但齐整的牙齿,这可
比我的牙齿好多了,我想,我可能比他死得早。我这样想很怕,因为好多事情总是与你
担心的一样。我只要一根绳把他一勒就成了,但我那些不肯给他医病的叔叔们可高兴
了,不说把我送到官府去,至少他的丧葬费肯定是我一个人出了,不划算,还是由着他
吧!
他越来越沉默,这让我害怕。他老担心谁又要死了,谁就真的死掉。他梦见一个山
上卖柴人挑着两箩筐人头,走到村外的弯龙桥时,把人头都倒入溪里。第二天,他去赶
集,坐在桥上的石栏杆上抽烟,一辆载满了人的拖拉机快乐地从另一条坡路上驶来,他
看见这辆拖拉机冲下了山谷。他就往回走,他自己念叨:我昨夜就晓得了!
去年冬天,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在路上看见正在溪里洗衣服的老高。我们先是谈我
的学习情况,再是哀叹社会风气,但他劝我不要去插手国家大事,小百姓只要想着怎样
赚点钱好改善自己及家里的生活。最后说到我奶奶,我说:她好几天没吃饭了。面对我
的悲哀之色,他说:傻瓜!老人不会吃饭吗求之不得。我奇怪自己一下子接受了他的观
点。
他的母亲已在床上躺了七年了,而她的丈夫好好的,却在她卧床的第二年死了。我
常常盼望她死掉,这是我把小高当好朋友的体现。可每次见到,她总是又白又嫩,脑子
又清晰,小高倒是越来越瘦了。
死亡是不可能的事,这多令人悲哀啊!就是我也还活着,真不可思议!
我六岁时,从一棵树上掉到石头堆里,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床上。我大姐现在还
记得,他们以为我没用了,好几个钟头才醒过来。我奶奶说:你本来蛮聪明,也蛮可爱
的,这一倒把你的眼睛倒小了,脑子倒木了。我依稀记得这件事,但又仿佛是发生在别
人身上,但我的胡子只有三根,就长在下巴的伤疤上,这条长长的伤疤就是那次事故的
遗迹。
读小学时的一天,我独自在家,我把手指伸进一只电灯碗头,我感到我的手指被咬
了一口,就像被连根拔走的样子。
读中学时,一次回家,我坐的三卡翻进路边的山沟里,我自己从倒过来躺在沟里的
三卡中爬出来,走回家。
去年暑假,我一个人在水库里游泳,我在水底挣扎,已经绝望了,但没想到,我放
弃挣扎,放下脚时,头却已经出来了,我已经在岸边了。
唉!我也是不会死的。看中学时的日记,我怎么在县城读了三年高中?那些荒唐事
都是我做的吗?我真的没有死吗?我真的还活着吗?或许我的肉体在不断发育,而我的
灵魂已经被换过好几次了。
按理说,我该去看看我外婆,她以前对我那么好,她又是那么孤独。但看与不看还
不是一样的吗?她老了,她已看不清是谁站在她面前。再说,现在看与以后看还不是一
样吗?她又不会死。我童年时的小手帕丢了,可我童年时的外婆还在,一切都稍纵即
逝,可我外婆是永恒的。
我外婆没有死,尽管我常忘了她的存在,她是我童年的一个诱人的远方。她活着,
在我洗澡时,在我恋爱时,在我高兴地喝酒时,在我感冒时。她一个人活在只有她一个
人住的旧四合院里。她不会死的,我可以等更空的时候去看她,或者到我退休以后去看
她,反正她是不会死的。我母亲告诉我,外婆准备死后盖的被子已经烂掉又准备起来又
已烂掉,被虫蛀了。
人是不会真的死的,尽管你以为谁快死了,而恰恰是她比你长命。我五年前的那个
暑假爱上了一个来自北方的女生,两个月内通了五十多封信,见了三次面,但后来我把
她忘了。但是在节日前,我按多年前的地址寄去一张明信片,没想到竟然收到她的回
信,上面只写着“你好”,就好像告诉我她还活着,而我总是难以想象她还活着。
同样,那些听说已死掉的人,我也没有把握说他已死了,完全有可能去打工了,等
他想回来时会回来的。他们死还是活,对我也不重要。
我毕业回到家里,正好赶上阿公的第三个七日祭祀,我继父正好牙痛,不能喝酒,
就由我去吃三七宴。酒宴上人们欢声笑语,划拳行令,吃得不亦乐乎,喝了不少酒后,
黑黑的村庄里无处可去,但我又觉得还有什么事没有干,就朝一户人家走去,我记得那
个屁股大大的小姑娘就住在那里。小姑娘先叫了我一声,她一个人坐在黑黑的屋檐下,
家里没开灯,我就坐到她边上。黑乎乎的,我把自己向她挪近一点,能感到她那肥肥的
肉,我的一只手隔着裤子摸着自己的小鸡,我真想跟她那个。我和她聊着村里的死人和
说死人的事,我把手伸向她,但快碰到大腿了又缩回来,按辈份她可是我姑妈,我握住
她的手,她轻轻抽回去,继续跟我聊天。然后她把她的手递过来说:我这只手指甲很
长。我摸了一下说:真的很长。我的酒却已醒了,我的四周也渐渐有了轮廓了,这时有
几个小孩看完了为做七祭放的录像后回来了,我就回到我爷爷家去了。
我现在是明白还有什么事没干了,回到房间里,找到那本黄色小说精彩片段合订
本,就从毕业影集里取出最漂亮的一位女生的照片,就在蚊帐里拼命地手淫,然后把精
液射在这张照片上,精液在上面流动,她仍在微笑,手里捧着几本书,精液也从下往上
流上了学校的图书馆,直流到上面的蓝天,我又让它往回流。
照片上,她只有上半身,远方的她不会因此而怀孕,但她梦中可能会遭到一场莫名
其妙的暴雨袭击。
我觉得阿公一直在远远地跟着我,看着我,但什么也没说。
死亡是不可能的事,而我也将会醒来。
(1996.7.14-15.
于浙江三门叶继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