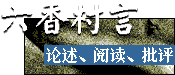西南联大诗人群与新诗的现代性转变
--个案研究与主题学研究
一
中国的白话新诗发展到40年代,其形态与初期的《尝试集》已大相径庭了。这其实与在更宽广的一个背景中,中国新文学经历了大变革之后的平静,渐渐向多个向度分化与探索是同一个过程,其动因从很大程度上说便是文学“现代性”的冲动。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现代性文学在“五四”之前十几年就已发生,而现代文学乃至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是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一部份,其启发性倒不在于对现代性源头的考察,而在于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各种形态的更迭都来自于文学现代性的冲动。本文所要论述的西南联大诗歌在此前的诗歌现代性冲动的基础上,在新的现实背景和文化氛围的激发下,加上西南联大诗人群创造性的工作,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短短五、六年内一下进入了一种成熟阶段。我们很难说此前的现代主义诗歌有多少现代性的冲动,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西南联大的诗歌所具有的现代性冲动是带有质变性质的,对中国新诗来说,它是走向成熟前的最重要的一次冲动。
联大存在的大部份时间里,整个中国都处于抗日战争的氛围中,联大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抗战虽然胜利了,但内战的威胁又起,“两次战争之间”成了战争氛围的一种独特派生状态,此其独特处之一。其二,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缘状态却使得云南在统治者的思想控制上又是相对放松的,这形成了一种极有利于诗人生存的社会环境:战争环境和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使知识分子能切身到感到现实的压力和苦难,而宽松的政治环境又可以让他们相对自由地把内心中的种种焦虑与不满、抗争与思考的状态表达出来;言说的理由和言说的自由同时具备了。在1937到1946年间文化语境中充满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战争文化心理与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很难容纳复杂的思想状态及其晦涩的表达,而这种思想的复杂和混乱恰恰是来源于战争的。这形成了一个极有意味的悖论:文化语境中存在的人被禁止用与这种文化语境本质相关的方式言说。西南联大的语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对这种悖论一定程度上的消解,战争文化心理渗入到西南联大的内部,而意识形态的作用则被联大民主自由的氛围、独立不羁的民间立场大大地屏蔽了,思想的复杂与言说的多义实现了统一,而这正是与现代主义的本质相适应的。无疑,西南联大诗歌的风格也是复合的和多向度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内核,这一内核的出现源于其中国本土的原创性色彩,从本土经验、民族文化心理出发,诗人们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危机意识和焦虑心态。
二
讨论西南联大诗歌与新诗现代性转变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说的诗人就是冯至。曾写出过《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的“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30年代末开始出任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教师,出版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十四行集》(1942年)。
纵观《十四行集》,我们首先感到的就是诗人对自身生命体验的开掘之深。里尔克说:我们应该一生之久,尽可能那么久地去等待,采集真意与精华,最后或许能写出出十行好诗。因为诗并不象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已足够)──诗是经验”。冯至等待了十年的时间,在经历了长久沉默,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是一口气写下了27首十四行诗,用“体验”为这个整体定下了基调。
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这些入诗的事物,渺小而平常,冯至却凭借着敏锐的感觉和深邃的洞察力,发掘了隐含其中的为一般人所忽视的诗味,找到了它们与人生、命运、价值之间的可通约性,哲理思考与广阔的现实世界联为一体。其实,中国古典诗歌或是西方浪漫主义都有一个“花开伤春,叶落悲秋”的诗歌范式,这是一种文化心理积淀,在历时的诗歌中多次出现,当然可以理解。但在这些范式里人们发现的物质性的自然和哲理层面的人生之间的联系,是固定的、习惯性的,多少反映出人们感觉的钝化和想象力的匮乏。冯至却努力地从前人或他人并未发现的角度去揭示自然事物与人生哲理的联系。我想,朱自清称赞冯至是一个“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因为“在日常的境界中体味哲理比从大自然体味哲理更进一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冯至的日常生活当然离不开阅读,从一些人的作品(文学/绘画/音乐)中按自己的方式把握其精神特质,在冯至看来,是极有价值的。他为尤里西斯、歌德、凡高、杜甫、鲁迅、和蔡元培各写了一首诗,以一种向这些人物倾诉的口吻,为他们画了一幅幅思想肖像。冯至从这些人物的某个具体的关联物(作品或言语)入手阐发诗意,向内找寻自己小宇宙中与这些人物的精神特质的共鸣点,向外又升发出对包括时代生活、民族苦难的大宇宙的关怀。在这里,冯至把体验上升到了生命的高度,他的体验不是瞬间的感官体验,而是对一段生命过程或一种生命现象的整体把握,日常经验或是先辈诗人在冯至那里都被视作一段段具体的生命过程,而他写成的诗又是这些生命过程在作者生命中浓缩之后夹杂着主体意志的显现。这些都是他的诗歌现代性的表征。
它们经过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
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
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
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十四行诗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
西方的那座水城,
它是个人世的象征,
千百个寂寞的集体。(五)
冯至因其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与中国传统精神的结合,成为中国诗歌现代性转变的先导,他的诗歌创作成为了西南联大更年轻一辈诗人的直接营养,而与他地位和作用相似,却显出不同的诗歌特质的重要诗人还有一个,就是卞之琳。众所周知,在卞之琳延安之行前后,他的诗歌出现过一个所谓的“现实主义转变”。一般认为,30年代写出过《白螺壳》、《断章》、和《距离的组织》等诗作的卞之琳,抗战之后虽然走出了“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尴尬处境,但诗歌的表现力在《慰劳信集》中却是不及当年了。这种观点有相当的合理之处,对匡正仅以政治思想性评定诗歌的做法大有裨益,但在《慰劳信集》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却被忽视了:第一,卞之琳超越自身的努力的价值;第二,卞之琳诗歌实验性探索本身的价值。卞之琳无疑是30年代诗人中现代主义色彩最浓的一个。唐祈认为“与其说卞之琳是现代派诗人,不如说他是一位为现代而写诗,由现代意识和文化而产生的诗人” 卞之琳较早地意识和把握到了现代人的精神矛盾,把个人内心深处的追求与失落、焦虑与向往等展露得深沉含蓄。从个体气质上讲,卞之琳具有内省式的审美思维方式,善于将冷隽的哲理玄思与深永的诗歌意境结合,使作品富于含蓄性和展延性。这些在1938年前后的作品中都能表现出来,只不过前期作品表现出了从外部世界游离出来的审美价值取向,而后期作品将个人气质体现在了与现实的融合中。以《慰劳信集》(1940年)为代表的诗人西南联大时期的诗作所关注的对象几乎全是与战争有关的人和事,甚至连题目也都是形如“一位夺马的勇士”、“一位刺车的姑娘”、“前方的神枪手”这样“定语+人物中心名词”的结构,可谓是再贴近现实不过了。(袁可嘉把这样的诗作称为“新型政治抒情诗”,用于与时兴的浮夸的英雄腔和标语口号式的抒情诗区别开来)但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现实的人和事后面似乎总有着一只源自作者的清醒的手,这只手用当年“距离的组织”的方法组织着多种相关的质料,防止它们象在传统叙事诗中那样各自在正常逻辑下无休止地展现自己,也不让它们象在英雄口号诗中那样成为一种虚假的热情操纵的傀儡。卞之琳遵循他所发现的事物的内在意蕴和相互关系,组合成一个新逻辑下的整体。诗作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特徵因而就是:按现实中的人所不熟悉的逻辑发觉各种现实质料的独特诗意,然后在作者的新逻辑中展示出它们共同营造的诗美效果,同时又与时代的总体记忆(现实苦难、战争、革命热情)形成深层次的对应和契合。从《修筑飞机场的工人》、《一位政治部主任》、《〈论持久战〉的作者》这些比比皆是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见,作为诗人,卞之琳30、40年代中善于思索、机智幽默等个人气质的延续,也可以看出他面对新的时代,保持自我和超越自我的有机的结合。
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认为西南联大时期卞之琳的诗过份依靠机智,而非诗情。我们知道,虽然30年代,机智是卞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元素,虽时有充满“小聪明”的词句,但诗歌的内在逻辑并不仅停留于形式推演而是深入到事物内部;也就是说,更多的地方是玄思和哲悟在发挥作用而不是机智。这种观点,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合乎事实的地方,但并不完全,况且即便西南联大时期的卞诗真的依靠机智也并不能直接导引出对其价值判断上的贬低或否定。如前所论,《慰劳信集》中,诗人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从一般逻辑转向特殊逻辑看待现实生活、组织现实质料的能力,这其中机智所占比例颇大,有时这种机智是为了提供看待现实事物的一个新角度,
至于事物的本质要么是诗歌形成之后自然而然展现的,要么并不张显,有待读者自己去领悟。比如《实行空室清野的农民》一诗中有这样一段:
谁说忘记了一张小板凳?诗人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描写战争,读到最后一句之前,我们体验的是诗人的机智和幽默,但读完最后一句,一股新增的诗情元素便会在与前几句的对照下显露出来。常有这种诗情的流露才能使机智不会流于乏味或是油滑,反过来说,这也正说明不涉及事物的本质或是内在意蕴的机智在这一阶段的卞诗中,运用得的确较多,不过因此就招致贬低,并不公允。因为一方面,要求诗人面对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作者能够达到比面对个人经验和内心世界更加具有后者诗歌风格的艺术高度的要求本身就不成立,也就是说,不能以卞之琳30年代的诗作为标准来衡量40年代的诗。卞之琳30年代的现代诗与他的时代相比无疑是超前的,以至这些诗作为整体可以视作西南联大现代性诗歌的直接先导。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别说卞之琳没有在30年代的老路上走下去,即便是走下去,客观地讲也很难写出比《距离的组织》、《尺八》更具“现代性”的作品了。相反,正是《慰劳信集》的出现让卞之琳在实现自我突破的同时也在诗歌中反映了现代性转变的诸多特质(现实、象征、玄学),实现了对时代的真正理解。
也罢,让累了的敌人坐坐吧
空着肚子,干着嘴唇皮,
对着砖块封了的门窗,
对着石头堵住了的井口,
想想人,想想家,想想樱花
可以这么说,卞之琳40年代的转变于他自己是一种用带有个人遗存的新方法写作全新题材的尝试,于中国诗歌却有着推进其现代化进程,至少是某一类诗歌向着某一个方向“现代性转变”的作用 (袁可嘉就称推进政治抒情诗现代化为卞之琳几个重大贡献之一)。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卞之琳写作《慰劳信集》的时期正是奥登来中国访问,并写作《战时在中国》27首十四行诗及卞之琳着手对其翻译的时期。奥登一生诗歌风格多变,但在诗歌技巧上始终表现为用松散的口语表达富于机智和暗示的思考,诗歌中常充满着经过深思熟虑而制作出来的奇思妙想,卞诗中新逻辑的构造和诗情的脉冲式出现的风格与《战时在中国》所表现出的十分相似。
三
以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自己的“学生诗人”,是中国诗歌现代性转变的生力军。与冯至、卞之琳这些早就闯荡诗坛的西南联大“教师诗人”相比,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先天优势。20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为他们提供了营养和前车之鉴,特别是冯至、卞之琳等人的作品成为他们直接阅读和仿写的对象。他们在与前辈诗人的对话、交流乃至置疑中不仅看到了中国诗歌现代化显然的死路和潜在的障碍,也反省了自身诗学观念(主要是早期)中的偏颇。这使他们在很短时间内便形成了成熟期的诗歌风格,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具有延续性的诗学观念和诗艺的探索中去。
在这一点上,穆旦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般认为,穆旦的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中最具有前瞻性的,但在其早期(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有过一段时间不长的浪漫主义情结(众所周知穆旦对拜伦、雪莱情有独钟,至死不渝。这与所说的浪漫主义情结不是同一个意思,前者更多的是对个人气质的偏好,而后者指的是对整体浪漫主义诗学观念和诗歌技巧的接受),他曾借着评价艾青诗集《他死在第二次》,指出“我们终于在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和贫血的堆砌辞藻当中,看到了第三条路创试的成功”,这种“第三种抒情道路”的概念他在另一篇早期文论《〈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里加以了确定。他认为卞之琳30年代的作品主要是以机智来写的,但这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有进步意义的。可是在新的环境中,“放逐抒情”就应被理解成放逐“自然风景+牧歌情调”的旧抒情,创造一种以“用理性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为内涵的新的抒情。应该说穆旦的这些观念多少都来源于他自己的良好愿望:其一,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最终走向光明有一种必然的联系,认为鼓舞人们去争取光明最符合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其二,他对机智的排斥来源于对诗人天生就具有一种直观把握力和想象力,不通过思想中介,就可以将诗和现实形成一个感情的大融合的幻想。如果穆旦这里所说的“机智”指的只是我们前文论及卞之琳时说的“小聪明”,那问题也许就不存在了,但他似乎直接指向“玄思”,如艾略特自己所说,“机智”是指“存在于抒情诗温柔美下面的刚劲的合理性” 的话,那么穆旦此时对感情的偏重及现代性因素的缺乏就可见一斑了。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诗学观念和诗歌写作之间具有的差异性,穆旦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渐渐体验到了这种早期观念的不合理之处,有意无意之中对“机智”的运用越来越多,而感情渐渐走向潜层。一个明显的例子,穆旦后来的诗歌要比他写于1939年的颇有新抒情色彩的《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 要成熟优秀得多,穆旦在后来的《五月》等诗中还写出对“火炬行列”进行反讽的诗句,这或许是他自我反思的结果。
穆旦曾在多年之后,带有总结意味地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主要的分歧是:是否要以风花雪月为诗,现代生活能否称为诗歌形像的来源?”这是指诗歌关注对象的现代性转移,它有现代经验摄取和诗学主题开拓两个层面。现代经验的摄取,对处于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年轻诗人来说,不象此时的冯至或卞之琳那样来源于对过去经验的回忆和重新发掘,而是更多地来自于当下的现实。诗人们根据这些现代性经验,提凝出一个又一个颇有意味的诗歌主题,这使诗歌现代性转变有了可以直接承载的精神内涵。
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丰富与人的精神匮乏之间张力的分析思考,工具理性对人主体自主能动性的限制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体独特性的丧失,人的制度化和异化这些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主题早在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形成之前就渗透到里尔克、艾略特这些人的诗歌之中了。工具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科技和工业。与它们相关的经验就是城市和城市生活。由此而形成的诗学主题在西方因工业化的历史悠久,从历史的正题发展到反题,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中国,它的引入就会面临诸如此类的问题:第一,整体上中国诗人乡村生活的集体记忆如何转化;第二,在科技落后,工业不发达的中国,对工业的反思如何克服或说绕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伦理关。西南联大诗人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西方现代经验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穆旦有一首叫《五月》的诗,从文本的意义层面上考虑,这首诗把现实的阴暗用工业产品的极端例子──各种各样的枪指代,把制造社会苦难和个人痛苦的罪魁祸首以社会能源和权力的掌握者来隐喻。用这样一种方法,穆旦使现代工业的主题包含了更深一层的意思:工业社会并非诗人直接批驳的对象,而工业社会意象却被用来揭露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阴暗;冰冷的工业品与人性的对立面、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工业机制与社会的权力机制何其相象!这就绕过了对工业社会本身反思可能具有的伦理上的不合时宜性,而把反思的视角通过象征拓宽到了更广的包括农业社会记忆的范围中了。在语义层面之外,这首诗整体上还具有了一层极富象征性的意味:富有传统诗情画意和明显牧歌情调的段落与充满工业社会意象的段落交叉并置,作为参照,传统的“游子思乡”、“怨妇伤春”、“感怀人生”、“饮酒纵情”这些主题多少带有了反讽的意味,乡村式诗情在与诗歌主段落的对比中就显得单薄而且僵化了。然而,这两种迥异的段落之间又有着隐约的联系:五月这一农业和乡村生活中最为美妙的时节,在城市生活中是“劳动者的节日”。我想,穆旦这样处理这首诗,多少都想告诉读者这样的潜台词:诗歌要成为关注时代命运的承载物,要摒弃习惯的乡村记忆转化成诗情的方式,从现代城市社会的特质中找寻可以涵盖传统诗情的元素,是一个很好的取径。穆旦其他一些诸如《还原作用》、《在旷野上》、《蛇的诱惑》等诗以及俞铭传的《金子店》、《压路机》,袁可嘉的《南京》、《上海》等诗中也有现代城市生活和工业意象的大面积织入,可见,我们从《五月》中解读出的意义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在西南联大诗人群还对战争主题进行了现代性的开拓。杜运燮在抗战期间随军到过印度和缅甸,对战争有着切身的体会,其诗歌中以此为题材的作品有很大的数量。《草鞋兵》、《号兵》、《无名英雄》、《游击队歌》、《树》一类数量不算多的作品保持战争初期的那种激昂和乐观的情绪。诗歌主要试围绕具体的敌方和具体的我方展开的。而后来的很多诗中,这种与时代要求一致的情绪不复存在了。战争主题的内涵转向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战争作为死亡的代名词对人的压迫、战争与个体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之间的关系等。在《悼死难的“人质”》中,“我们”面对的再也不仅仅是具体的敌人,而是客观的战争了。
而你们只好无声地死去,而《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林中鬼夜哭》这一类诗中,诗人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叙述角度,通过“死人”向“活人”的倾诉,虚构了人死亡之后仍对战争留下的恐惧,他们是战争的牺牲品,但从战争那里得到了启示性的反思,这最为真实而又深刻地隐喻了战争对人深及灵魂的打击。
来不及哭泣或诅咒,但一切
是工具的时候,利用工具与成为工具
与等待被使用,是一样的不幸。
与杜运燮相比,穆旦对战争的开掘就不仅停留在战争对整体的人类压抑,而且也引出了对战争中个体生命存在与生命价值的思考。《野外演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事实上已承认了大地的母亲,诗人写的是演习,实则是在写他对战争的感受。正是从演习之于战争是游戏和虚拟性模仿的意义上,诗人看见了战争本身的虚无。个体生命在经历了大的动荡时,必然会遭受痛苦,这种痛苦本身能导致一个人更接近自己的存在,然而当战争这种动荡保持了很长时间之后(八年抗战)就会形成习惯和常规──这是遮蔽存在的黑幕。当社会结构有所松动时,具有前瞻性和先锋色彩的诗人,就能够离开人们曾一度无意识接受的那套习惯和准则──这是诗人在揭开帷幕。穆旦觉察到:对人来说,永恒的敌人不是战争的双方,甚至也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人的存在的遮蔽和人自身的蒙昧。由此,我们方可对穆旦为何在战争环境下还能写出《诗八首》、《我》这样的诗有所了解了;回到自我,回到个体,这不是逃避,而是更高层次的介入。
又把几码外的大地当作敌人,
用烟当掩蔽,用枪炮射击,
不过招来损伤:永恒的敌人从未在这里。
这又引出西南联大诗歌另外一个现代性的主题:人的寂寞与死亡及个体的存在价值。郑敏出身西南联大哲学系,对这些哲学命题进行直接的探讨和思辨,比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死讯》从生命与死亡入手,对情感与理性、命运的偶然与历史的必然进行了分析性的思考。《时代与死》看到了生与死对立而又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这一类诗中,生与死一被郑敏加上了引号,便从统摄一切主体的权威地位客体化为与一般事物无异的实体名词,任诗人以冷静的语句驱谴;宏大叙事为哲理性思辨所取代,这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且她把每个人都似曾经历过的含有生命与死亡的具有重大诗意的瞬间展现了出来,独特思辨所开拓的巨大意义空间由这样一些瞬间的诗意填充,使诗歌读来既促人思考又触动内心深处隐秘的情感。
与生命与死亡这一主题相关的是,郑敏把握到了人寂寞的生存状态的意义。在《雕刻者之歌》里,从寂寞对人的消极影响中解脱出来,诗人看出寂寞是从无常的时间之流中找到永恒价值的炼狱。在另外一首更为直接的作品《寂寞》中,诗人传达了她对这一人生主题更深入的思考。人类摆脱寂寞和孤独的热烈渴望没有因为现实中寂寞的无所不在而减弱,而是以人发现寂寞的庄严力量和严肃意义从而获得反驳和抗争力量而加强了。不仅是郑敏,杜运燮、穆旦等人对“静默”这一精神状态的倚重,也具有同样的深刻意义。可以说“一切皆为时间之流”的柏格森式的生命哲学在他们这里最终获得了积极的阐释:寂寞成了一种抗争的姿态,是诗人跳出了社会僵化机制之后,与仍处于社会习俗中的蒙昧的人无法交流,但又不愿堕落也不愿弃他们而去的结果。
西南联大诗歌的另外一个“现代性”的主题,虽然普遍性不及前述的几个,但其对于现代性转变的意义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穆旦诗歌浓重的宗教氛围。其实不止穆旦一人,更为宽泛地说,我们可以在很多诗人那里看到重新找回可以皈依的价值体系的努力。这与宗教氛围有着相同的内涵。 在穆旦的诗歌中,特别是40年代后期的诗作中,“主”、“上帝”、“神”是经常出现的字眼。在一首名为《隐显》的长诗中,穆旦系统而深入地体现了个体诗人对现实乃至整个文明的批判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上帝的信仰。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穆旦的宗教主题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与我们前面论及的现代工业文明批判主题、个人生存状态、寂寞主题密切联系的;如果套用流行的批评术语可以说,前几者分别代表了现实对人的围困、被围困中的诗人,而后者代表了诗人力图突围的努力。事实上,穆旦充满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他企图寻求自我解脱的努力可以说是并不成功的,但他在诗中建构一个上帝的努力却生成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在现实中,穆旦并未找到个人价值的最后基点,未能重构个人的价值信仰,但在诗歌中,这种未完成的突围,未有结果的抗争却成了诗人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了解穆旦的王佐良和杜运燮各有一段话涉及了这种宗教主题的现代性价值所在。王佐良说:“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杜运燮说穆旦“并非基督教徒,也不相信上帝造人,但为方便起见,有一段时间曾在诗中借用‘主’、‘上帝’来代表自然界和一切生物的创造者。”这两句话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从两个相关的方面反映出“宗教诗”在中国的“现代性”特点。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作家虽然并非无神论者,但他们却什么也不相信,冷漠的表面下其实隐藏的是空洞,然而同时他们又恰恰是最为传统的,因为他们具有的是中国式的平衡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的精神上的起伏就不可能出现,因而宗教诗也从来没有发达过,“但是穆旦,以他的孩子似的好奇,他的在灵魂深处的窥探,至少是明白冲突和怀疑的。” 这相对传统来说,无疑是具有反叛和超越性的。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在西方现代派诗人中,无论叶芝、里尔克还是T·S·艾略特都具有极其浓厚的宗教气息。艾略特自称是英国的天主教徒,他的诗在批判现代文明社会的同时想指出的正是宗教复兴之路。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充满了宗教拯救自身和人类气息,而叶芝则在诗歌之中建构起了充满基督教色彩的历史循环价值体系,这些诗人都是对穆旦乃至整个西南联大诗人群起过重要影响的,他们诗歌的宗教气息向穆旦的渗透时夹杂了诗歌现代性的种种特质和规定性便不足为奇了。但杜运燮的话也是事实的一面,与有着千年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西方现代派诗人相比,穆旦“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现实或许有着更为广泛的文化含义:中国的现代诗人不可能完全沉入主体与绝对客体(理念)之间旁无他物的对话(尽管这种对话可能包括了万物),而必须将周围的现实和中国诗人传统上具有的责任感更为直接和清晰地纳入视野之中,故尔在这里说“借用‘上帝’这一名词”虽有一些偏离事实(毕竟,如前所述,寻找最终的立法者和价值的基点确是穆旦的主观愿望),但大体上说出了一个真相。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到诗歌“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下所表现出的特殊性。
四
通过对西南联大诗歌的主题学研究和个案讨论,我们大致得到了它与新诗现代性转变的内在关系。他们不仅担负了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汲取营养的责任,还为“诗歌现代性”的本土色彩的确立付出了努力。在他们之前,转变虽有了一定的诗歌技巧的准备,但并无成型的现代性诗歌的中心观点;在他们之后,由于时代语境越来越向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转移,政治的不可让渡性被政治的决定性和唯一性代替了,诗歌现代性的转变因自由兼容的诗歌氛围的失却、诗人独立人格的减损,渐渐平息下去了。
不过,无论如何,西南联大这批诗人的创作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成果,甚至多年以后,当八、九十年代的先锋诗人们偶尔回顾历史,也会惊讶于中国诗歌还有这样一些极具现代性的作品。反过来说,一旦西南联大诗歌的意义被重新发现,就能引起哪怕是当代最先锋诗人群的共鸣,这也说明了西南联大诗歌本身现代性转变的意义。
■〔寄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