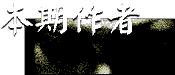我构想我能达到的境界
--路离访谈
问:你是什么时侯开始小说写作的?
答:产生写小说这个念头是95年夏天。那段时间不安心工作,有两个月赋闲在家,看米兰昆德拉看余华看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是他们激发了我写小说的欲望。头脑中构思了一部小说的提纲,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想想罢了没有落在笔头。97年写了两个短篇,谈不上是小说,只不过是把一点想法记录下去。幸亏是用电脑,要不然我连中文字都不会写了。写得极其艰苦。写了上句不知道下句写什么,每一句写下来觉得好象是别人(反正不是上帝)握着自己的手写的,离原先的意图相差很远。才知道看似容易做起来难。然后就是2000年5月,我开始把写小说当成一件事情来做,并以乔丹的一句话为自己的座右铭:“我构想我能达到的境界,我能成为什么样的选手。我深知我的目标,我集中精力,到达那里。”
问:是突发奇想如接上电源的机器开动,还是长期积蓄然后就象打印机吐出一页页小说来?
答:应该说是长期积蓄吧。“我要写小说。”这句话在我头脑中盘桓了好几年,尽管没怎么写,但我一直在阅读和考虑应该怎么写小说。97年的那两篇虽然写得很差,但我从中感觉到写作的乐趣,这种乐趣是如此强烈以致使我念念不忘。
问:那么小说写作是否与你的个人经历有关?比如有许多作家常常谈到儿时的记忆、经验对写作产生影响。
答:我以为写作一定是与个人经历有关。人可以超越经验却无法摆脱经验。
我在上海和北京两地长期生活,这两个城市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写作动力。
我十五岁以前在上海。那是个温情的腐朽的乖巧的恣意的让人无法忘怀的城市,它深入我的骨髓溶入我的血液,织起一张梦幻的背景永远悬挂在我身后。因为是童年生活在那里,我的活动范围很窄,所以上海对于我来说更象是一个江南小城。我固执地认为如果曾经有前世,我的前世一定是在某个传统的江南小镇,粉墙黛瓦的小楼,湿漉的青石板地,小桥流水。
而我的思想启蒙在北京,那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我接触了很多新思想,认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我在北京开始了新生活并且开始热爱那里——傲慢得近乎低微,先锋的思想和顽固的杂碎并存的北京!
在我的眼里南方象征着世俗生活,我在那里展开回忆:一幢老式的三层楼房,一层一户,近二十口人,鸡犬相闻,蜚短流长象细菌一样在每个隐秘角落里穿行,还无法理解的我就在那里木然地观看倾听。现在我写小说时其中的某一个片段会不期而至,当我写下它们后,我才对其中的奥秘有所领悟。
北京则象征着青春期的迷茫,压抑,反抗,狂乱和思索。它们对于我是更现实的,可以触摸可以感知可以呼吸。如果说在上海我是被动的,在北京我则是主动的。而这中间的转换非常微妙。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问:你说到对米兰·昆德拉、余华、西蒙·波伏娃的阅读,还有那些作家出现在你的阅读中?
答:如今大多数写作的人都以西方作家为范本,大谈这个主义那个理论,我却要说余华的早期小说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它们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小说,我感觉它们离我非常近。也正是它们使我产生了写作的愿望。前一阵刚刚看到余华在一九八九年写的创作谈《虚伪的作品》,从中可以体会到当他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法时的狂喜,那种反叛和自信的快乐。他说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知道为什么写作”。他提到虚伪的概念时说:“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这正是我感觉到的,也是写作以来一直在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也同样认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一种确定了的语言,这种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它强行规定了事物的轮廓和形态”。最近我对这个问题依然比较迷惑,我还在寻找自己的方法,也许这是一个写作者需要始终思考的问题。多么想欣喜若狂一回!
还有一个是韩东。我喜欢他貌似平静的叙述,他小说的节奏和语言的质地让我对诗人心生敬畏。
苏童的作品很好读,他的天赋的语言技巧和结构故事的能力很让我向往,他笔下的南方生活非常亲切。
还要说到孙犁。语文课本的里《荷花淀》使我对朴实的艺术之美感触极深。当然年少时我也曾经错过过我不能体会的。几年前随手翻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集,当时感到非常惊愕,因为他写得实在是太好了,完全无愧于被当成经典阅读。只要轻轻拭去一层看似平淡无奇的尘埃,我们就能从中发现优雅,恰如其分的节制,黄金分割般的平衡,还有公正,同情心,理解和宽容。
另外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作家是托尔斯泰,芥川龙之介,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卡夫卡。我也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和《一千零一夜》。因为我的阅读和理解有限,一定还错过了很多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希望能有机会和它们相遇。
问:在你的学生时代是否对写作有兴趣,你的专业是什么?
答:是否有兴趣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是太清楚。如果一件事你想做,有人万般阻挠,结果你还是想做,那可以称之为有兴趣。我的作文小时侯经常受到赞扬,被当成范文,语文老师对我宠爱有加,在上海市小学生作文比赛中得过奖,这些无疑会增加一个小孩子写作的兴趣。这是一种顺水推舟的兴趣,与其说是对写作有兴趣不如说是对赞扬有兴趣。高中时一次在课间自发写了一个小短文,是表达升学考试压力下的心情的,写得不那么中规中矩,也知道老师肯定看不入眼,我却很喜欢,第一次觉得终于写出了活生生的文章。从那以后,我知道了文章可以有另外的写法,可以表达心声,才觉得写作的乐趣倍增。所以,我要说的是,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正确的引导在我们的教育中是多么匮乏。那时侯写作文都要求一个明确的高大全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荷塘月色》的中心思想不是很向上,于是问老师。老师回答的大意是,那是名篇,作家写的,和你们的作文不同。稍有判断力的年轻人都会对这个回答产生怀疑。
95年曾经想去考中文或者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并不是多想上学,只是这样可以离自己的兴趣近一点,更冠冕堂皇一点。我倒情愿呆在家里看书写点什么,考虑到这过于叛逆,周围的人会有异议,做了一个求其次的选择。最后还是没能力排众议。
原先专业是日语,出国后学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写作的确象有些人说的好象吸毒一样,一旦染上了,就算暂时戒掉也总会复吸。
问:在开始写作的时侯,周围的朋友是否对你产生影响?
答:楚尘说他写作是因为他身边有太多的作家朋友,每个人都在写作,他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向他的作家朋友们表示敬意。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羡慕的说法!我还没有机会和别人探讨过关于小说的问题。我的状态是孤独的,默默的……呵呵。
当然朋友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的。我初中时最好的朋友喜欢看高阳的小说,喜欢古典诗词,我们一起背诵《长恨歌》,以最快的速度,上气不接下气,计时,精确到秒,好象是最快两分多钟。高中时有三个同学,坐在我的前后左右,我们上课不说话,交流靠传纸条儿,写点风花雪月和人生感悟之类的。现在我还保存着那些东西。和其中一个同学曾在空置的教室里写过满黑板的诗。她前年到波士顿,离我不远,我们见过两面,她说如果有机会她愿意写点东西。还有一个现居深圳,以前她背得出所有罗大佑的歌词,听说她偶尔还写写散文。总之,人以类聚。但个人机遇有所不同。
对我产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书籍,超越时空和伟大的灵魂相遇是人生最最美妙的事情。
问:你的小说是曾在哪些地方发表,在网上发表对你的写作热情有没有负面影响?也可以这样说,某些自由撰稿人希望写作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所以关心发表,而网上发表不大会有实际的利益,其中也能够说明一个写作者对文学写作持什么样的态度,你是如何考虑的?
答:我写小说就是因为喜欢。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不想临死前回顾一生的时候悔恨交加。写小说肯定是个不挣钱的行当,就算小有名气,有文学刊物来约稿,也是“难以为继”(上海女作家丁丽英的感慨)。靠小说发财就更别指望了。有一个文学频道的斑竹就自嘲为“穷人郭发财”。替有史以来最挣钱的王朔掰手指算算,在各行各业的首富里他是最穷酸的。铺天盖地的盗版打击作家致富的信心。靠稿费生活的自由撰稿人更是举步维艰。篡改一句李宗盛的歌词:“想写是容易的,想写下去是困难的”。据说给杂志写时尚文章稿费丰厚,但我对那些假情趣假俏皮的东西不敢兴趣。我自认为在开始就对文学和金钱的关系认识得比较透彻,否则在两者之间徘徊和挣扎太痛苦了,更容易搅扰到写作的心态。
目前文学的处境的确不容乐观,但是真的艺术历来总是在缝隙中生存。我以为文学领域的“优胜劣汰”是指伪装的文学青年逃跑;忠诚分子留下来,探索更远的路。至于网络写作,也是因为我的实际状况,我开始正式写作是在国外,在网上发表非常方便。我感觉自己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游泳,《橄榄树》这个小小的岛屿供我休息和稍做停留。真正专心写作的人之间会通过文章产生心灵感应,这种灵异第六感使我在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塌实而温暖。
我不是个不关心发表的人,也需要鼓励。网络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但是网络文学确实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橄榄树》这样优秀的网络纯文学杂志,会减弱很多我投稿的兴趣。我的内心自然有一个标准,不是登在哪里我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感到骄傲。
半年来,在传统杂志上的发表情况比较幸运(比我预料得要好,我有长期作战的准备),有两篇在《佛山文艺》,一篇在《山花》发表,还有一篇即将刊登在《天涯》。
问:你前面谈到,1997年你才真正开始写作,应该说时间不长。我读过你的几篇小说,我觉得你前几年的小说与最近的小说有一定变化或者说是深入,而且是有意识地在形成你自己的东西,你对自己的小说写作如何看?你试图在小说写作达到怎样的状态,形成怎样的风格?
答:97年写的两篇提起来汗颜,纯粹练笔,记流水帐,构成一个小故事。那时对我来说把文字写通顺了就是大功告成。原始稿非常粗糙,去年修改了一下,但是底子太差,涂脂抹粉也无济于事。那完全不是我想象的小说。我自定义的真正写作始于2000年5月。
我想象的小说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形态,呵呵,要谈对小说的理解真是一件困难的事,也非常危险——给写作设定规范,就象下一个圈套,然后自己一头钻进去。
在这里想提一下京剧。以前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去看京剧,多时一周一至二次,真是折磨,我对这种老掉牙的东西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听不懂,节奏缓慢,固定的程式极其乏味。但是我不得不坐在那里,就算心不在焉,眼睛和耳朵也是打开的。所谓耳濡目染。难以置信的是,看着看着居然有一天我突然从中看出“美”来了。演员的举手,投足,眼风,被固定在一种特殊的千锤百炼的形式里,在咿咿呀呀的京胡伴奏中抑扬顿挫。每一种形式对应一种“象征”,一一对应的简单“象征”和“象征”的不同组合就神奇地构成了无限大或者无限小的世界。由此我意识到,“象征”在艺术形式中普遍存在,无论戏剧,美术,文学还是最为抽象的音乐。“象征”同时具有稳固性和流动性,它由创造者和感受者(观众,欣赏者,读者,听众等)共同合谋完成。每一种“象征”都因为这种合谋得以加固,嬗变,衍生或者分化。年深日久的“象征”同一件纯粹的物质一样会老化,而老化的“象征”无法激起人的情感和智慧。
所以我希望在小说中表现“崭新的象征”,这种“崭新的象征”热情洋溢,无所不在。不是以红色代表激情白色代表纯洁那么单一和具体,而是小说的一切的因素:语言,节奏,质感,情绪,叙述方式,结构等等,所有的暗流都指示某个方向——无论这个方向混乱还是明确。
卡夫卡临终前要朋友烧掉他的全部手稿,这是盘旋在我心头的巨大谜团。我的小说永远需要读者(不是指人群的大多数),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我的小说是未完成作品。
小说不仅体现我对世界的看法,更体现我的困惑。上学时喜欢看哲学书,是想要别人给我解惑,看来看去总觉得他们说着说着把自己给说糊涂了,要不然就是对自己的说法产生了怀疑。那时我迫不及待地需要一种明白无误的说法对身处未知的宇宙中的好奇的自己做一个交代,我要求这种交代历久弥新,照耀一生。自然是失望了。后来当我把阅读投向小说,以冷静的思考而不是投入,忘我,感动来延续阅读时,我终于发现了小说的妙不可言。
好的小说是一块打磨精细的钻石,从不同角度看过去呈现不同的光泽。也就是说,好的小说应该提供给读者多个观察角度,尽可能地让读者在作者思考停止的地方继续下去。好的小说把“不达意”的字词巧妙地连缀起来,以故事或者零散的故事碎片组成一个无穷多面的晶体,展示宇宙的无限可能性。
同时我要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设立“第四堵墙”。我以为距离感,荒谬感,断裂感更有助于客观地思考;看好莱坞言情片的那种被诱发的生理反应:泪水浸湿几块手帕,片刻后丧失记忆般笑逐言开不是文学应该追求的效果。距离感,荒谬感,断裂感还提供给我们另外一种观看世界方式,在我们千万遍以同样的方式默然地打量世界之后,是该换一种方式了。“事实不会过时,看法却会陈旧”。人的思考总是不到位,细心体会“荒诞的事实”反而利于我们离真相更近。当然“荒诞”不是毫无根据的信手拈来,“荒诞”基于事实,之所以成其为“荒诞”只是因为在有限的一生里我们遇见“荒诞的事实”的概率很小,我坚信这一点。我个人有很多次“现实比想象更荒诞”的经历。
想要谈清自己的写作理念很累人啊,呵呵。当我开口说的时候,我走在一条离原先的意图越来越远的道路上。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的由来吧,一幅画,一段音乐,一篇小说,一首诗比说明的文字表达得更彻底。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最需要努力的也是尽力缩短表达和想要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差距。至于风格,我没有想过。我的风格就是我的风格,是自然流露,只有写出来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风格不可能模仿,那种形式感可以照猫画虎,但顾及了形式感,就会丧失内在的东西。最重要的没有了,光剩空架子还有什么用呢?我模仿不了别人,别人也模仿不了我。
我写作的时间还很短,一切都是探索阶段。风格由理念和作者的气质而来,我的风格还没有形成。
问:你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哪一篇?
答:第一篇小说是《单身女人的周末》,在网上点击率惊人。:)铁嘴钢牙的鲁迅先生说过,人们想看女人的书,就是想看看女人的小脑袋里都有什么,把她们的著作搁在枕边,就有了亲狎之感。更何况这篇小说有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并不是刻意而为之,写的时候还没有上网,也没有打算给任何人看,只是写写心情,写着写着比较完整了,看上去象小说,便称其为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如果我是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一定不肯讲出这是我的“处女作”,但和严于律己相比,我更是个诚实的人。:)
问:有不少小说作家是从诗歌开始文学写作,你一出手就写开了小说,为什么?有人说写小说一上手就不能放弃,你是否觉得写小说比写其他体裁感觉更好?
答:其实我很羡慕从诗歌转向小说的作家,他们普遍掌握良好的语感和节奏感。人在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写诗,等年龄增长了,只留下少数拥有“诗歌性格”和“诗歌生活”的人还在写诗。真正的诗人气质纯正,和社会的距离要比小说家远。这种气质有时侯被神化,有时侯被异化。在我的概念里诗歌界于文学和音乐之间。我尊敬真的诗人。
为什么一开始就写小说这个问题以前从未想过。我对诗歌还是心有向往的。现在想来是我有可能走向诗歌的时候被压抑了。为了上大学而寒窗苦读,上了大学后努力把过去十二年中“失去的欢乐”都夺回来,工作后一门心思赚钱……说得宿命点儿,我不具备诗人的气质。
看过一篇两个女作家的对话,她们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女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开始写作,一场疾病?抑或是一场恋爱?对于我来说两者都不是。之所以提到这里是因为偶然性和必然性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小说是包容性很强的一种形式,有足够的空间让作者天马行空,就是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具有“无限可能性”。同时小说这个物件本身具有“无限可能性”,这种“无限可能性”由貌似“没有可能”的具体的描述,故事传达出来,写下一篇小说好象种下一颗种子,随着条件的成熟,种子会发芽,然后自由地伸展。这两种“无限可能性”是由作者和小说,小说和读者之间的比较大的“互动性”决定的。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体裁如杂文,抒情散文一类太过直接,总是就事论事或直抒胸臆,完了就是完了,没有“后劲”。它们执行“表白”的功能。这或许是我的偏见。
问:你说的距离感,荒谬感,断裂感使你的小说具备张力,其中的叙述好像是对事物做了格式化。而现在你的小说基本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如果换一视角你会觉得困难吗?
答:我居然以为自己第三人称视角的小说要比第一人称多!自己数了一下,包括我还没发给你的两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果然比第三人称的多了两个,但是其中有三篇中的“我”不是主人公。
小说的视角的确很有意思,我不觉得这种好或者那种不好,给第三人称冠一个“全知视角”的恶名。采用哪种视角全看作者要表达的东西与作者之间的天然距离以及作者力图控制的距离和辐射面,在总体的距离感之中还有许多细小的距离感和各种距离之间的微妙转换,这些东西完全靠个人感觉来平衡。和作者的偏好也有关。
总的来说我喜欢从远处打量。在远处我看得更清晰一些。我情愿用思想而不是皮肤写作。当我和我的小说过于亲密的时候,我感觉被捆缚,无法进行下去,写了一半报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形。我小说中第一人称视角的“我”往往比第三人称离我本人更遥远。我喜欢通过作者和叙述者,叙述者和作品在不同媒质间制造多次折射的效果。而不是以本人贴近叙述者,写出市面流行的半自传类的小说。
第二人称还没有尝试过,比较适于心灵对话,但弄不好会显得生硬。
我写作起步很晚,按理来说处于我的年龄应该有十年左右的写龄了,但目前创作还处于初始阶段。从2000年5月才开始认真写,每一篇都是一种方法(不是什么创新,是写作的基本方法)的尝试,直到半年后我才觉得自己对写小说这门手艺有了初步的了解。11月中旬开始我的写作停滞了,到现在为止两个月里,我全面反思过去的作品,预感到我写作的第一阶段暂时告一段落。
问:作家朱文曾谈到“对成型那个东西我一直很警惕,感觉到自己好像找到一些东西了,找到一种表达方式了很吸引我,我甚至有点开始享受那种感觉,这种时侯我就觉得必须停了。”你所谈到的一个阶段写作之后的反思,具体是怎样的感觉?
答:小说写作不断挑战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如果这只是个找到个把漂亮模子把原料灌进去的简单工作是不会吸引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
我还没到朱文那种境界。我正在寻找一种足够吸引我的表达方式,迄今为止的一切作品都是寻找的过程。我感觉离它越来越近。
具体地说就是我需要新的方法(以往的那些不够享受),我感觉以前所有的作品正在集结成一股强大的力,我在仔细地揣摩和把握,生怕这股力量传达到我身上会有所削弱。
问:我认为小说写作难免是在生存经验上展开想像。你认为小说与现实是什么关系?你如何看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答:我理解的小说是对鱼龙混杂的现实去伪存真的整理。小说提供给人们另外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使人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早已习以为常视若无睹的周遭世界和内心。因此好的小说必然不是一幅栩栩如生的照片,再经典的照片也只是“眼见之实”的记录;好的小说是对“眼见之实”的现实的颠覆,让我们看到现实深处和现实以外。和现实相比,好的小说离真实更近。
人的一生经历有限,直接经验也有限,直接的不够就要靠间接的补充。直接经验因为其直接性感受起来较少障碍,因而也具备冲击力,容易在作者的心中留下抹不去的烙印。有时即使自己不察觉,它也会潜伏下来,一旦时机成熟自动引爆。间接经验则建立在直接经验之上,它们互做加减法。我觉得同类型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的对比有助于人思考。对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感受因人而异,不排除有些人对某些间接经验更加敏感的可能性。不管怎么样,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建立在生存经验的基础上的。
对于一个写作的人,在生存经验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以为这是心理历程(阿城讲过)。过着平淡生活的人有可能内心波澜壮阔,这种状态提高对生存经验的敏感度,是写作源源不绝的推动力。
问:有些作家尽可能回避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许是出于一种叙述策略。我觉得你的小说中对话也不多,你是如何把握的?
答:我没有刻意回避人物对话,可能我的人物都处于比较隔绝的状态,我更喜欢用其它的方式来写他们。也有不少优秀的小说靠对话来推动情节。我很喜欢余华的《战栗》,还有朱文《因为孤独》那个集子里的一篇,好象叫《如果你因为穷困潦倒而死》,陈卫的《我是野兽》也不错。其实我也尝试过这种方法,只是不太成功。
问:你目前生活在美国,处于一个英语环境中,对你的汉语写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我在加拿大。单从语言上来讲这个环境对我的写作没什么影响。加拿大是个鼓励多元文化的国家,在这里聚居着世界各地来的人,有一半人说着带口音的英语。到了唐人街就是汉语世界了。
来这儿以后才深切地体会到汉语太美了,准确精妙,韵味无穷;很多意思用英语表达起来却如同骨鲠在喉索然无味。我不能体会别人语言中的微妙之处,就好象用刀叉吃饭对中国人一样,光顾了摆样子,尝不到半点滋味。而且他们的饮食真的是不如我们的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在这里有一点好处是:人为制造了空间上的距离。活生生地把我从熟悉的无法根除的环境中抽离。感觉有点象顽皮的鱼一不小心跳到岸上,或者野生动物贪玩跑出了原始森林,离开固有的环境连鱼和野生动物也不得不开始想一想了。:)))
我的意思是写作者和生活应该保持一定距离。象谈恋爱一样水乳交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纠缠得神志不清,到最后总是会用上“如梦方醒”这个词。当我和“生活”死缠烂打不可分离之时往往是我心中的杂草一丛丛蓬勃生长之时。而当我有所觉悟,摘下头上的紧箍,咒语也不再起作用。神力无边的孙大圣为什么要服从手无缚鸡之力的唐僧呢?写作者只有抛开现实的纷扰,以心灵的显微镜观察肉眼不可见的事物时才会有所启发。距离是客观条件。古代所说隐士中的高一等“大隐隐于市”属于自由穿梭于两个空间中的超人,除非真的得道,否则必然是痛苦的。我更愿意在客观上保留和火热生活的距离。这里人少,安静,与己无关。
还有一点,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利于我反观对照,与其说我获得了新经验,不如说我对旧经验获得了新的认识。
问:你说大学学的是日语,那么你曾对日本文学产生阅读的兴趣吗?
答:日本文化中有对一种“纯粹的美”的追求,他们的某些异端行为如“切腹”就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作家中自杀的也较多。我最喜欢芥川龙之介,看过原文的《鼻》和《罗生门》。还看过一个中文的短篇《竹林中》。他的小说自诡异中渗透出一股杀伤力,令人过目不忘。芥川也自杀而死,可惜了。川端康成那一路的则极具日本式的美感,我喜欢《伊豆的舞女》。日式的“美的精神”从日本的茶道花道中尤其体现出来,就是特别的洁净,安详,朴素,细致,余味无穷,最重要的一点——美得充满了缺憾。
日语具有粘着性,情意性,句尾感叹词繁多,用来写文章看上去罗嗦,但因注重留白的效果,俳句却意境悠远(比唐诗还是差了一些)。
三岛由纪夫则特别体现日式的阴郁的激情,这种激情中包含绝望和坚忍。
问:头次在橄榄树看到你的小说,确是那篇《单身女人的周末》,但这个题目引起了拒绝心理,说实在我没有去读。昨天我读了一遍,觉得也不差,起码不是“虚伪的作品”。后来读到一篇《夜行鸟》,我说这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了,具体地说是不自觉地坐坐好一口气读下去了。读了第一个段落,就认为是一篇好小说。有一种想笑又笑不出,随后又无奈摇头的感觉。我喜欢这篇。你对你已有的小说,相对来说哪一篇最令你自己满意?
答:没有真正满意的,也不能说没有偏爱,但这种偏爱时常会变。自己的孩子嘛。有时抱起这个看看这个不错,有时抱起那个看看那个不错。我只知道有几个不满意的。《夜行鸟》那篇写得比较有趣,还有人说过喜欢我的《阴翳街》《小贩的黄金》什么的。现在我离他们太近了,或许几年后我自己会有个清楚的判断。
问:你周围的朋友熟人知道你写小说吗?你给他们看吗?
答:有限的几个朋友知道。给他们看过。但是写作是个孤独的事业,靠内心的力量来完成。
问:你认为文学写作中对写作者性别的强调是有益的吗?
答:这个问题专对女性。男作家基本不考虑这种问题。有个别擅写风月题材的男作家偶尔会不露痕迹地强调自己的阳刚之气,这只是例外。男人有先天的心理优势,觉得自己的性别明明白白不用强调。所以我理解这个问题是——女性写作者要不要强调自己的性别?性别可能是人所有属性中第一重要之物,写简介必然想起先把性别列在前面。有的女人喜欢强调性别是因为总可以得着些便宜;我在简介里说明性别是我不想得着什么便宜,尽管做女人常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但我更愿意活得理直气壮一些,并且高呼一声——尽管环境险恶,我还是在成长。一个美国妈妈忧心忡忡地看着自己四岁的女儿说:“她以为世界是一大碗鸡汤,她正兴致勃勃地准备象一根面条一样跃入其中。”我热爱的黑人女歌手崔西查普曼说自己处于社会的最下层,因为三个原因——“我是穷人。我是黑人。我是女人。”伍尔夫也说过女人写作是为了给自己在社会中找到一个阶层(大意)——真正值得女人落泪的一句话。
据说原来的女性写作者愿意把自己往男性思维靠拢,以男人为标杆来衡量自己,写出貌似男人的文章。现在的潮流是强调自己的性别,特别是在生理上和与男人有关问题的女性心理上,抛弃所谓男性思维,什么社会问题啦,人生终极问题啦,让它们统统见鬼去,痛痛快快地做回女人自己。
女人犹犹豫豫,反反复复,终究逃不过假想当中的那只男人的眼。
女人的基本特征究竟是什么呢?是鸡零狗碎,家长里短?是带着自恋意识的雪月风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女人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雄心?
琐碎,感情用事,拘泥于井底而自得其乐不是一个健康的女人的特征。这是男人给女人强加的定义也罢,是一部分女人不争气造成的的一叶障目的事实也罢,这终究是不健康的。如果女性写作者本身就具备这种种不健康的基因,还要呼天抢地地把自己的丑态如实记录下来,一边吆喝着:我是女人我怕谁;更有甚者另有一番壮志凌云——意欲造成人类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集体意淫的蔚为壮观场面,那她们还是“歇菜”(北京土语,重音在前,意为:打住,一边儿凉快儿去)为好。
但是如果我们反其道行之,穿起西装,系起领带,并且哑着嗓门说话,生造出第三性,还沾沾自喜以为迈上了第一性的领奖台欣然接受男性掌门的颁奖的话,我们自己强颜欢笑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心比黄连苦不说,造物主也会龙颜大怒。
因此,我以为做女人必须有平和的心态,女性写作者更应如此。
性别无时不刻影响着女人的状态,是刻画女人之所以成其为的女人的最锋利的一把刀子。一切无须表白,尽在不言之中。社会从来就是在教你怎样做一个女人:女人应该笑不露齿,轻移莲步;女人应该含羞作态,适时落泪;等一切本领练就了就该待价而沽……
对这些再拒绝也好,哪个女人又不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呢?如果按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在我们还没有辨别能力的幼年时期种子已经种下了。我们干什么都要先怯生生地瞥一眼男人的榜样。无数的男人在前面指引方向:哲人,艺术家,政治领袖,经济泰斗,女性问题专家;还有我们身边的人:男老师,男同学,男同事,男朋友,丈夫等等。可是事物都有两面性,这种劣势同时也给女人提供了一种观察角度的优势,这就是——我们不仅本能地站在女人的角度看问题,我们还常常自愿地设身处地地站到男性的立场上。男性好象领跑者,女性紧随其后。真不知道到了终点,是怎样一番结局?
我说过,女人比男人更具备广阔的观察角度。问题是女人愿不愿意把这种观察深化下去。如果愿意,如果女性能够尽量客观公正地看待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心理历程,以淡定的姿态处之泰然,并且抛弃个人得失,把眼光放得长远且深邃的话,女性写作必然天地宽广,如同其名为鹏的大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基于以上观念,我自己的写作没有突出性别意识,一切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既有写女性问题的小说,也有一些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终极问题的小说;既有女性为第一人称的小说,也有以男性为第一人称的小说。全看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写作是人的事业,非某一性别专属,更无须画蛇添足在作品中宣布自己的性别。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原则是不惧怕,不妥协,不谄媚,不苟且。
问:以卫慧为代表的女性写作被视为“身体写作”,当然这只是一种流行的说法,也有人指责是“殖民写作”。你如何看这一类写作?
答:先说卫慧。卫慧之流格调不高这是肯定的,但是卫慧引发的问题好象还没有完结,就算卫慧消失了,卫慧这面镜子照出的影象还没有消失。轩然大波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人们蠢蠢欲动的欲望。有网友在关于卫慧的讨论里说:“你不觉得她们活得很精彩吗?”这象一个女人羡慕的口吻,也不排除是男性的可能。更多人对美女玉照封面感兴趣,对细致入微的性描写心旌荡漾,即使边看边骂要呕吐还要考验自己的忍耐力。所以卫慧有市场的也是必然的。我要表彰卫慧,卫慧同志有大无畏的奉献精神,起码客观上起到了“照妖镜”的作用。我很想知道鲁迅他老人家活在这个时代会有什么精辟的观点。
要是从广义上理解“身体写作”的话,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历来艺术家分两类:身体先行和思想先行的。在理性思维无法到达的地方,人只好打破传统逻辑,消灭以无须证明的“公理”为基础形成的理论,拿自己的身体直接摆上祭坛。只要这种有胆量需热情的作为在冥冥之中是为了离真理更近的缘故。那部影响了一代人的《在路上》即是代表。 “殖民写作”这顶帽子扣在卫慧头上是太大了一点。我不太明白这个批评是指卫慧之流的生活态度——对西方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还是指卫慧的写作方法。如果是前者我也高举批判的旗帜,如果是后者我倒有些想法。
文艺理论界的某些论调早就把先锋写作归结为“殖民写作”,横扫一批中青年作家,我觉得这不对。“殖民写作”这个词充斥了强势文化对第三世界文化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在越南背包旅行的途中遇到两个西方游客,他们眼望着越南贫瘠的土地轻撇着嘴角说:“WHAT DO THEY GROW? RICE! RICE! RICE!”他们自己不喜欢吃米饭,就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爱吃。若是他们脑子再有些问题的话,就会夸大其辞以此作为越南落后的一个原因。这是所谓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惯有态度,学术界也不能免俗。而第三世界呢,找不到病因便白日做梦疑神疑鬼,被第一世界的一个眼神搞得心惊胆战,忙不迭地把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拿来衡量自己的文化。我认为,在我们左奔右突在有限的视界里找不到好的方法时,借鉴一下别人优秀的东西又有何妨?借了东西抱着“扬弃”的思想细心研究揣摩不归为己有最后完璧归赵了就行,没有必要“拿人家手短”,左一个对不起,又一个抱歉,做人做到抬不起头来,还要自己抽自己嘴巴。地域文化的强弱依赖经济发展水平,日本韩国都借鉴了不少中国的东西溶入自己的文化,现在反过来,他们开始影响中国文化了。
不加鉴别消化生搬西方的观念技巧固然是不对的,但也没必要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打击虚心学习的态度。
以我看来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与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一丝相仿。
问:你谈到你的小说“不是以本人贴近叙述者,写出市面流行的半自传类小说”。有些作家认为所有的作品都是写作者自叙,意思是事物经过作家的观察、感受进入小说,由此可以把作品看成是作家的自叙。你认为你的小说中存在你自己的影子吗?
答:那要看对“自叙”这个词怎么理解。如果你没有对“自叙”加以解释,我不同意“所有的作品都是写作者自叙”的观点。好的小说不是自己在说自己的事,女性小说往往写成这样,这不是什么优势是局限。这类小说好象梦呓者在自说自话,全看说得动不动人,凑巧说得跟会唱歌的夜莺似的,就会有人喜欢。我们往往可以从梦话中窥见人见人爱的隐私呢。如果说“意思是事物经过作家的观察、感受进入小说”那我同意,作者头脑中的既有意识一定会被读入文本。
我的影子在小说里肯定有,但是“幻影游动”。我喜欢把个人经历放进碎纸机或者干脆捣成纸浆再做一张新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