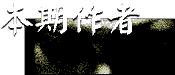幸福大街十五号
我又一次看见了你,我的神秘的爱人。你的微仰的头颅,环抱在胸前的手,嘲弄的嘴角和寒星般的眼眸,我不敢向你所在的地方靠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脑前,生怕又一次将你错过。你仿佛是浮光中的一点幻影,只在某一个无法揣测的角度出现。有时我会碰巧看到你,更多的时候,你是我心中的一个影像,我用心的热度一点点靠近你。
我停止写作已经半个多月了,这你也看得出来。我半年前来到这里,充满了理想和万丈豪情。我把洁白的纸铺在桌子上,给钢笔吸饱了纯黑的墨水,企图用黑字落在白纸上这一最传统的方式开始我的写作生涯。我写了一个大大的“我”字,还有我的名字,除此以外有几滴墨水滴在上面并渲染开去,使我的第一张为写作而准备的白纸因此废弃。我也发现写字是一件困难的事。在我写下一串没有意义的词以后,我回忆,有多久我没有写字了呢?我对许多字感到生疏,不是因为提笔忘字的缘故,我是太久都没有写一个字了,很多字明明写对了却看着不可靠,只有靠字典来确实。一个决心写作的人,常常为一个字的写法感到烦恼,这是一个绝对不够健康的开端。作为我写作生涯的第一次妥协,我放弃了纸和笔。
你知道,写作远比我想象的难得多,我的神秘的爱人。每天当我在这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坐定,总有一丝恐惧伴随着我。从我早上醒来恢复神智的一刹那,我的每一个下意识都阻止我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在床上磨蹭的时候,关于现状的考虑不自觉地溜进我的脑袋。现在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没有职业,也没有职业可想。我告诉所有的人:写作是我的职业。这是一份什么样的职业啊!没有薪水,没有目标,没有对手……我缓慢地下床,穿衣,刷牙,洗脸,吃饭……这一系列的仪式是我延缓向写作靠近的一系列的障碍,我行动如同构造一堵堵横亘在我和写作之间的墙,这也如同我在费力地拆除一堵堵的墙,最后我无可避免地坐在我的电脑前面。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这里是城市的边缘,离我曾经熟悉的地方很远。那段时间我习惯性的厌倦生活和工作的毛病又犯了。我寝食不安,浑身瘙痒,在办公室里总是横眉冷对。那天同事贾琨做完了手头的工作,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溜溜达达,和女同事的眼光对上时,就如往常一样嘴角翘上去,色迷迷地笑笑。我眼不见心不烦低头干自己的事。当他行进到我的桌子前时,发现我表情严峻地坐着,在电脑上用穷凶极恶的颜色画一些奇怪的小图,眼睛直勾勾的,对他视若无睹。他的“与生俱来”的怜香惜玉的劲头儿又上来了,他义正严词对我说:“舒平平同志,你的小资情调又犯了,又不安心工作了。让我握一下你冰凉的小手吧。”说完,把一张大熊掌伸过来,不由分说地抓住了我的手。我的手确实很凉,而他的手粘糊糊,汗津津的,令人恶心。我大声叫起来:“你干什么了?手上怎么粘的。洗洗干净去!”引得周围一阵狂笑。大家笑得姿态各异,好象各有好笑的事,一直在心中酝酿着,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或者是被注射了一种集体狂笑疫苗,定时发作。男的都笑得肆无忌惮,女的一般开始都笑得很压抑,后来便发出一阵阵类似抽泣或断气般的让人提心吊胆的声响。连经理都从小办公室里伸出脑袋,做莫名其妙状瞪了每个人一眼。我感到非常解气。贾琨沾便宜没够吃亏难受的毛病也该改改了,单位里哪个女的没被他随便拉过手呢?谁都不好说什么。平时都是好同事,谈起工作来一副把工作当成家事以天下为己任的认真派头,配着套在笔挺西装里的身躯,显得人模狗样。为了保持表面一片和谐的同志气氛,谁都不会去告他“性骚扰”,也没有人让他下不来台。如果你反应过激,还会被别人认为“假纯”“装嫩”。但是——我在心中例数贾琨的种种不是,心情无比激动,我突然站起来,冲着贾琨办公桌的方向喊:“贾琨,你别整天装傻冲楞地沾女的便宜,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我的神秘的爱人,我就是这样奋不顾身地离开我的工作岗位的,在最后关头我破坏了公众眼里的纯情玉女形象。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留那种带刘海的直长发。在大家冲我投来惊异的一瞥时,我终于明白我需要的就是这个——揭开羊皮,变成一头狼。我朝思暮想脱离这个可恶的集体,但我无能为力自觉和它脱离关系。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象一条鱼一样在同事老板客户之间游弋,和他们相处得就象亲人一样。我如何张口说,我不干了,我烦了之类的话呢?我必定要为我的选择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来避免在他们怜惜的注视中接受无法承受的安慰。我不需要他们的同情,该同情的是他们,我要把假惺惺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得粉碎。他们何尝又不明白呢?我竖起浑身的刺,省得他们靠近我,灌输给我一些貌似合理的道理。
今天的阳光明媚,好象一把金灿灿的稻谷洒落在了无生气的灰色屋顶,已经是冬天了,雪也下了好几场。我是春天来的,那时风儿轻柔,我的心情和春天香艳的花儿一起绽放。我高高地扬起手,把一切安稳的中规中矩的饱受赞扬的传统全部抛弃,然后对城市背转过身去,站在过去生活的反面,拿起了枪杆一样的笔。我终于觉得我有资格和力量写作了。
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第一篇小说的问世,我有话要说,然而我低估了写作的艰难。在电脑前面我比电脑更加安静,我的过于灵巧的手指半天等不到一个敲击的命令。我枯坐在那里,定格在一扇四方的窗户中间,以手扶腮或者把蜷曲起的手指久久地放在键盘上,发呆,思考,等待所谓的灵感。我的接受信号的四通八达的感官失灵了吗?多少次不期而至的灵感如今在远方的城市上空飘扬,却不肯降落在我的窗前,我的伸手可及之处。
我的神秘的爱人,我的生活龟缩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我孤独而自在,连视野也很少受到污染。在静谧的时刻,偶尔我会打开头颅,让灵魂出窍狂欢。她在这几平米的空间肆意奔驰,她纤弱的身形在空中尽情舞蹈盘旋,如同点燃天空的焰火。这时,一切声响都小了下去,我只听到你的衣裾悉悉梭梭地滑过屋角,然后你清癯苍白的面庞便出现了,水波纹一样浮动着,待我伸手去摸时,一无所有。我缩回手时,你又出现了。你一定如同我一样有一颗不灭的灵魂。可以吗?我把你叫做神秘的爱人。恍惚中,你出现了,恍惚中,你又倏而消逝了,让我怀疑这半年幽闭的生活使我产生了幻觉。
幸福大街十五号,灰长巷子里的院落中的一个。我住在东厢房,窗朝西,窗下放置着宽大而斑驳的书桌。你永远不会看到我伏案疾书的样子,我只是隔很久才轻敲一下键盘,以此粉碎我心中的一点点忧虑。在每个傍晚来临之际我和阳光拥抱,然后阳光一点点暗淡下去,和我的心一同跌落到海底。我惧怕黑夜的降临,灯光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提醒我睡眠的不可抗拒和一天的一无所获,我也满可以把希望寄托在明天。有很多次确实是这样的,但每当我这样想我内心的力量就退缩一点,我知道长此下去,我会不堪一击。
辞职的当天,任筱琳给我打电话:“舒平平,你也太cool了。你找着新单位了?”我回答:“没有。”“真的假的?你打算干嘛呢?”“没有打算。”“歇了?”“恩。”“傍着大款了 吧。”“没有。”“太酷了,太酷了,比王菲酷多了。她是装的,你是玩儿真的。我服了。”我心想:让我的同事任筱琳去接着干她的狗屁工作去吧,我金盆洗手了。
我走上写作这条路不是偶然的。从小我的作文倍受老师赞赏,几年前随手写的一篇小小说被刊登在了全国发行量数一数二的文学类报纸上,由此归纳而来:我是有写作天赋的。我怎么舍得放弃?我需要的是与世隔绝的环境和心无旁骛的态度,前提是我必须脱离那种由惯性而来的生活。每年的春季,阵发性的,我会对现状产生深深的厌倦,我要离开,掬大捧的时间给自己,把思想和感情诉诸于写作中,小说是我最喜爱的表达方式。它是我与现实抗衡的武器,也是对我毫无保留的栖身之地。
世上总是会有一些神差鬼使般碰巧的事,在我正式办完辞职手续回家的路上,我遇见了我的旧情人宏图。他三步并作两步地横穿马路,我坐在出租车里望风景。这是很有戏剧性的一幕,原来总是他坐的时候多,我站的时候多。他是一个有与众不同生活理想的人,或者说,他的生活理想就是与众不同。他可以坐着喋喋不休五个小时谈他的理想和对未来的展望,我却不能陪他坐五个小时。我站起来,坐下去,再站起来,惦记着旷工要扣多少钱,俯视他虽然年轻却日渐稀疏的头顶。他的屁股却象粘了强力胶一样,这使他修长的上身看上去极其稳固。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我的一切决定都是他那只无形的手圈定的吗,在已经一年多没见他之后?我暗自问自己。此时此刻,我纹丝不动地坐在车里,而他在匆匆地赶路。说实话,坐出租是我对自己的奖赏,总算跑上跑下办完了所有手续,把该交单位的钱交了,把借单位的钱还上,我的积蓄又微薄了一些。我这个人一遇困难和挫折就爱用物质奖励自己,更何况未来还茫茫无期,我的心中非常空虚。就是这样我坐着出租车看见了等候红灯然后穿越人行道的宏图。
我和宏图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新型关系,彼此觉得不错,呆在一起也不错,各过各的也不错。彼此对对方都没什么要求,不见也不想,见面了还挺高兴,做爱也可以,不做爱也可以,不用肢体语言就可以聊得很深入很投机,主要是他在聊我在听。宏图一直是一个无业游民,浪迹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有时在酒吧唱歌,时不常卖出去两张画,有稳定工作的我曾是他的讥笑对象。我暗地里是羡慕他的潇洒自在的,所以我万分高兴在我这样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上能碰上他。他自然很惊讶,我正等他夸奖我两句,他摆摆手说:“我上班了,恢复集体生活。单打独斗太累了,要靠你们年轻人继承我们老一辈的事业了。”开始还以为他在说笑,后来才发现的的确确时过境迁,宏图头发又稀疏了一些,他的生活和我掉了一个位置。我楞了半天,本来打算表白在办公室里气势汹汹扬眉吐气的最后一幕,现在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宏图还劝我呢:“舒平平,你一个女孩瞎凑什么热闹呢?踏踏实实的吧。”宏图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常常为女人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鸣不平,不把女人看作一个弱智群体。他这一句话立刻让我怀疑这还是不是我认识的宏图了。
我希望宏图帮我找个房子,宏图说太巧了,他认识的一个叫吴前的哥们儿那儿刚空出一间房子,远点儿,简陋点儿,便宜,是吴前的亲戚的,和他们合住一个院子,人家要求要一个安静的房客。我说:“我肯定安静。安静得吓死他们,让他们怀疑我是不是断了气。”我咯咯地笑笑,掩饰近几天来我在语言风格上的变化,变得特别通俗和嘲弄,特别象过去的宏图。
我的理想实现得如此顺利,这多亏我遇上了已经叛变了的宏图。三月二十日我乘坐的黄色小面的出现在幸福大街的街口,吴前说好了来接我。我盯着街口的一个小黑点,看它由小变大,最后变成一个瘦弱的男人。他立得和身边的树干一样笔直,戴一幅深度的近视眼镜。我把头伸出窗外,向他挥手,他居然没有反应,我只得大喝一声:“吴前。你是吴前吗?”
那个瘦男人就是吴前,我也自我介绍我就是那个要来租房的舒平平。敏感的我注意到吴前掩饰了一丝惊异,虽然我们接上了头,但他对于的我的某种想象破碎了。是什么呢?这我也不怪他,我相貌平平,不是令男人想入非非的那种女人。
尽管如此,下车时吴前为我殷勤地打开车门,见我卯足了力气去拖那两只大箱子就说:“你下来吧。我帮你拿。”我笑了笑,说“没事儿,不重。”又龇牙咧嘴去搬箱子。吴前乐了:“还挺会逞能的。让开。”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抢我手中的箱子。我撒手在一旁,感激地看着他。他举重若轻地搬下箱子,头也不抬,自说自话道:“真要在这儿安家呀?这么重。是跟家里吵架了吧?”我讨厌他的这种自做多情的大哥作风,心想:“宏图没告诉他我是为写作而来的吗?作家不敢当,说是写小说的总可以吧。宏图别是什么都没说吧。”
我的神秘的爱人,我在不知不觉中向你靠近。我跋涉过整个城市,拎着两大箱子的书。我在马路边招手拦了五辆小面,第六辆才同意拉我来偏远的幸福大街。在家里我跟父母费尽口舌,解释我并不是对他们不满。我只是需要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写作。我有一个所谓白领的工作,是父母和邻居闲聊时的骄傲。尽管他们也注意到我时常空有一副躯壳,神游千里之外,但他们没有料到我会放弃饭碗,一门心思在“歪门邪道”上。我是为写作而来的,我抛弃了城市,远离父母,来到这荒郊野岭,孤身一人。
房子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砖墙土地,赤裸裸地透着简陋。窗倒是玻璃窗,幸亏不是纸糊的一捅就破。“卧室”和“客厅”隔开,中间隔墙整整齐齐修了一半,另一半就豁然开朗着。没门,一根生锈的铁杆横据在门洞上方,挂着丝丝缕缕的布条。
房东是个涂脂抹粉的半老徐娘,带我在屋里走了一圈,告诉我这屋子怎么好怎么养人:“这屋子接地气啊。你们在城里住惯的刚开始可能觉着不方便,时间长了就离不开啦。搬到别的地方都觉得不舒服。上一个房客啊——”房东若无其事地把眼光扫过我,停留在丝丝缕缕的布条上,“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住了五年呢!”说完,她踮起脚尖去撕那些碎布条。我说:“不用,我自己来打扫吧。”房东不肯走,跟我说了一通注意事项,八要八不要,我都一口应承下来。房东说:“我一看到你就觉得放心。”“哦。”我附和,打开箱子,唯愿房东和吴前赶快走,好清净清净。房东不识相,靠墙站着,好象古树生了根。她把又黑又肥的脚从拖鞋里伸出来,俯下身挠了挠脚心,又开口了:“我知道你们城里人都讲究个隐私什么的,但我是房东,我得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心中一喜,用余光扫了一眼半天没说话的吴前,我清清楚楚地告诉房东:“我是写小说的。”
我的神秘的爱人,当他们走后,我站在屋子的正中央,张开双臂,仰起头,两眼微闭,房子就慢慢地旋转起来,速度越来越快,令我头晕目眩。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有自己的家了,有房顶和四壁以及坚实的土地。它如同一个闪亮的贝壳,静静地卧在幸福大街的某个角落,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我都将看见它无所不在的温柔的光芒。我热火朝天地收拾了房间,把被褥铺上,把桌布铺上,把一些小摆设放在合适的位置。这样做后,我感到这个新家又亲切了许多,我真的无法确定我将会在这里住多久。我想起房东的话:“上一个房客啊——,跟你一样也是一个人,住了五年呢。”
那以后,我就感到有一个在这里住了五年的人陪伴在我的左右。我无从猜想他的性别和年龄的大小,我只知道他就在我的身边,无时不刻。我一厢情愿地想象他是一个男人,苍白而消瘦,他的目光如炬,头发纤细而蓬乱。他独自一人在这里度过了很多时光。他是做什么的呢?他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我的写作经历了意想不到的艰难。起初,我希望用一种最传统的方式,纸和笔写作。一计不成,我鸟枪换炮把纸笔换成了电脑。有好几个星期,我只是在规定时间坐到电脑前,脑袋里却和电脑屏幕一样空白一片。后来,我干脆放弃了构思,随意敲出几个拼音的组合,我想象这就象我随意翻开一本字典,我挑选出几个词,写下来,当我有足够的词时,我在它们中间寻找可能的联系,我把这叫做我的“拼词游戏”。我在词与词之间终于寻找到一线希望,故事和人物在我的脑中渐趋完整。
我就这样写了几篇小说,打印出来,装在大个的牛皮纸信封里,郑重地把它们投入信箱,可我无法再集中精神开始我的下一篇创作。我在等待中度日。这时夏天来了。
在我等待的日子里,我开始走出房门和房东聊天。一整个春天我看见她在院子里进进出出,买菜,接孩子,或者干些其它的事情。她很少和她的丈夫一同出现,她的丈夫和我一样是个安静的人。
“我还以为你一直不在呢。”房东主动和我答茬。她是知道我在的。
“你不是喜欢安静的吗?”我反问。
“安静好,还是安静好。你来之前我招了两个小伙子住进来,是吴前的朋友,天天来一大帮人喝酒喝到一两点。我可受不了。还好,两个星期后就走人了。房租倒给了我一个月的。”
我感到有些纳闷,“你不是说有一个人独自在这儿住了五年吗?”
房东肯定地点点头,居然叹了一口气,眼睛里似有晶莹的物质闪烁,语气也沉重了些:“是个好小伙子啊!他在那两个人之前走的。”房东的声音越来越虚弱。
我心头一惊,猜测被证实了,曾经有一个年轻男人在这里独自住了五年。
我的投稿杳无音信,只好重新打起精神写作。有时我真希望弄点什么植物要不干脆是化学合成的玩意儿,在我身体中引起一系列化学反应,刺激刺激我麻木的神经和大脑沟回,自动把小说最起码把小说的创意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输送给我。我想起宏图的话:“……单打独斗太累了,我恢复集体生活了……”现在我是一个没有集体的人,不是我被集体抛弃了,而是我抛弃了集体。
吴前是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我的情景的:他站在暮色苍茫的街口迎接我,而我坐在一辆破旧不堪风尘仆仆的面的上,脸上写着疲惫,厌倦和星星点点的希望,整个脑袋探出窗口,听凭脖子的转动而转动,象一只孤独无助的狗,找寻记忆中的主人和家。我还听到吴前提起这样一个版本:在雨后泥泞干结的土路上,随着黄色面的的颠簸,舒平平的头颅如同一只波涛中的西瓜漂浮在车身侧面,时隐时现。
在没有思路时,我一遍遍回想吴前描述的场面。吴前是怎么出现在幸福大街路口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我站在吴前的位置上,看自己由远及近而来,镜头被拉得很长,最后是一个大特写。我的脸上写着所有的内容:我为何而来。有时我在自己脸上也会发现一点点的迷惘。
我已经很久不照镜子了。我带了一面小圆镜子,但我从来不去看它,它被藏在柜子的深处,被一块谁遗落的蓝地白花的蜡染布包裹着。我相信一接触外部的空气便会让我写作的愿望通通氧化掉。我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在我不熟悉的城市的边缘,一条大街的某一个角落,谨小慎微地地躲避着一切把我送回原来生活的东西。它们是无孔不入的细菌,令我战栗。我避免朝那个方向眺望。
在我读到的作家传记里,他们都曾收到无数的退稿信。时代变了,没有退稿信这回事了。我不能肯定问题是出在邮局身上,还是我的信寄到了却从来就没有被打开过,亦或在被阅读的过程中遭到了无情的嘲笑和唾弃。当然我也幻想过这样的情景:我的小说被编辑们传阅,或者某个编辑看了个开头便欲罢不能,挑灯夜读。
我已经不能继续我的下一篇小说,头脑中充斥着寄出的小说颠沛流离的命运,我是编导兼剪辑,把一部关于小说的细致入微的记录片搞得一团凌乱,破碎的镜头刀光剑影般闪回,还有大量琐碎混乱意义不清的有如谶语般的旁白,它们割裂我的神经,令我坐卧不安。
有一天,房东在外面叫我:“小舒,你也该出来散散心,这样整天一个人要闷出毛病来。”我没说话。房东又叫。我还是不说话。她竟然急了,过来敲我的门,嘴里自言自语道:“千万别想不开,怎么写小说的都这么古怪,千万别出人命……”我哗啦一下打开房门,光线如千万支白晃晃的暗器般齐齐向我射来,我抬起手来遮了遮眼睛。房东“哎呀”喊了一声,“你吓死我了,这么多天不出来,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能有什么事?”我定定神反问。“出来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天天闷着,就算不是想不开,对身体也不好。”我问:“还有哪个写小说的人也这么古怪?”房东犹豫了一下说:“就是在这里住了五年的那个。”说完,就走了。
我回身环顾这间平淡无奇的房间,把房门关上,幽暗的光线似乎更适合它,我的眼睛也如同猫一般在黑夜里更加熠熠闪光。这个狭小的空间在白天是单纯的,由一堵墙一分为二,我在这间写作在那间睡觉。此时,那堵墙晶莹剔透,坚硬的棱角融化了,我分明看到你,我的神秘的爱人,你蜷身坐在那里,手托下巴,在凝神向我望着,你的目光轻柔而忧郁,好象层层的花瓣,让我感到一往无前的安全。
我的神秘的爱人,我感觉到了你的温润如雨丝般的呼吸,你站起身来,在这个房间的角角落落时走时停,你的模样符合我的想象,苍白而消瘦,头发纤细而蓬乱,目光如炬。我设想着和你交谈。
我问:“你是谁?我怎么好象见过你。”
“对,我们彼此见过。”
“我们从前见过吗?在哪里?”
“在你的脑海里,在我的脑海里。”
“也许我们真的是见过的,在街上,公园,电影院或者学校,我们擦肩走过,也许我跟你很熟,我知道你的名字。但我现在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也许。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记得我们彼此见过。不是吗?”
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把我埋没在无比惬意的海潮之中。我苦思冥想我究竟在哪里见过他,时间,地点,光线,空气中的味道,一无所获,但我和他曾经见过面这个事实却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人物渐渐地凸现出来,背景模糊下去,最后变成了一张白纸上的炭素肖像画。
我的小说不见起色,头痛病却一日胜似一日。大概是由于久居室内,我的苍白引来吴前惊骇的表情。他路过这里,顺便给我带来宏图的消息:“宏图结婚了。你不去看看吗?”我摇摇头。吴前拘谨地在我绝无仅有的方木凳上坐下,点了一支烟。他说:“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你有工作有父母。好多外地漂来的写小说的羡慕你还来不及呢。”我问吴前:“原来这里住着一个写小说的吗?”吴前点点头,“死啦。”“怎么死的?”“病死的。”
我对这年的元旦记忆深刻,父母去串亲戚,我在家手执电视遥控器百无聊赖翻来覆去地换台,最后一个鲜血淋漓的画面把我吸引住了:在一家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里,摄像机对准了作为某电视台编导的妻子的产妇生产的场面,画面不稳定,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看来摄影师对拍摄此类新鲜事物也没有把握。产妇声嘶力竭的喊叫被话外音代替,人们只能从她扭曲的脸部感受她此刻无以伦比的痛苦和幸福。相对于婴儿的出世,我更偏爱产妇饱受折磨而又容光焕发的脸,她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猜想现在我就具有一张产妇一样爱恨交加的脸。
我的神秘的爱人,我以为有一天我会抚摩你,你的苍白的胸膛,冰凉的肌肤,你的芬芳的嘴唇,但如今我才知道我们竟是远隔天涯了。我坐在屋子里,屏息等你,哪里有任何另一个人的证明呢?除了我心跳的声音,万籁俱寂。
我问房东有没有止痛的药,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和她说话,房租预先交了半年的,我始终保持着一种我们两清了的姿态,避免从她身上传染上令我不适的病菌。房东关切地问我:“怎么了?年纪轻轻的。”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头痛,懒得去看病。”房东如临大敌:“头痛可不是小病,弄不好要死人的。你还是去看看吧。”我讨厌她的大惊小怪,但我也竖起耳朵来听进去了她嘟哝的后半句话:“怎么住这间房子的都头痛。”
我的神秘的爱人,不能否认,我是有一些嫉恨你,你扰乱了我的生活,使我花更多的时间冥想,回忆和遗忘。我也变得更加警觉,仿佛全身心浸泡在无边的海水里,静静地等待起伏的海浪带给我你在海洋的另一边微微的颤动。我们慢慢地熟悉了,拉进了身体的距离。当我写作的时候,你从我的背后俯身过来,有时你会把手搭在我左侧的肩膀上,轻轻地按一下,我立刻就心神不宁了。你是一剂沉鱼落雁的毒药,让我牵肠挂肚,无法从容。我睡觉的时候,你爬上床来,侧躺在我身边。有时我半夜醒来,恰巧看见树影摇动月光映在你的大理石般的脸颊上,你肃穆得象一千年前的雕像。
我的神秘的爱人,我渴望在房间里找到你的手稿,在墙上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我找到了,那显然只是一个题目:幸福大街十五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由于你变得不只是一个门牌指示的空洞洞的居所,而象是一个无遮无拦的舞台,我努力躲到幕后,幕布却一层一层地拉开,丝毫不理会我东躲西藏,追光跟着我时,你在哪里呢?我的神秘的爱 人!
我头痛欲裂,生理上的痛苦已经严重影响我的写作,我的投稿依旧一去无回。我习惯了。每当我因此情绪稍有低落的时候,我阅读一个著名作家的传记,他写作八年,稿纸装了两麻袋才发表第一篇小说。我这区区半年,又何足挂齿呢?当然,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维持不了太久,有半个多月了,我靠止痛片和镇静类药物打发日子。
过几天是母亲的生日,我已经太久没出去,从这个叫做幸福大街十五号的地方,这条曲折的街,城市的边缘。每天夜里有一束巨大的激光从城市的方向升起,我曾经在那个全市最大的迪厅跳过舞。那时,我是一个快乐的青年,偶尔有些无伤大雅的惆怅,我和宏图去过那里,和别的情人也去过。我们抽烟喝酒跳舞摇头,然后我们借着酒精去什么地方做爱,第二天我披挂上整齐的职业装,一丝不乱笑容端庄地走进办公室。同事贾琨有时会摸我的手,很礼貌的。他说:“我给你看看手相吧。”就把我的手捏住了。我在心里笑,性变态吧,摸摸手就能达到高潮。贾琨看我满不在乎无所谓的样子兴味索然,他接着对坐我旁边的项岚说:“我给你看看吧。”项岚就把手乖乖地递上去。每天春天我都发作一次颠覆现实症,突然对乐在其中的事物感到无比反感。所以一到春天我会花光积攒了一年的假期出去旅游,一次两个星期的旅游大概是对付我的疾病的一年的剂量。今年我怎么突然对早已熟识的一切无法忍受了呢?我努力回想半年前的情景,伸出手去,凝视掌心,妄图让过去的因果在上面停留,但我的手掌空空,一无所有。
我好象是在等待着什么。我在等待着什么呢?
我的神秘的爱人,那天夜里我看见你站在窗前,这是第一次你的目光不再围绕在我前后左右,你背对着我站着,月光为你描绘出清晰而俊秀的轮廓。我就这样缓缓地靠近你,站在你的身边。我希望自己是一颗被风吹落在你脚边的种子,长成小树依偎着你。我顺着你的目光望去,你的目光很长很长,在你的目光尽头有一本翻开的书在风中哗哗作响。然后你转过身来,你的目光象昙花一样开放又骤然凋谢,随后你隐身而去,留下匆匆的感伤的一瞥。
我失眠了。我怀疑我得了什么精神方面的疾病,他们把我这样的病例称之为“癔想症”。
第二天,我想起那本在风中哗哗作响的书,以前我从来没见过它。现在,它就安详地躺在我的窗台上,如同我的爱人神秘地出现。它散发着莹莹的蓝光,好象一块千年的寒冰。我双手捧起它,这是一本众所周知的文学杂志,那翻开的一页是一篇小说,名字叫作“幸福大街十五号”,开头写道:
我又一次看见了你,我的神秘的爱人。你的微仰的头颅,环抱在胸前的手,嘲弄的嘴角和寒星般的眼眸,我不敢向你所在的地方靠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坐在电脑前,生怕又一次将你错过。你仿佛是浮光中的一点幻影,只在某一个无法揣测的角度出现。有时我会碰巧看到你,更多的时候,你是我心中的一个影像,我用心的热度一点点靠近你。我惊愕万分,匆匆地翻到小说的结尾,还来不及看,就被后记中的作者简介吸引。
作者简介:佚名(1970-1999),小说写于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