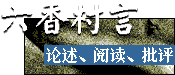网络时代经典写作的命运
1.从一杯水开始
一位自己给自己取名为马格利特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在谈到他的作品《黑格尔的节日》时曾说:“我最近的一副画开始于这么一个问题,即怎样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画出一杯水?怎样以一种古怪、专横、纤弱但又是天才的方式来描绘一杯水?”实际上,在任何“经典的”艺术家那里, 眼前的、习见的事物,都不能按照它的原初模样搬进作品世界,也不可能依它的原貌有如照相一般被挪进艺术空间。诚如弗朗索瓦·达高涅在评价加斯东·巴什拉所说:“死死盯住原初物质不放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此,这个代价就是牺牲艺术的本真内涵。相对于实存世界,作品从来都具有陌生化的面孔,都应该而且必须具备陌生化的性质,哪怕是水这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事物。李白诗曰:“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李白那杯价值远超“万言”的“水”,和马格利特那杯“水”一样,无论和我们天天都在饮用、每天都在荡涤我们身上污垢的液体何其相似,都已经不再是我们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水了,它业已组成了另一个有关水的世界,或者说,它本身就是那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基本元素不再是氢(H)和氧(O),而是其他元素;这个有关水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线条、形状、疆域、多变的脾气、性质、呼吸、生殖、青草、土地、阳光和跳动的星辰。它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不依赖任何外在事物的完整世界,不像在现实时空中,水只是构成实存世界众多事物中的一种。
在此,我们有必要承认罗兰·巴尔特看法的正确性:任何现实世界当中的事物,就它与人的关系而言,从来都存在着三重面貌——真实的、意象的和书写的。 的确,“意象的”水,才是马格利特和李白“书写的”水的基本来源——书写形态的水和“真实的”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不需要多重中介就能进行相互转换的关系。热·热奈特在评价柏拉图的模仿说时,有过这样的话,完全可以和巴尔特的看法联系在一起:“柏拉图把模仿与叙事当成完全模仿和不完全模仿对立起来;但是(正如柏拉图本人在《克拉蒂勒》中所指出的那样),完全模仿已不是模仿,而是事物本身。说到最后,唯一的模仿是不完全的模仿。模仿即叙事。” 不能说热奈特说得不正确(当然也不全正确),问题是:这种叙事和实存的事物当真有那么多直接关联吗?
2.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报道
犹太文学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叙事体作品的建构》里,就“文学即报道”发出了一个明知故问的疑问: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荷马开始写史诗的时候,当但丁穿越地狱,当堂吉诃德骑在马上和桑丘·潘沙骑驴跟在其后的时候——这里也仅仅是形式上的报道吗?在论述性的文字还没有来得及分段之前,德布林就马上暗示说,那都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报道,和真实的、眼前的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无论叙事作品对事件的报道形式和报纸上的报道形式有着怎样惊人的相似性。 有趣的是,多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回答文学(即巴尔特意义上的“书写的”)与生活(即巴尔特意义上的“真实的”)的关系问题时,毫不犹豫地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答案: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可是,这种理论又该怎样回答马格利特和李白的“水”以及德布林的“报道”呢?在此,我们一贯擅长查漏补缺、拆了帽子补裤裆的文学理论,开出了一剂特殊的两分法药方,以为立马就会起到药到病除的功效:它把来源于生活叫做再现,最明确的例证据传就是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描写;把高于生活唤做表现,自以为有效的证据就是诸如马格利特的水那一类的东西。在此,我们倒不妨听听在野党的意见。有关前一点,伊格尔顿在评价罗兰·巴尔特改写巴尔扎克的《萨拉西纳》而成的狂欢式作品《S/Z》时说:“《萨拉西纳》被证明是现实主义一个‘有限度的文本’。这部作品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现在看来危机四伏:整部作品充斥着败笔、性别的阉割、资本家财富来源的不明不白,以及在固定的男女情爱的角色中出现的大漏洞。” 有关后一点,早在几十年前,钱钟书先生就将之嘲讽为“捏造的”和“摸象派”。钱先生揶揄说,我们就取它“捏”着鼻头向壁虚“造”和瞎子摸象的意思。 难道还不好玩吗?
我们就这样长时间误解了我们的文学与艺术。实际上,文学和其他艺术一样,最大的魅力之一,根本就不在于它是否再现了世界,也不在于它是否表现了生活,而在于它始终致力于创造和建构一种与实存世界毫无直接联系的整体世界和整体生活——无论作品中的世界、生活,看上去和我们眼前的、习见的、理所当然呈现出如此这般模样的世界与生活多么相似。它永远是“书写的”世界与生活,只和“意象的”世界与生活发生关系。文学赞同德布林为它下的定义,因为后者充分维护了文学的尊严,没有把文学降低为生活的摹本、二等品与下士的地位——文学就是自己完整世界里的实体和总司令:它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报道。德布林假设过,如果有一位作家向他朗读最近写成的小说,他不会相信该作家作品里的任何一句话会和我们现实时空里发生的任何事件相等同。而这恰恰是欣赏文学的首要前提。德布林说得好极了,这正是我和那位作家之间达成的基本默契。 对此有着更为明确、更为精辟表达的,是我所欣赏的一位中国哲学家:艺术“不是思考的对象,而是像神一样的另一个世界,当然艺术不是让我们去相信的,而是让我们去经验那种本来不可能经验到的世界的完整性,”文学、艺术世界很完美地描绘出了一个“世界所可能有的那种完整性”。 经验当然早已告诉了我们,完整世界、完整生活,对于必死的、只能此时此刻存在的个体之人,根本就不可想象:谁敢说他在现实世界上经验了世界的完整性、经历过所有可能的生活(即“完整的生活”)呢?
3.碎片与“全”
人在完整生活、整体世界面前,永远都只能是碎片(fragment)。但人(无论他作为文学创作者还是欣赏者)对于完整的渴望,始终在推动着他妄图以一己之碎片来把握完整(“全”)的巨大野心。 屈原在《天问》中以打机关枪和放排炮的方式,一口气问出了“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等诸如此类的上百个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经典证据。“全”只属于上帝,正如《圣经》所说:“一切来自你,一切通过你,一切在你之中”; 也正如上帝洋洋得意宣称的那样:只有爷爷我才能“充塞于天地之间”。 “全”不属于海德格尔所谓“此在”(Dasein)的人类。但人类的努力,终于把这一痴心妄想转化为现实,那就是我们早已看到却又惨遭我们误解的文学和艺术。正是文学和其他艺术一起,向我们联合报道了另一个既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又寄存于我们的意识之内的完整世界、整体生活依然存在的消息。它向我们详细报道了诸如马格利特的“杯水世界”中一切可能的情报。文学就是有关一个完整世界、完整生活的消息树。它使碎片状态的人有可能经验上帝的时空,它使人有可能在特定的时刻直接等同于上帝,但又绝不等同于“见性成悟,直指本心”的刹那式永恒。文学不玩这种吊诡的禅学妖术。
本着这样的目标,文学总是现实生活、现实世界的反对者和否定者。文学那种来源于人性深处的目的,宣告了再现说和表现说的破产:文学的目标和目标所要求的方法论,也超越于任何型号的再现说和表现说之上。文学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一种实存的事物,任何包纳于文学形式之中的实存事物,都呈现出罗兰·巴尔特所谓的书写形态,它只对文学建构出的完整世界有效。正如我们不能想象要是孙悟空从《西游记》走出,真的进入了上海的地铁、北京的王府井商场、巴黎艾菲尔铁塔上的咖啡馆,我们也无法想象,现实中的人进驻文学空间还会不会和现实中的人有相同的心脏和肠胃。在所有对于文学的有名误解中,柏拉图是最有名也最愚蠢的一个。他只看见诗人在恬不知耻地说谎,却没有观察到诗人和他一样,也在建构一种完整的、具有创生意义的世界——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学世界,都是一次性的,它绝不可能被重复,对于创造者本人,它永远都是初始性的,永远都具有“上帝说要有光”、“事情就这样成了”的特性。
面对这样的世界,走进这样的生活,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可怜虫”(爱因斯坦语)、悲惨的碎片,总是显得心情复杂。一方面我们会为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居然能够经历一次完整的世界与生活感到满足、感到惬意;另一方面,我们尽管看到了它的全景,却对它的理解呈现出千差万别、五花八门的面貌。长期以来,人们对“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成因,给出了“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解答(我当然不反对这个答案), 假如我们转换一下思路,把该结果的出现看成是碎片在整体(“全”)面前的卑微,也许我们更能体会到文学和艺术的力量——它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证实,我们卑微的碎片身份尽管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全”,也可以去经历各种各样以致于无穷的可能世界与可能生活,但它最终更加深刻地证明了我们的卑微与渺小。碎片在“全”面前,永远只能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摸象派”:摸见象腿就说是柱子,摸见象耳就说是扇子,而摸见象尾呢,那就只好叫做鞭子了……。就这样,文学艺术既让我们感到骄傲,又让我们感到沮丧。但这种骄傲和沮丧的双重性,与各种型号的再现说和表现说都没有任何关系,它只和人性深处碎片对“全”的渴望,以及渴望必然派生出的摸象派密切相关。完成这一渴望的写作技术根本就不是什么再现或表现,虽然看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情。如果文学真的来源于生活(更为正确的看法刚好相反),文学还能再现出和表现出一种(仅仅只有现存的世界这一种)完整的世界和生活吗?恐怕世界上还没有足够大的纸张来承载它呢。
4.虚构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从前所有人的集合物累积出来的结果:我们的手、脚以致于每一个器官都是无数年进化的成果,我们头脑里任何一个现成的观念也同样是别人的产物。我们身上的所有一切都不为我们所独具:每一个人身上的所有成分都既属于自己,又属于他人,既是现实的、血肉的,又是历史的、死去的。就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虚构了。我们都是虚构的人。我们同时都是他人和历史的影子,我们的血肉之躯、看起来属于我们独有的器官和意识,只是在更加深刻地证实我们被虚构的命运。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它的发生,远在拨开迷雾看见青天的初民以远。从一开始也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逃脱这一宿命。要想把自己从虚构的危险身份中拯救出来,是每一个H·布鲁姆意义上的“强力诗人”的天然任务 :他通过自己的创造,通过对不同于前人创造出的完整世界、完整生活的创造和建设性努力,使自己真正拥有独具的品质,拥有新的、不同于任何人的库存,从而成为一个现实的人、实存的人,一个新人——尽管无论他怎样努力,他独具的东西和虚构他的东西相比都是如此之少。这既是文学写作的内在律令,也是每一个不想被虚构的作家的天然使命。
从虚构的人到实存的人的转换,只有通过创造;作家的创造,只是完成这一转换的所有可能创造形式中的一种。正是从这里,我们能够再一次证明米歇尔·福科的著名论点(福科的思维言路及例证当然与此不同):历史是断裂的。因为每一个把自己从虚构的危险境地拖曳出来的作家,从来都以个体形式出现,他和那些始终被虚构的人、暂时被虚构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真正的文学史永远都是断裂的,这种断裂的形象有如一座座拔地而起、互不相连的山峦组成的长长序列。我们之所以把文学史看成是连续的,可能的原因之一就存在于那些始终被虚构的人身上:他们接受了强力诗人们的独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甚至把独创成果弄成了常识。就是在这个习见的过程中,始终被虚构的人填充了一座座互不相连的山峰之间的空白和距离,使得历史看上去真像是连续的一样。庸众的双腿对历史的唯一贡献就在这里。在此,有两种情况值得考虑:填充者始终是在地面行走,不可能站在半山腰,更不用说会到达山顶;填充者并不会因为他的填充行为而改变他被虚构的面貌与神情——他在继续着被虚构的命运:他只充当了碎片在“全”面前的观看者角色,他只为再一次被创造出来的整体世界、整体生活所吸引、所掌握、所捕获、所控制、所奴役,完全缺乏把自己从被虚构境地拖曳出来的能力甚至冲动。
5.向着虚无出发……
完整的世界就是虚构的世界,完整的生活就是虚构的生活,因为除了上帝(我衷心祝愿他能够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它们中间:它们只能出现在纸面上。文学(当然也包括其他艺术)永远站在虚构一边。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存在一种叫做现实主义的鬼画符。这种看起来可以被轻易撕掉的世界与生活——希特勒、秦始皇和中国的红卫兵最能理解这中间的要诀——其实具有庞大的危险性,因为它会从两个方面把写作者,那个试图走出虚构身份的“强力诗人”带上被毁灭的道路。一方面,虚构的人身上已经有了太多别人创造出的完整世界、完整生活,他得和它们进行殊死搏斗,一如布鲁姆说过的那样(马格利特对“水”发出的疑问,就是这种搏斗的一个小例证);另一方面,虚构的世界始终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它的无边无际,它的不知从何开始不知到何处结束,始终在以它的恐怖神情惊吓那个试图扔掉虚构身份的人。它同样要求作家和它进行殊死搏斗。每当战争结束,我们往往会看到,只会有一个残缺不全、浑身硝烟的胜利者。在这里,曾经臭名昭著的非此即彼陡然又回光返照式地变作了香饽饽。
事情总是这样:所有旨在挣脱虚构身份的写作,在开始的时候总是无中生有的,它从第一个字开始,通过和词语商量,已经把写作者置入了广大虚空之中,置入了漫长的虚无航程之中。一般说来,写作者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的最终宿营地在哪里。即使他预先设定了航船的抛锚地,写作的天然目标、它要求制造出完整世界的内在律令,依然会很不象话地将这个不想被虚构的危险分子,带向一片片充满着暗礁的未知领域。他预定的抛锚地经常被证明是错误的。要完成对整体世界的构筑,迷路、触礁、充当没有“星期五”的鲁滨逊甚至是道渴而死化为邓林的夸父,就是可以想见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写作就是哥伦布航海,他以为他到达了印度,可后人很快就会向他喊:喂,哥们,那是美洲,你见到的都是些说鸟语的棕色人种,而不是释迦牟尼和菩提树的国土!
6.快乐地认命吧……
希望以上理解和论述,能够说明网络文学兴起之前文学写作(我们不妨将之唤做“经典写作”)的一般特征,尽管它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危言耸听,对于网络文学却不见得有效。实际上,互联网的出现,正在逐渐蚕食上述特征,并且以最终废除上述特征为暗中指归。“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陈寅恪《赠吴雨生》)这差不多正是对经典写作在网络时代命运底蕴的较好描述了。几十年前,当电影艺术刚刚探出头来,有着浓厚怀旧倾向的W·本雅明就惊呼过,电影所代表的复制艺术(Copy-Art),正在使艺术品的韵味和原真性一步步消失殆尽。 我们不能想象,要是这位“运气奇差”(汉娜·阿伦特语)的犹太人活到今天,看到下载艺术(Download-Art)已经以它突飞猛进、充满着摇滚精神的姿势迎面向我们撞来时,该会做何表情。在本雅明心目中,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本来面目(原真性),都有它独一无二、即时即地的不可替代性(韵味)。放在此处的语境,我们满可以把它误读为:所谓原真性和韵味,就是作家通过创造一个不同于他人创造出的那种完整世界,从而在把自己从被虚构的境地拖曳为实存的人的过程中,赋予被造物以独特秉性。在此行程中,作家永远都是孤独的,他是有了“星期五”之前的鲁滨逊,是只身一人逐日的夸父:他在从事一项孤独的事业——一如海明威所说。但是,William Henry Davies笔下那只孑然一身的蝴蝶,却早已给这些鲁滨逊和夸父们做出来榜样(Example):
发过了感慨以后,让我们再来看看眼前的情况。互联网的出现,为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个与经典写作绝然不同的开放式写作空间,它以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在虚拟的信息平台上,它至少从理论的维度,允许无穷多的写作者同时参与同一件作品的写作。每一个写作者都可以有限度地改变、规定、矫正作品的未来走向。 因此,假如这就是网络文学的真正涵义,那么,网络文学写作就不存在一个固定起点,也不存在一个固定终点。这实际上已经宣布了经典写作构造整体世界与整体生活的努力的全面破产。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方面,无论哪种写作者一开始都是虚构的人,即使是他使用了电脑,仍然逃不出这一宿命;另一方面,由于是直接的、多人的共时创作,用于虚构这些写作者的物质材料,也就不仅来源于前人、历史,一如经典写作者们遇到的情况,更有甚者,还来源于同时参与写作的个体之间——他们在同一时间内互相虚构对方,也同时被对方所虚构。这种虚构是即时即地的,它修改了经典写作者之间互相被虚构那种的方式:前者的作用是致命的,因为在网络文学写作中,只有预先接受了被虚构的命运,你才能参与其中,这是网络文学写作的基本前提之一;而在经典写作中,写作者对来自于同行的虚构力量始终持一种反击的态势,因为他们在进行着独立的、不依赖于旁人的个人写作。
Here's an example from
A butterfly
That on a rough hard rock
Happy can lie ,
Friendless and all alone
On this unsweetened stone.
网络文学写作,一方面宣告了经典写作中挣脱被虚构命运的努力的破产、失效,同时也宣告了,网络文学写作者甘心于被虚构的命运,诚服于被虚构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被允许说,他们直接把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哈姆雷特书写了出来。几乎不需要什么中介,他们的哈姆雷特就可以径直现身。因为网络文学写作从理论上已经取消了写作者和欣赏者的界限:一个人在同一时刻既是写作的人,也是欣赏写作的人,不仅是自己的欣赏者,也同时是他人的写作者:正是这种环环相扣的写作运动提供的摩擦力,才使得网络文学写作空间的巨大开放性能够化为现实。从理论是讲,经典写作那种有头有尾的整一体系(正是在此整一体系中,整体世界才会诞生)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不能把无是无终的巨大开放性看作是整体世界。 因此,网络时代的书写者,对于自己被虚构的命运无动于衷。他们乐于迈动庸众的脚步,不承认还有拔地而起、互不相连、旨在使历史断裂而不是连续的山峰的存在。因为人无力充当这样的高峰,它被认为是一种狂妄的、试图偷窥上帝宝座的自不量力。从这种窃取了经典写作里包纳的创造光芒产生出的伪创造中(无贬义),他们获得了狂欢式的快乐。按照某些论者兴高采烈的话说,从这里出现的,才是真正“快乐的文本”,它无头无尾,几乎怎么都行。于是,接下来的口号也就顺理成章了:让我们快乐地认命吧!
7.“行为艺术”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写作那种可供反复阅读、欣赏的情况在网络写作中将不复存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中的九百九十九个已经死去了,只剩下一个还在此时此地嬉皮笑脸,做抓耳挠腮的快乐状。一位网吧间的万事通先生宣布,网络文学已经使对经典写作欣赏中所包含的“多次性”全面破产了,它已经非常民主地打破了经典写作对读者的霸权主义,因为在网络时代,至少在理论上已经破除了读者和作者的界限。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只能见到一个具体的哈姆雷特,而且,这个人也不需要见到另外的九百九十九个。一个已经足够,也就是说,一次完整的欣赏也已经够多了,同样的快乐出现两次,那刚好就是对于“乏味”的定义。是的,无论这个口号会让一部分人怎样高兴,也无论它会让另一部分人(比如本雅明)如何悲哀,一次性的文学写作(或欣赏)反正已经出现了。网络文学写作的一次性,和经典文学写作的一次性有着不同的所指:前者指向一次性的写作和阅读(既然已经消除了写作者和欣赏者之间的界限),而且写作和阅读往往是重合的,它只意味着在同时进行的写作与欣赏中对写作与欣赏的消费;后者则只意味着一次性地对整体世界、整体生活的创造。马格利特的“水”在经典写作中只能是一次性的写作(否则就是模仿或抄袭了),但它可以被无数次地阅读——九百九十九个哈姆雷特和另一个哈姆雷特同时并在。
阿伦·卡普劳把网络文学写作唤做“即兴写作”,他还非常有趣地将“即兴写作”与日常生活中“用过即扔”的快餐盒相提并论。这个比喻十分贴切。网络文学写作的目的仅仅在于:在共同的、开放的信息平台书写过程中,多人在共时性地把握文本的走向;在相互被虚构的命运中,体会到那种狂欢式的文本愉悦。从这一点上,用过即扔确实是最理想的。说实话,没有必要否定这种即兴写作和它的结果即兴作品,但它和经典写作所倡导的多次性欣赏比起来,毋宁充当了一种卫生巾的角色(无贬义,只是为了形象地说明问题)。
就这样,网络文学遵循着行为艺术的内在律令。行为艺术在此不仅意味着它是即兴的、一次性的,而且意味着,它可以把虚构的瞬时世界快速地拉进实存的世界与生活。这个世界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短暂的整体世界,它和“见性成悟,直指本心”式的刹那永恒有些形似;而消费了这一刹那,整体世界也就土崩瓦解了。这毋宁是在说,虚构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眼前,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能将它唤出,并与我们的实存世界相焊接,它由此制造出了一个中间地带:一边是实存世界,一边是虚构的另一个刹那世界,站在交接点上享受着狂欢快感的妙人儿,就叫做网络写作者。经典写作也能让我们看见这一结果,但它们还是有所区别:网络文学写作的虚构只存在于瞬间,而后者的虚构不仅是长存的,而且它创造出的整体世界,和实存的世界永远没有焊接点——它也许在实存世界之上,也许在实存世界之下,但就是不和实存世界交界。耶亚柯夫·阿甘姆说,通过网络文学的写作,“我们与三分钟前的自我不同了,再过三分钟,我们又变了。”“我试图创造一种不存在的视觉形态为这种看法造型。形象一出现又消失,什么东西都留不住它。” 说得还不明白吗?
8.能指的世界
因此,与网络文学写作根本就不奢求“全”相适应,它也不在乎航程的去向。他们也会碰到虚无——毕竟网络文学写作以它无始无终的开放性,使它营构的世界看上去和实存的世界更加神似,但这种虚无对他们而言是无所谓的,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正是他们寻求快乐的方式:他们不知道自己将会走到什么地方,但意想不到的地方一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景致。所以,他们乐于在写作中遇到虚无,乐于在虚无中迷路,以便得到意外的惊喜。和经典写作的快乐观不一样,网络文学写作的快乐只存在于狂欢之中(变动不居),它以狂欢为快乐定义,也以狂欢为快乐标明了等次和成色。经典写作的快乐产生于表面上的不快乐之中:它在惊恐、焦虑、触礁的危险中体会到虚构整体世界和整体生活(“全”)而产生快乐。它是一种内敛的快乐。
有的论者认为,在网络书写中,到处都是能指的世界,所指将不再对能指起到调控作用。这的确是真实的。正是所指指挥不了能指,才造就了“到哪儿去都成”的漫游式写作、开放式写作。经典写作中,所指处处管制能指,才使写作朝着营构一个完整世界的方向迈进,尽管这个虚构的世界同样是无穷的,但它看上去却又像是有限的一样。如果他们(网络写作者)本来是想去印度(其实根本就没有预设这样的目的地),最后却出人意料地到达了美洲,也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不会像经典写作中受到所指调控的哥伦布那样,迅速返航去向国王报告自己的喜讯。相反,他们仍然将继续向前,以期能到达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美洲。碰见什么就是什么,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根本不在乎“水”是不是一定要以古怪的、纤弱的、天才的模样进入写作空间。因为这只是一个能指的世界。因为这是一个漫游的、漂泊的、并从中产生出一次性快乐的世界。既然用过即扔,那就得尽量长地拖延“用”的时间。
9.赶紧结束
我不知道上述情景全面来临会在哪一天,但我们可以推知,在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年代,这一天不会太过遥远。在网络技术的培养和教育下,注定会诞生一整代全新的、热爱用过即扔的、一次性的行为艺术式的写作者,他们从中将获得不同于经典写作中所能够获得的那种快乐。经典写作对于写作快乐的定义注定将遭到修改,未来文学也将呈现出全然不同于经典文学所具有的那种特征。
经典文学写作在网络时代的命运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整整一代人愿意在写作中甘于他们继续被虚构的命运,经典文学写作的黄昏就已经来到。但这是永远不会走向夜晚的黄昏。甲骨文对“暮”的形象“解释”在这里是有效的:所谓“暮”就是用“人”手从“草丛”抱“日”而出。经典文学写作也有一只手会从草丛中抱出落日,这只手来源于我们心灵的深处:对“全”的渴望。正是仰仗这一点,经典文学永远会把黄昏留住,把从早上到黄昏之间的这一长段时间送给了网络文学。
在《论土地与静息》中,伟大的加斯东·巴什拉说,经典写作中的诗歌“不是游戏,而是产生于自然的一种力量,它使人对事物的梦想变得清晰,使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比喻,这类比喻不但从实践角度讲是真实的,而且从梦的冲动角度讲也是真实的。”这个比喻就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报道,它是关于人类对“全”永恒的、不灭的梦想的比喻。只是这个比喻的创造者和欣赏者,将会变得越来越少,以致于总有一天几乎会达到不存在的地步。但这些少量的人,传承着来自于人类灵魂深处的灯火。他们的举动多少显得有些不合适宜:正如不能因为发明了飞机,人们就放弃了散步,恰恰相反,正因为有了飞机,散步反而显得奢侈起来一样。
(2000年11月13-14日,北京看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