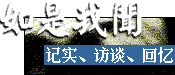沙门:请问《黑白条纹衬衫》和《李小多分果果》〔见《橄榄树》一九九九年八月期--编者注〕你更喜欢哪篇?或者说,自认为哪篇写得更好?
巴乔:我对《李小多分果果》更满意些。
沙门:《黑白》中你用了层层剥笋式的逆推结构来揭开悬念,从手法上来讲很先进,但内容却异常简单,你怎样看待形式和内容?你认为仅仅靠高妙的叙述手段就能构成一篇好的小说吗?
巴乔:《黑白》的结构显然是有意为之的,其实也说不上新鲜。刚写完还算兴奋,可突然地想起:张弛的《不腻斋》、《与范哥犯葛》(记不太清了,好像是这两篇)似乎是类似结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是否潜意识受了他的影响也未可知。
我们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提起笔,冒出的却是别人的东西,而尚不自知呢。作为我最初的想法,“逆推”是一个方面,各章节之间的“勾连”也是我的经营。
还有,尝试着用一种“简洁”的叙述、“少年血”等等都是我动笔前的想法,不知现在做得怎样。也许正因为考虑得太多,以及“逆推”的必然后果,《黑白》一文预设的意味似乎很浓,这也正是我对它不太满意的原因。其实我倒不觉得《黑白》的内容简单,事件可能小了点,惟其“小”,少年时对暴力莫名的崇拜便更有了探究的必要。也许是功力有限,文章没有充盈起来,让人看出“薄”来,但这却绝对不是字数的原因(两千字)。至于形式与内容,太多人说过了,好比穿鞋,大两码固然不跟脚,削足适靴更要不得,吃排档时趿拖鞋,结婚时我是定要西装革履的。叙述于小说来讲当然十分重要,其实小说也无非两点:“讲个什么故事”、“怎么讲”。单田芳的评书人人爱听,倘若我登台开口,不吓死吓跑十之八九那才怪呢。另外,你要让单田芳去讲“星球大战”,估计也能吓跑个五六成。
沙门:《李小多》中你设计了一个具有迷惑性的角色混乱,让人弄不清“我”到底是成人还是幼童。以我的理解你是用这种方法来获得一种新的性感,如同人们做爱时变换交合体位一样,你说是这样吗?或者还有什么更深的用意?
巴乔:《李小多》中的“我”应是个成人,但你所说的未必不是一种解读的方法。
其实这篇小说的产生很偶然,那时我还在电视台干活,有一天想做一个专题:“世纪末的童谣”,收集一些古怪好玩的儿歌,串连起来,不著一词。“李小多”便是一盒幼儿歌带其中一首。这个节目后来流产了,这篇小说倒写成了。是“李小多”给我找到了视角,叙述的基调也便在“分果果”中确定了。开头我制造了一些叙事的遮蔽,以后则注重于情绪的表达。有两处遗憾的地方:一是写到“老军医”时我因事外出一周,回来后先前的感觉怎么也找不到了,因此草草收场。
第二点是别人指出的,“我”的形象似乎是“半痴不癫”的,但究竟是个透心亮的无业青年,作为叙事的迷雾可以笼罩全文,但具体场景处理应兼顾事理。如与幼儿园园长的对话,语气可以是童稚痴呆的,但问话本身应合乎常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沙门:你受哪位作家影响最大?
巴乔:影响过我的作家实在太多了。
我最初写小说的动机十分简单,因为苏童。苏童与我是校友,小学校友。在他到北师读书后的第三年,我成了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看到了他那些“香椿树街”小说。我几乎没有考虑就喜欢上了它们,因为它们与我实在是太熟悉了。那条香椿树街我每天都要经过(我家便在香椿树街横向的另一条街上),作为童年记忆和当时生活的绝大部分,我为能从《城北地带》里找出每个能与现实对应的地方而感到兴奋。而那篇苏童自称对他影响深远的《桑园留念》里的故事发生地——“桑园里”,至今还住着我一位小学同班同学。
我因此发现了小说是一个多奇妙的东西啊,而写小说又是件多么有趣的事啊。
当然,我正式写小说始于两年前,而似乎知道了一点小说是怎么回事则在去年冬天。或许,将来这个时间还会修正,如果我继续写下去的话。但至少,阅读的兴趣和写作的最直接动因却是苏童给我的。去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苏童。
那天正好下雨,我站在江苏电视台的大门口,苏童剃着板刷,好象是和王干一块到的,我觉得,他比我想象中的可要胖多了。
还有,范小青于我有类似的影响,我称她为“范老师”。而汪曾祺和废名使我对“语言”有了概念,韩东朱文让我看到一种“力量的写作”,王安忆则常令我突生幻灭之感:你还写什么小说啊?!
影响我的外国作家当然也有很多,因阅读与感悟均有限,还是不谈为好。
附上一篇短文〔见附录--编者注〕,是篇“创作谈”,或许能表达我对真正好作家的由衷的尊崇之意。
沙门:巴乔,你说你辞职在家写作,我心里一下就出现高更和 Sherwood
Anderson 的名字,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你毅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又是什么使这样的举动可能呢?我想这一定会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事实上我已暗暗受了你的启发,心里筹划着将来如何在挣到一点钱后停业一年专心写作呢--不能全神贯注于自己热爱的事情实在是一件太辛苦的事!
巴乔:其实也没有什么,一种个人的选择而已。我原先在电视台干,待遇在我们那应算是不错的,可它留给我自己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你知道,写作总得有一定的时间保障,当我苦于脑子里有想法却没时间动笔或情绪来时却被外在的东西阻隔间断得四分五裂时,我想,还是歇下来吧。我的《离开南京的日子》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多少传达了自己一些这方面的想法:“那不正是我想要的一种状态吗。一份时间充裕的工作,一种松散的关系……”它们都符合我对“工作”的要求--如果我非要工作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份工作的好,它至少能给我基本的生活保障,那样我写作的心态就会更平和些,可我也知道这样的工作可遇而不可求--谁会愿意养个闲人呢。你要吃饭,你就得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来南京前,我对原来的单位颇有微词,我本以为可以得到理解和声援,可有个朋友却并不给我面子。他说:“单位给你发工资,你倒总想呆在家里写东西,从道义上讲,这也说不过去啊!”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简直可以说是醍醐灌顶,它彻底扭转了我对生活的许多看法。我辞职,不是单位给了我什么压迫,我更不能以受害者或是叛逆者的形象自我标榜,那将是很无耻的。我辞职,仅仅是我个人的选择,它仅仅说明了我的无能(因为不是跳槽--我也无槽可跳),我无能到不想工作,我无能到只想着写作……”七月初,我递交了辞呈,单位挽留了一下,八月批了下来。我的辞职理由是“丧失工作热情”,这也算是原因之一吧。辞职后面临的经济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不懂得节省,而电话费却因上网和与外地朋友的联络而直线上升,我还要抽烟,间或还得请次酒,我目前的稿费还不足以负担这些,基本上在靠积蓄维持。辞职后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兴奋点少了。请注意,我说的不是所谓“资源”,而是“兴奋点”。写作当然是需要兴奋点的,但我目前成天呆在家里,面对的除了电脑便是书籍,使我产生写作冲动的“点”越来越少了,这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苏州毕竟不比北京或南京,没有一拨相同状况与想法的朋友(就我接触而言,辞职居家写作的在苏州可能也就我一个吧),白天我常常会找不到出门的理由,朋友们都要上班,我出去干嘛呢?事实上,辞职后我的生活反倒比以前规律多了,熬夜也少了,是的,熬夜干嘛呢?明天不多的是时间吗?……再过一阶段吧,等我的经济不足以维持目前的生活状况或“兴奋点”的困扰加剧的话,我可能会出去找工作。
同样,我也不觉得这是种值得自怜的妥协,看到吴承骏的一段话,我觉得他说得没错:“对我来说,我觉得辞职是为当时的情形所迫,而重新找工作同样的也是为目前的情形所迫。这两者在时间上是错开的。它们仅对各自发生的那个时刻负责,而它们本身决不是互为因果。”沙兄,如果你将来也打算居家写作的话,经济一头当然会考虑到,有关“兴奋点”确实也该有预见。不过,北京不比苏州这小地方,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形。
不管怎么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总不会太苦的。
沙门:嗯,你的情况对我很有启发。经济倒在其次,你说的“兴奋点”的问题确实值得考虑。海德格尔说“烦”乃生存之本,佛家说“烦恼即是菩提”,生活的不如意也许正是创作的源泉,离了这个源泉,给自己布置一个安静隔绝的“巢穴”,反而写不出东西来,也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我想如果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家,
有需要长时间劳动才能完成的写作计划者,还是必须全力以赴吧?希望你能走出低潮,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